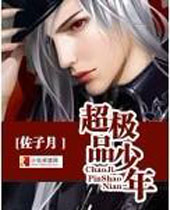莫欺少年穷 by: 廑渊-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醒挽真伸手撩开帘子,看了眼外边不见丝毫人气的大悲寺,不由笑道:“只有一个涅仪在,宣识色胆子未免大了些吧。”
他懒懒地挥了挥手,既然如此,那便……杀了吧!
第二十五章:方看梅柳春
雪落在宣识色的眉上,他看着眼前一片灰烬的大悲寺,难得想放声大笑。
与太虚道一战未完,却听闻碧海流霞境之人正在赶来。
万般无奈之下,也唯有放弃一途。
至半路之时,就有噩耗传来,宣识色静了百多年的心,在那一瞬间几乎完全崩溃,喉间一股腥甜被他狠狠压下。
他面上虽然不显,但内里却是乱到极致。
一步错步步错,大悲寺千多年基业,竟然真就毁于他手!
等到了浮晅,见了那一片被烧成灰烬的断瓦残垣,他再难以忍受,低头便吐了一口鲜血。
身边弟子一阵惊呼,方从古臧赶回的知微扶住他的身躯,神容着急:“师父!”
“涅仪何在?”宣识色靠着知微的扶持,声音虽然低弱,但仍清晰可闻。
知微扶住他的手紧了紧:“大师兄……不在了。”幸存弟子告与他,涅仪不敌醒挽真,葬身火海,尸骨无存。
“啊,”宣识色脸上滚落一滴清泪,“不在了……不在了,你说,这是否是报应?”
他想起那个焚城的命令,一时恍然不知身在何处。
知微声音哽咽,但仍旧坚定:“大师兄不悔,我……弟子不悔。”
“我……也不悔。”宣识色推开知微,有些颤颤巍巍,过了片刻,便站得笔直。
“师父!”知微心有担忧。
宣识色伸手阻住他靠近:“仲闲与重兆何在?”
知微低头回道:“二位师兄还未回来。”
“好,好,很好……”宣识色突然低声笑了起来,“你将大悲寺……散了吧。”
“师父你在说什么!”知微大震。
宣识色低头站在风雪之中,衣衫不动,闻言缓缓道:“散了又如何?我大悲寺人未死绝,将来换了名字卷土重来,有何不可?焚城……焚就焚了,有何可悔?世人……大多容易忘记,百年之后,你且问问,谁还记得我大悲寺?”
“我大悲寺弟子遍布大荒,无处不在。他们都很好,只要还有一人在,我大悲寺就还在,纵是名字变了,大悲寺还是大悲寺。人说无不散之宴席,可散了之后,再聚一回便是,有何可惜!”
他说到此处,突然大声笑道:“知微你且看着!百年之后,这大荒必定还有我大悲寺弟子缁衣而行,谁敢说我大悲寺败了!哈哈哈……”
宣识色一贯声音低沉,知微首次见他如此激扬,耳边听见他笑声穿透云霄,身周弟子似有所感,俱都跪在地上,垂头不语。
知微跪在宣识色脚边,听着笑声渐渐微弱,终至无声无息,心中悲怆难发。
抬头看去,宣识色背脊裸露,双手垂于身侧,风过之时,身上雪白衣衫突然掠起,拂过他的面容,他闭目抿嘴,宛如生时,甚至比之从前更多了一分生气。
知微三叩首,伏在他的脚边,低声道:“师父走好。”
一片白色的衣袂扫过知微的手,他怔怔看着那片白色,突然伸手握住那片衣角,泣不成声。
待花开时节,与君同归。
宣识色死讯传到醒挽真耳中之时,他正倚在榻上,手上握了杯美酒,只是随意应了一声。
当年的天下三大宗主,如今……竟剩了他一人。
“其实,还是我比较幸运。我喜欢美人喜欢美酒,只要我喜欢,夺过来便是,随心所欲。也没有什么大抱负,只想过得舒心些。可怜叶抱玄思虑了一辈子,宣识色劳累了一辈子,连个安稳日子都没过过。甚至说……连杯美酒都没喝过……”
醒挽真盯着手里握着的那杯美酒,低声自言自语:“不过,我还是个好人。”
他起身手腕一转,那杯透彻如琥珀的美酒全与了尘土:“看在你们没喝过什么美酒的份上,这杯酒就给你们吧。”
“虽然可能晚了,但我还是想说一句,这黄泉路上,可千万行得慢些。等我哪天也下去了,我们三人还可聚上一聚。”
“生时没有见过几面,死了可得让我看个够啊。”
他伸手为自己倒了一杯酒,仰头一饮而尽。
古臧大火烧了整整七天,方才渐息。
曾经的繁华小城,如今不过是一片焦土。
沉醉初醒的时候,神智还未完全清楚,背后的那人紧紧拥着他,却无一丝声息。
他心中兀地一震,片刻才回过神,提肘推了两下。
耳听着那人呼吸声渐起,直至往日绵长,他低声道:“你可还好?”
祁薄阳“唔”了一声,才回道:“无事。”
沉醉起身打开山河图,许久不见光明的眼睛一时竟有些刺痛,待遮了会眼睛,才没了这种感觉。
他掸了掸衣衫,黑灰飘落,举目望去,尽是一片焦黑色。
常年居于东海,他见过浩瀚无垠的大海,却是初次见得这么一大片的焦黑色。
断梁砖瓦民屋,全都付之一炬,焦味扑鼻,甚至还有许多不成人形的残骸隐在其间,惨烈无比。
见此之景,纵是向来心如止水的沉醉,也觉胸中积郁难发。山河图铺展开来,略一振手,抖落了一片烟尘,才见山水之色宛然如新,日光中才发现原来那墨色竟然带了青色,只是不甚明显。他将山河图收入袖中,手抚过长袖,肃容无话。
祁薄阳面色同样凝重,腰间的乌鞘长剑突然发出一声脆响。
他拔出一看,才发现这剑已断成了两节,断口平整,不似外力所成。
“这……”
沉醉伸指拭过断剑:“剑本至凶之物,焚城一难中,无辜枉死者众,满身怨气凝而不散,与你这剑相冲。这剑不过中上,自然抵不过这满城沉怨。”
祁薄阳默然片刻,方道:“人死果然还有灵在?”
十年前边陲小镇,他与沉醉一同过了中宵之节,他曾言人死了便是死了,可如今……
他却开始踌躇了。
沉醉闻言,似是想起了什么:“若非恨深情切,人死自然如灯灭,再无痕迹。这满城沉怨虽在,却不过是死前胸中一股怨气所化,过些时日便就没了。但……”
他顿了顿,问:“你可知道凤凰城的露清饮?”
祁薄阳颇有些恍然大悟的感觉:“她……”
自他接掌太虚道以来,大荒诸多隐秘也一一向他展开。
露清饮当年创了一门转生之法,虽然有些疏漏,使致身体荏弱不堪,但记忆却是不曾缺失分毫。
以她看来,这便是求得了长生。
而这转生之法,唯有在她躯体将朽时,才可用来。若人死脱了躯壳便是无灵无感,她哪里能用成这法子?
他方才有所顿悟,却听沉醉道:“当年露清饮与你太虚道先人交好,历代道主随身之剑景风,便是她亲手所铸。三十五年前,景风剑却突然有了个缺口,叶抱玄心中深以为憾,恰逢我师父登门拜访,带了去凤凰城与了露清饮,重新开炉锻造。”
“景风剑所用材质世间难寻,只找齐材料一事,便花费了整整二十年。露清饮身体荏弱非常,为了动手锻造,又休养了十年。如今算来,正是取剑时候。”
“三十五年……”祁薄阳心中惊骇,“她竟为一把剑耗费三十五年?”
沉醉点头:“而且,若我没有猜错,等景风重铸之后,她也该再一次转生了。”
“何必……”祁薄阳低声道,“太虚道中好剑许多,为何一定要这把景风呢?”
沉醉道:“于你而言,景风虽好,却不过是一把剑而已。对于她而言,这却是一份故人情谊,聊以凭吊,也可一抒情怀。”
“这大荒千多年之事,她一桩桩一件件全都看在眼中,当年的故人,一个个地不在了,若是没了这份寄托,她如何活着?况且,当年那位太虚道先人,是她倾心爱慕之人,虽已轮转几世,但他的随身佩剑,她怎舍得?”
祁薄阳心脏抽痛,忍不住握了他手:“你……你既然知道长生之苦,为何……”
沉醉摇头:“她那门转生之法,本就有所不全。若是只求长生,我早可从她那里得来法子。可我要的却是无一丝破绽的长生,这二者区别,你可懂得?”
见祁薄阳不语,他又道:“露清饮虽然不死,却困于凤凰城中,不得外出。而我,绝不会走这样的路子。”
他低头吹去婆罗花上沾上的烟尘,神色温柔:“你看,这花快开了。”
祁薄阳凝目望去,果然原本只是个小小突起,现在却能看出是打出了指甲盖大的花苞。
“按古籍记载,婆罗花花开奇大,如今这花苞,还未到极处,怕是还得等上段日子。不过,我猜也用不了多久了。”
祁薄阳与他相处这么多日子,却是首次见他如此温柔表情,衬着身后残酷之景,犹为诡异。
况且,这婆罗花许久不开,怎就到了这焚城之日,长势便迅猛起来,其中奥妙,怎能不让他深想。
第二十六章:共别川河上
大火熄了之后,城内渐渐有了些人走动,观其形容,多神思不属,脚下酿跄,不乏老幼之辈,相偕而行。
满面悲怆,一身凄凉,衬着暮色斜阳,将将日落星垂时,如行走人间的孤魂,多了些森然之气。
古臧之外的旷野,原本也有许多百姓聚集在一起,见大火熄了之后,才陆陆续续回了古臧。
他们多于火中仓促出逃,却有亲友仍在城内,故而于城外徘徊不去。回城之后,所见得的便是残骸烟尘。原本高大结实且排列紧密的建筑,被大火烧成了焦黑色,略微触碰,就淅淅沥沥落下一片碎屑,更有甚者,不堪重力,轰然崩塌。躲避不及,难免还有些伤亡发生。
在火中呆了整整七天,沉醉与祁薄阳踏着满城尸骸走出的时候,面上虽然拭去了尘土,但原本整洁干净的衣衫,却不复原先衣色。
加上鬓发微乱,哪有平日半分出尘模样。
但除了他们,再没有人于这七天之内,走出古臧。
回首望去,焦黑中难见异色,七天的人间炼狱,饶是沉醉向来心智坚定,也有些说不出的感受。
当初事未起,他与祁薄阳就对宣识色的手段有了猜测,只是……
到底任凭他去,未曾相阻,甚至还有推波助澜之意。
不知何时,天上竟然落了瓢泼大雨,雨线密密如注,一扫残存烟尘。黯淡昏色之中,银丝接天连地,碧落幽冥,不过两端。
呼吸间,似有远方草木清香,绕于鼻尖不去。
有人于雨中披发跣行,嚎啕大哭,声嘶力竭,捶胸忘形,欲癫欲狂。
若是这雨早下片刻……会否有所不同?
此次焚城之劫确为大悲寺所为,这一消息早已散出,一时之间,大悲寺声名剧降,与魔头无异。
加之宣识色身死,哪有功夫来平此声潮。
风满堂一众静候城外,见他们出得城来,撑伞备马,一行人便往昆仑赶回。
或是刚见过了人间惨象,心有余悸,一路竟无人多言,寂寂无声,只闭目静思。
日夜兼程之下,十日后,终至昆仑。
与大悲寺一战中所损的玄圃宫,已经大致清扫过一遍,虽然还有疏漏之处,不过细枝末节,可缓缓整改。有些弟子身死,还有更多的弟子受了伤,但当祁薄阳站在天庭之时,大多数人的脸上并无怨愤,脸容平静,俯身之时青袍曳地,峻挺如青山。
大悲寺弟子众多,散于大荒各处。
虽然宣识色临终前,已下令散了大悲寺,但除了极少换下缁衣过平常生活的弟子,也不乏焚身随宣识色而去,或是隐于暗处,伺机再出之人。
太虚道的与祚山极默契地将原来大悲寺的范围,一分为二,于各自范围内开始搜寻大悲寺弟子。
若有结果,格杀当场——二者于这一点上出奇一致。
与是否心有仁意无关,无论是醒挽真或是祁薄阳都知道,终会有大悲寺弟子脱逃,只静待良机重来。
百年之后的局面或可想见,宣识色纵然不在,但谁都没有真的以为大悲寺会如此简单便真的湮灭了。
大荒,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千年间风起云涌,人物辈出,宗门林立,到最后不过昆仑、祚山、大悲寺与蓬莱而已。
当年昆仑一系化而为三,后又为四,如今笛吹云、白日迟与楼沧海,再加上归来的祁薄阳,四宗宗主自上回别后,重聚昆仑。
若是从前,有大悲寺作为太虚道与祚山之间的平衡,自然无碍。但宣识色已逝,大悲寺呈退隐之势,直接将太虚道与祚山推至对面,再无转圜余地。
祁薄阳执剑立于天庭,焚香祭告天地。
时隔千年,昆仑三宗重归于一,再无三宗之说,只有昆仑,祁薄阳为主。
沉醉是除昆仑外,唯一观礼之人。
耳边鼓点声声,檀香悠远,云气疏淡,祁薄阳站在他两丈开外,背对而立。
他扶剑的手修长却有力,玉冠束发,墨发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