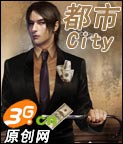暗香腐月黄昏-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觐灵摇头,他不明白,他一直在思念著这个人,却想不起他是谁,即使知道他的名字,也无济於事。
远处,湖心亭上,红色披风士子正在辞行,登舟离去时,舟子喃语:“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暗香浮动月黄昏 第十章
这段时间,觐灵没有出去走访友人,几位友人留意他好几日没出现,结伴上门拜访。见觐灵病恹恹,脸色苍白,还以为他生病了。觐灵笑说他没有生病,大概是终日关屋内,没晒到太阳的缘故。这几位友人与觐灵认识多年,这才想起觐灵怕热,又逢孟夏,龟缩在宅中,足不出户,也属正常。
觐灵平日朋友只有寥寥几人,以琴友居多,里边有老迈的古琴大家,有年少的琴徒後生,有开古琴培训班的古琴教师,这些人,聚在一起,除非举行琴会,基本不弹琴,也就是聊聊天,俩俩成群,在院子里下棋。
午後院子,树阴下,石桌前下棋,是个好消遣,耳边蝉叫一片,偶有几声蛙声,十分惬意。
觐灵棋艺不错,连赢两盘,起身给众人烧水,倒茶。院子中的两张石桌各有两三人,有的观棋不语,有的举棋子琢磨,有的抓耳挠腮。
“觐灵,上回那些木炭还在吗?干脆搞个烧烤会,我出啤酒。”老刘兴致高,见觐灵过来给他倒水,急忙询问。
老刘是古琴培训班的老师,年纪与觐灵相仿,为人幽默,好说笑,也常被友人取笑是开培训班骗家长钱的流氓。
“还有一小袋,但不够用。” 觐灵回答。邻桌立即有人喊:“烧烤啦,大家准备掏银子了,老刘说要出啤酒!”
众人听说要烧烤,纷纷表示赞同。有的自告奋勇说回家载烤架,有的说他去买食物,有的说去买木炭,一哄而散,一眨眼功夫,就只剩觐灵与林老两人。
林老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古琴演奏家,为浙派传人,他资历深,但喜欢跟年轻人凑一块,没脾气也没架子,觐灵及这个小团体里的人,都很敬重他。
林老拄杖进厅看电视,他倒也想帮点忙,只不过这些晚辈也不让他搭手。
觐灵独自在厨房忙活,准备油盐酱醋胡椒白糖,刷子,叉子,清洗烤架──往日也曾在他家烧烤,他有一具烤架。
如果没有这群友人,觐灵的人生将十分的寂寥,他的性子不擅於去主动结交人,而身边又没有亲人,最亲的一位已去世,次亲的两位,形同陌生人。多年前,他身边还有个李则成关心他,多年後,真得只剩这群友人了。曾有次大病,身边一个人也没有,病得实在沈重,自己去不了医院,好在林老正巧打来电话,知道他生病,急忙叫人过来将他送去医院。
这群友人中,并无人知道他的性取向,这些人不爱打探别人的私事,也是因此,觐灵跟他们相处总是很开心。
太阳偏西,大夥陆续归来,有提木炭的,有提食物的,有扛啤酒的,有抬烤炉的,凑一起,眉开眼笑。
洗牛排,串羊肉,剁蒜头,扇碳火,各忙各的。也有人偷懒,比如老刘,坐石桌前啃买来的卤鸡爪下酒,被人逮著,吆喝去照看烤炉上烧烤的食物。觐灵将装食物用的碟盘搬出,正好听到他在哀号。
夜幕降临,院子灯火点起,众人围在一起,喝酒吃烧烤,老刘建议玩麻将,竟真得凑了桌麻将,就在院子里搓麻将。觐灵拿空碟子到烤架旁,将烤好的食物装上,赌鬼们在一旁喊:觐灵,来两串香肠,来根玉米,来个鸡翅。觐灵回:“自己过来烤。”
将两块牛排夹上盘,就听到院子外的车声,觐灵放下盘子,朝院门走去,他认得是卿甫的车。卿甫下车,看到院子里满是人,还有人搓麻将,一时间,还以为来错地方,见到觐灵才确定他没有认错房子。
“喝,好热闹!”
卿甫先是十分吃惊,一见到觐灵腰间围的熊猫崽图案的围巾,又忍俊不禁。觐灵被他笑得莫名其妙,发现卿甫眼睛落在自己腰间,才想起自己围条围巾,但仍不知道卿甫在笑什麽。
“觐灵,介绍下,这位朋友很陌生啊。”
老刘又在一旁起哄,其他人因为不曾见过卿甫,也和声说是啊是啊。
卿甫这人虽然不像卿年那样自来熟,但是他心情好的时候,也十分好相处,拱手介绍:“小弟姓赵,XX街1451档开古玩店的,正好过来送货,大家日後多捧场啊。”卿甫这是玩笑话,众人一开始还信了,以为卿甫是来送货的夥计,後来见觐灵待他十分亲近,也猜出这人是觐灵的朋友,交情还不薄,只是都好奇觐灵怎麽不曾提起,及往日也不曾见到。
“觐灵,有烧烤会,应该通知我嘛。”
说这话时,卿甫已经自行去烤炉前夹了两串羊肉一只鸡翅,坐在石桌前大快朵颐。
被这麽一说,觐灵都不知道回什麽了,时冷时热的卿甫实在让人不知所措。
“这几天店里生意忙,仲敏跑货,我抽不出身,要不早想过来看看你。”卿甫边吃边说,还将桌上的一些竹签残羹扫去,示意觐灵也坐下。
“我身体早好了。” 觐灵在卿甫对面坐下。
“你没生病时就不能来看你吗?”卿甫不满嘀咕,将一串羊肉解决,抛掉竹签说:“说起来,你好像从没打过我电话吧?”
又没事,打你电话做什麽?这几天,你不也一个电话都没打过,觐灵暗忖。
“哇,你们两个躲这里,来来,觐灵叫你那朋友,一起过来玩一圈。”
小武大概是赌输了,正到处抓人替位,找到石桌来,见到觐灵跟卿甫,十分兴奋。
“叫林老吧,林老在那边看烤炉。” 觐灵手一指,将小武支走。小武是林老的徒弟,还是个大学生。
卿甫往觐灵所指处看去,见到一位白胡须老人,很有修道之人的气质,心想,觐灵这群朋友,也不知道打哪冒出来,以前来觐灵家几次都没遇见过。“卿甫,罗先生,最近没再出什麽事吧?” 觐灵的话将卿甫的注意力唤回,卿甫一听又是谈仲敏,心里不满,随口回:“他搞人鬼情未了,外人也不便说什麽。”
卿甫纳闷,觐灵怎麽每次都问仲敏,也不问问他这几天做成了哪单生意,关心一下他。
其实,觐灵要是不问仲敏的事,也找不到话题跟卿甫说。
“你怎麽不问问我手怎麽了?”卿甫抬起左手,一副可怜状。觐灵根本没留意卿甫左手,卿甫举起,觐灵才看到卿甫食指和无名指包扎纱布,两个手指捆在一起,吃惊问:“手怎麽了?”拉过卿甫的手端详,见纱布上的血迹已经干涸,纱布也有些脏,看来是旧伤。
“抬木箱时夹到手指,骨折了,医生说一个月都别想碰键盘。”
卿甫纯粹装可怜,这点伤他没放心上,再说他现在懒得很,连约稿都没接,一个月不能碰键盘,能有啥影响。觐灵轻轻说:“那尽量不要去碰水,要不伤口会溃烂。”
卿甫将伤手袖起,继续单手拿鸡翅啃,还拿眼瞅不远处搁放的一箱啤酒。觐灵留心卿甫,起身去拿来两瓶,还携上两只杯子,为卿甫与自己都倒上。卿甫喜悦,急忙去烤炉上夹烤好的食物,又将猪排,鱿鱼,豆腐皮,玉米都给摊上烤架上,排满一烤架,才美滋滋端份热气酥脆的食物回到石桌。觐灵坐在石桌旁,注视卿甫毛躁的动作,嘴角带笑,他心情很好,不知道是因为有朋友来拜访他,大夥凑一起烧烤,还是因为卿甫的到来。
两人坐一起喝酒,觐灵先前已吃了点烧烤的食物,光是小口喝酒及看卿甫啃鸡翅。卿甫喝酒不用杯子,直接拿酒瓶灌。
“我脸上有虫子吗?”卿甫揄揶。觐灵也没意识到自己一直在看卿甫,嘴角还挂笑,被卿甫这麽一说,脸立即红了,低头喝酒不语。
华灯初上,院子的角落里,两人於石桌前对坐,觐灵低头,手握酒杯沈默不语,卿甫的手不规矩地摸上觐灵的脸庞,将头凑过去,唇几乎贴上觐灵的耳际,喃语:“觐灵,我那天,摸著你的脸,突然想……”
没来得及觐灵做出反应,摔开卿甫的咸猪手时,老刘突然鬼鬼祟祟“喝!”的一声,出现在远处。六目相对,你震惊,我恐慌,也只有卿甫面不改色。
“我我……我是来问你们要不要玩麻将。”老刘还处於震惊中,说话口吃。
这石桌位置比较偏僻,又有林阴遮挡,卿甫以为不会被人瞧见,这才敢对觐灵毛手毛脚,要不他这个人虽然不检点,但也会考虑觐灵的感想,不至於大胆做出这样的动作。
“我手受伤,玩不了。”卿甫将伤手举起,大大咧咧回道,面无愧色。觐灵脸色灰白,欲言又止。老刘当没撞见两人“奸情”,尽量平静离去。
“觐灵,我……”这回换卿甫欲言又止,觐灵摆手,别过头去,他本示意卿甫不必说什麽,不过这动作看在卿甫眼里,倒觉得像在拒绝他。卿甫一时狼狈不堪,焦急站起踱步。被人撞见,卿甫倒不绝狼狈,被觐灵拒绝才真叫狼狈,他又没追求过同性,也不知道如何表达。觐灵心绪烦乱,心想老刘这人嘴巴一向严实,人靠得住,应该不至於说予外人知晓,但也不确定老刘什麽也不会说;同时又想卿甫是要对他说什麽?又想,这是要违背自己曾下的决心吗?
他喜欢同性,他对异性一点兴趣也没有,他本以为自己已戒掉这恶习,不再为任何人所吸引,但自从遇到卿甫,他就知道,一切都是空谈。这是前世的情债也好,今生的孽缘也罢。
“都烤焦了,没人记得给它们翻一面。”林老拿串烤成黑碳状的玉米过来,正好见到卿甫与觐灵分站一旁,各有心事。“来,年轻人,叫你呢,过去照料你搁烤炉上的食物。”就是那个年轻人有心事,林老都不忘念叨,他最见不得人浪费食物。卿甫灰溜溜跑去照料烤炉,反正他心里乱糟糟,正好找个地方静静。
卿甫走开,林老邀觐灵到大厅下棋,说石桌这边灯光昏暗,觐灵把酒瓶酒杯带上,在大厅里边喝酒边下棋。林老棋艺很高,觐灵以往跟他下棋,总是赢得很艰难,谁想这回才下至半局,觐灵竟赢了林老,林老吃惊不已说:“我见你惊魂未定,本想好好赢你一回,谁想反被你狠宰。” 觐灵哑笑,问林老:“要不要再来一局。”两人各自将棋盘上的黑白子收回。
另一边,卿甫义务给众人烧烤,之後被老刘等人唤去喝酒,此时麻将已经散了。老刘只字不提刚才的事,其他人十分好奇卿甫怎麽跟觐灵认识,问个不停,卿甫说得谨慎,只说是在校庆上认识,其他的一概不提及。
喝酒时,卿甫不时往大厅里张望,见觐灵与林老下棋,觐灵边下棋边喝酒,还出来外头取了一支啤酒。卿甫心里也是瓦凉,为自己的情感感到苦恼,於是你喝,我也喝,同席的都说卿甫好酒量。
一夥人闹至深夜才离去,留下喝醉的卿甫与半醉的觐灵,卿甫拉住觐灵道歉:“我没想到老刘会……会突然出现,实在很抱歉。” 觐灵摇头,黯然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老刘与我结识久了,也许早便知道了。”卿甫喃喃:“那我回去了。”他摇摇晃晃要去开车,迈出门槛时,狠狠跌了一交。觐灵急忙去扶住他,焦急说:“你醉成这样,怎麽能开车回去!伤哪了?”四周灯光昏暗,觐灵在卿甫身上胡乱摸索,见卿甫裤子膝盖蹭破,将裤筒挽起,察看伤势。膝盖被地上沙砾蹭破皮,这种伤,伤口不深,但是很疼。“起得来吗?”将裤筒放下,觐灵想搀起卿甫,无奈卿甫四肢不听使唤,又摔伤膝盖,站不稳,两人没走两步,便跌做一团。卿甫压在觐灵身上,觐灵摔疼,又气又好笑,躺地上念叨:“谁让你喝那麽多酒了,你这样怎麽将你搬进屋去。”卿甫支起胳膊,翻身贴进觐灵,突然捧住觐灵的脸,不由说狠狠吻上,这个吻跋扈而霸道,觐灵被压制得不能动弹,想推开卿甫又没力气,只得由著卿甫又吻又摸。卿甫恨恨说:“你让老子喝了,就是你让老子只能借酒消愁。” 觐灵放弃挣扎,被吻时脑子一片空白,再听到卿甫抱怨的话语,心中无奈又酸楚。到底是谁让谁这段时日里,过得一点都不安稳,整日心不在焉,惆怅凄苦,只得神游太虚。
卿甫醉得不能行走,他强吻过觐灵後,觐灵还得将他架进大厅。他虽然不想累著觐灵,想自己走,无奈酒意上来,四肢都不听使唤。觐灵将卿甫又拉又扯又抱搬进大厅长椅,觐灵累得直喘气,卿甫看著觐灵,笑得很欠揍,说:“我那天……摸你的脸,就想吻你,就想吻你……” 觐灵脸红,想到适才两人跌地上,卿甫的强吻,接著又想这人醉了,醒来想必会忘记吧。觐灵进屋去拿毯子,拿好毯子出来,卿甫已睡去,睡得很惬意,嘴角挂笑。觐灵将毯子披在卿甫身上,多看了睡梦中的卿甫几眼,就也回房去睡,因为饮酒,他困得不行,一贴床就睡去。
清晨,宿醉的卿甫坐在长椅上,抱头呻吟,头疼难受,抬头正见觐灵递杯热水给他。他看到觐灵,隐隐记起昨夜的事情,也不顾接水杯,抓住觐灵的手臂,将他拉到身边,身子顺势贴近说:“昨夜,你搬我进厅是吗?”觐灵点头:“嗯。”卿甫凝视觐灵,将头凑向觐灵,几乎要吻上觐灵,觐灵别过头,不让他吻,卿甫笑得无赖,揽住觐灵说:“我昨夜吻过你了。” 觐灵哪里想到卿甫一觉醒来,就对他骚扰,他还以为卿甫昨夜醉得不行,早把发生的事情都忘了。“昨夜,你醉了。” 觐灵拉开卿甫的手,想起身离开,卿甫却欺身而上,再次将觐灵压制住,又想强吻,觐灵在拉扯中抓到卿甫的伤手,卿甫“哎呦”一声,急忙松手。“活该。”觐灵不喜欢卿甫对他强来,脱身站一旁不理会。卿甫清早索吻失败,在长椅上挺尸,觐灵让卿甫去他床上睡。睡了一夜又硬又窄的椅子,这人也不嫌难受。卿甫喜不自胜,赶紧爬上觐灵的床,枕著觐灵的枕头,披著薄被,舒适而惬意,拿眼瞧一旁的觐灵,说:“才七点呢,过来一起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