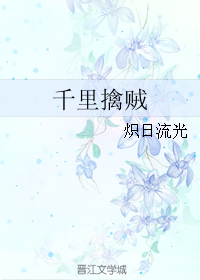送君千里-第4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叶鸿生低下头,继续与士兵说些什么。等他说完,阮君烈已经排除杂念,下定决心,对他喊道:“宾卿,你上楼来。我有事和你说。”
叶鸿生放下手里的事情,走到楼上,敲门说:“什么事?”
阮君烈指着椅子,让他坐到自己对面。
叶鸿生拉开椅子,坐下。
阮君烈手上拿着一张文件函。
叶鸿生等他说话。
阮君烈没有开口,只把文件递给他,简短地说:“你看一下。”
叶鸿生拿到手里,定睛一看,发现是一张调令,上面写明将他调至前线,负责前方战场七十三师的具体战术指导,加强固镇与彭乡两个点之间的战略防卫。调令上面是阮君烈的亲笔签名。
叶鸿生慢慢放下这张纸,重新看向阮君烈。
阮君烈硬着心肠,说:“明白了吗?”
叶鸿生说:“明白了……”
叶鸿生沉默着,不再说话,低头看调令,似乎上面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其实,调令上只有两行字。
阮君烈方才还不敢看他,现在又想听他说些什么。
叶鸿生却没有说话。
阮君烈忍耐不得,先开口说:“不是你做错了什么。宾卿,七十三师的位置很重要,他们没有经验,我不大放心。”
叶鸿生点点头,柔顺地说:“好。”
阮君烈一时没话说。
场面冷下来。
阮君烈端起茶杯,喝一口茶。
叶鸿生静静地坐了一会,问:“我什么时候走呢?”
阮君烈放下茶杯,冷酷地说:“现在就执行!”
叶鸿生站起身,大声应道:“是!长官。”
叶鸿生回到他自己房间,去整理行李。楼下的卫兵也忙碌起来,帮参谋长打包行李,再帮他把行李抬到外面去。叶鸿生的东西不多,没有多久,一切收拾妥当。
阮君烈在屋里坐着,忍着不去看他。
准备就绪,叶鸿生登上楼梯,来与他告别。
叶鸿生走进屋,对阮君烈说:“长官,我准备好了。”
阮君烈点点头,站起来,说:“好,我不送你了。地方离得近,你很快就能到。”
叶鸿生看着阮君烈,似乎对这种安排毫无芥蒂,目光温存。
阮君烈在这种目光之下,差点没法维持决定,但他还是没有任何表示。
叶鸿生说:“长官,我还能再见你吗?
阮君烈说:“按时发军报回来。我没有命令,你不要回来。”
叶鸿生立正,说:“是。”
叶鸿生转过身,向门口走去,阮君烈望着他。
叶鸿生忽然停住脚步,回过头,目光落在他身上,流露出一种难以磨灭的情感。
阮君烈心弦震颤,忍不住缓缓站起身。
叶鸿生凝望着他,低声问:“我可以想你吗,长官?”
阮君烈鼻子一酸,半响说不出话。
他走过去,揽住叶鸿生的肩膀,劝道:“宾卿,不必多想。我们最后会在一起的,一起名垂青史,或者一同被黄土掩埋。无论怎样,我们的名字会刻在石碑上,并列在同一个位置,永远也不会分开……”
临走前,他们没有亲吻。只有庄重的告别。
叶鸿生对阮君烈深深地鞠一躬,说:“长官,请多珍重。”
阮君烈目送着叶鸿生走出去。
叶鸿生迈步下楼,卫兵已经给他备好鞍马,做好准备。
离开时,叶鸿生抬头望了一眼楼上。阮君烈与他目光一接触,立刻将窗帘拉上,站到阴影里。
阮君烈透过窗帘,仍能看见叶鸿生,但是叶鸿生看不见他。
阮君烈看到叶鸿生垂下目光,离开了这个宅子。
叶鸿生骑上马,朝自己的驻地进发。同行的几名士兵使骡马帮他运行李,跟在后面。
阮君烈望着叶鸿生远去的背影,一直到看不见为止。
阮君烈走到桌前,喝了一口茶水,准备重新布置一下沙盘。
荒唐的日子过去了。
没有人会在意这种事,他自己也不会在意。
他与一个男子交‘媾,还因此获得了快感,这种事情太不可思议了。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不仅发生了肉‘体关系,像野兽一样地纠缠,还产生了彼此依恋的情感。
在这种情感的侵蚀下,其中一个人产生了厌战情绪,说他不想当军人,不再是曾经那个英勇无畏的军官。而另一个人在对方的影响下,情绪波动得厉害。
阮君烈深吸一口气,握紧拳头。
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实在是超出了一个军人所能有的荒唐。
调令还放在桌上,叶鸿生忘记把它拿走。调令没有实际用处,只是一个避免亲自开口的道具。
阮君烈伤神地伏在案上,又看了一遍,动手将调令撕个粉碎。
第 65 章
夏天像蝉鸣一样悠长,又像江里的水一样不知不觉地流过去。
叶鸿生离开后,宅子好像空了许多。
阮君烈感到,彭乡的山水生出些变化。过去的几个月,这个水乡晕染着一层如梦似幻的色彩,水边的茅草、石板上的青苔散发出一种柔绿,绿得醉人眼。船工的号子像一曲渔歌,哪怕是妇人们的捣衣声都是一阵阵柔和的拍子。
随着叶鸿生的离去,这种色彩悄然褪去,露出生活的本来面目。阮君烈发现,水边蚊虫多得很,捣衣的嘈杂声、船上的鱼腥味也叫人不耐烦。彭乡只是一个平凡的乡下小镇,并不比其他地方好在哪里,杂货店连杂志都买不到,只能等南京那边邮寄过来。
厨房每天变着花样做饭,但是阮君烈失去胃口。
阮君烈把叶鸿生送给他的那一副扇面图从卧室里拿出来,挂在书房。扇面上的山水依然是美丽的,画上有依山傍水的村落,透着氤氲的雾气,像一个小小的仙境。阮君烈不知道,是彭乡的钟灵之气统统跑到了这幅画里?还是说,叶鸿生摄走彭乡的水秀,把它藏进了这幅画里?
阮君烈撑着腮,望着这幅小画。
也许在战争结束之前,这就是一个到达不了的梦幻。
阮君烈站起来,把这幅画翻过来,将它面朝下,扣在墙上。
阮君烈打开新来的一叠报刊,翻阅《观察》杂志,想了解国府最近的改革动向。杂志刊登了上海方面的消息,蒋经国推动的金融整顿计划进行到一半,宣告搁浅,物价重新上扬。很多人在抛售房屋,转移财产。面对经济改革失败的消息,阮君烈心情跌落到谷底。
阮君烈只好不去细想,一想就觉得败象丛生。
徐州方面发来电报,这一次,阮君烈亲自去参加会议。
会议上,众人交换情报,猜测共军可能发起进攻的方式,议来议去,似乎是在捕风捉影。阮君烈感觉到,别的兵团情报还不如自己。阮君烈不赞成将战线拉得太长。他做汇报,告知上级,他把自己的队伍分成三个部分,摆成一个倒的“品”字型,他暂时想不出更好的防御方法。
散会后,阮君烈认为有必要巡视一下自己的部队。
他先去了十五师。
十五师驻扎在对岸,是先头部队,离其他兵团近,会掌握到最新的敌情。阮君烈到了军营,觉得队伍状态良好,听取过汇报。接着,他又乘船过江,去巡视七十三师。
阮君烈突然驾到,师长仓促地迎接了他。
叶鸿生不在指挥部,阮君烈心中失望。他耐着性子,听完师长的汇报,外面一阵嘈杂声响起来。叶鸿生听说阮君烈大驾光临,旋风般地从营地赶回来。
阮君烈打开门,看到叶鸿生同孙仲良一起回来,正在换沾了湿泥的靴子。
阮君烈一阵激动,把师长打发走,叫叶鸿生进屋。
叶鸿生进门,对阮君烈问好,坐在他对面,做了一个简短的报告。
阮君烈指着面前的沙盘,叫他过去演示。
他们靠近以后,叶鸿生不自觉就低下头,吻阮君烈的嘴唇。
阮君烈好像被魇住,没有反应,与他亲吻了好久。
当叶鸿生抱紧他的时候,阮君烈似乎一下子惊醒过来,按住叶鸿生的胸口,缓缓将他推开。叶鸿生后退一步,低头说:“长官,抱歉。”
阮君烈克制住自己,命令道:“你出去。”
叶鸿生出去,带上门。
阮君烈在七十三师的指挥部吃晚饭,时间不多,他要在天黑前回镇上。回去的时候,叶鸿生亲自送他,替他牵马。
叶鸿生陪着阮君烈走了很远,一直到他说:“行了,你回去吧。”
叶鸿生松开缰绳,阮君烈却没有立刻拍马离去。
阮君烈骑在马上,沉默良久,出声道:“你恨我吗?”
叶鸿生惊讶地望着他,微笑道:“我怎么会恨你?子然,我早就说过。我喜欢你,一时一刻也不会忘记你。不管你是否喜欢我,是否愿意饶了我。”
阮君烈黯然神伤,看着叶鸿生。
叶鸿生对他行礼,款款诉说道:“长官,我永远等你。”
阮君烈挥动马鞭,远远丢开他,回到镇上。
夜里,阮君烈躺下休息。
睡梦中,他与一个男子缠绵缱绻。这个人的嘴唇那么温暖甜蜜,和他想念的朋友一模一样。醒了以后,阮君烈暗自羞愧,梦中的温存和思念都是有害的,应该被清除的,眼下烽烟四起,这种情绪很不合适宜。
阮君烈下床,一个人望着月亮。
秋风中,万物凋敝,到处空荡荡的,没有声音。
阮君烈看了一会,觉得无趣,将书房的画摘下来,放在枕头旁边。阮君烈枕着山水,终于睡过去。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共军发动袭击,以四倍兵力将徐蚌地区的一个兵团包围。阮君烈得到军报,暗自庆幸被围住的不是自己。被围困的军团身负吸引敌军的任务,拖着共军,时不时苦苦告急。国防部发出通告,让阮君烈在适当的时机,派兵协助被围困的友军突围。
到了生死关头,阮君烈准备派十五师去执行任务。
阮君烈心想,战火快烧过来了,他应该把叶鸿生调回司令部,但是,他还在犹豫……
等一等吧,等到实在不行的时候,他再把叶鸿生调回来。面对一场云波诡诈的大战,仅仅一个人在指挥部坐镇,阮君烈感到不安,需要更多的策略支持。
还没等到阮君烈和共军交战,就在派出十五师的第二天,他得到警备师的加急信报,急报中称:叶鸿生率军反叛,举起赤旗,已经扫平山头,兵临城下。
阮君烈得到信报,好似五雷轰顶。
警备师的士兵一个个淌着汗,焦急地围绕着他,问:“怎么办?长官,怎么办?他们快要打来了!”
阮君烈将手中的军报捏皱,强自镇定下来,问:“七十三师哗变了?”
士兵们急忙点头,说:“是!昨天晚上发生兵变,没有人得到消息。今天早上,他们突袭了山上的守军,守军集体被俘。他们释放了一部分俘虏,我们才知道的!”
阮君烈问:“谁干的?是孙仲良吗?”
士兵们说:“是叶参谋。”
阮君烈说:“谁看见的?被俘虏的守军亲眼所见?”
士兵们沉默下来,面面相觑。一个胆子比较大的士兵上前一步,对阮君烈说:“长官,我们没看见,是听说的。”
阮君烈放开喉咙,骂道:“没看见你胡说什么!狗嘴吐不出象牙!”
阮君烈毒辣地咒骂这只出头鸟,眼中迸发出憎恶的火星。
士兵们六神无主,越发不知该怎么办。
这名大胆的士兵没有屈服,申辩道:“长官,只有叶参谋能指挥得动七十三师,旁人办不到!倘若你不信,叫下山的俘虏过来,问问他当时的情形。”
阮君烈立刻派人领一名败军的俘虏进门。
俘虏进来,不敢站立,对着阮君烈跪下来,说:“山上失守了,长官。”
阮君烈急切地问:“谁在指挥七十三师?你看见了吗?”
俘虏说:“是叶参谋。”
阮君烈太阳穴突突地跳起来,一阵刺痛,吼道:“你有没有看见?”
俘虏迟疑着,似乎在回忆。
阮君烈用手钳住他的肩膀,发狂地摇晃道:“你看见是谁指挥的?快告诉我!”
俘虏吓得连连求饶,士兵们急忙上前把阮君烈抱住,将他们隔开,让俘虏继续说。
俘虏道:“我不知道谁是指挥官,我没有看见。但是他们释放我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是叶参谋的命令……”
阮君烈晃动两下,终于站稳,问:“他们还有说什么?”
俘虏回忆道:“他们说,叶参谋交代,不肯投降的士兵可以下山,回来告诉司令。今天太阳落山之前,第十二集团军不投降的话,他们就要开炮轰击……”
阮君烈脸色阴沉得可怖,冷笑一声。
士兵们全部望着阮君烈。
阮君烈命令道:“做好迎击准备,把火炮摆出来。”
警备师的师长已经带人守备在镇外,传令兵去传令。
士兵们备好枪弹,去前方工事里。
阮君烈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楼,回到书房,关上门。
叶鸿生送给他的画还挂在墙上,像一个最最美好的谎言。阮君烈随手将画摘下来,扔在桌上。一个人呆着,阮君烈无需掩饰,他浑身的肌肉抖动起来,好像害了疟疾。阮君烈一手撑住桌子,让自己不至于倒下去,另一只手掩着面。
“我怎么会恨你?子然,我喜欢你,一时一刻也不会忘记你。不管你是否喜欢我,是否愿意饶了我。”
叶鸿生的话又回到阮君烈的耳畔,还有他春水一样表情。
阮君烈咬碎银牙,呼吸都烧起来。
那个时候,叶鸿生就露出反相,他已经想好了……
他是有预谋的。
他的行动那么迅速,干得那么漂亮!彻底!
阮君烈捉住画框,将它猛拍在桌角上。玻璃框瞬间被拍碎,清脆地响着,哗啦一声,碎成一地。阮君烈将扇面扯出来,将这幅该死的画撕成千条万缕。如果可以的话,他真想回到上一次见到叶鸿生的时刻,把叶鸿生彻底撕碎!让他的灵魂都碎成一片片渣滓,再也拼不到一起!
阮君烈将一捧纸屑扔在地上,将桌上的所有东西挥落下去。
当时他在做什么?
阮君烈自嘲地笑一声。他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