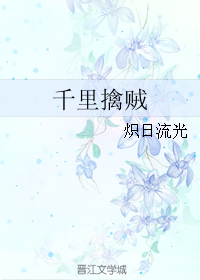送君千里-第5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叶鸿生有些惊讶,他意识到阮君烈的“退休”与自己的退休性质不同。就在同一年,台湾方面许可国军老兵回乡探亲。很显然,阮君烈的“退休”只是退居二线,他还在政坛上活动,有影响力,否则不会遭到这么严厉的抨击。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叶鸿生比金生更加丧气,他感觉到困难重重。半个世纪过去,黄埔军人们搞了两个同学会,像当年学校里的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军会一样各立山头,时不时互相斗嘴。青军会的干部们坐拥山河,吟咏“j□j”,已然心平气和;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到底意难平,火气不减当年。
阮君烈来大陆相对容易,叶鸿生去台湾难。像大陆的战犯名单一样,台湾也有个“罪人”名单,叶鸿生榜上有名。他单枪匹马,只要一上岸,能被人活埋。
金生得到的土地是一片山边的绿地,风水上佳。金生决定按照当年的祖宅样式,起一个阔大的宅子,里面有很多屋子,可以给他的子女、弟弟、侄子、侄女一起住。他找来匠人,准备种些花草,再建造一个马廊,养几匹小马。
金生跟叶鸿生讲,他准备到青海找马,育出良种带回来。
叶鸿生佩服他的精力。
金生豪言壮志,像只勤劳的老蜜蜂一样穿梭在A市与故乡,在废墟上重建昔日的家园。他梦想中的宅子尚未完工,灾难无声无息地降临。
噩耗传到叶鸿生耳朵,他难以置信。
金生去世了。
叶鸿生没有思想准备。金生是他们中间身体最好的一个。
叶鸿生背孙琳琳上楼,累得爬不完楼梯;金生提一包十多斤重的器材往家走,当锻炼身体。半路上,金生发现有人摸他钱包,举着文明棍追打小偷,赶出两条街去,同时高声叫骂。金生肺活量极大,心肌功能极好。他一向注重健康,又没有经过大的损耗,身体状态保持得很好。
叶鸿生赶到A市的时候,他生命垂危,宝铃和宝鼎在旁边泪水纵横。
原来,金生的孙子放假,住到爷爷家里。少年人好动,经常跑出去玩,去操场上踢球或者打球,每天回来很晚。有一天下雨了,雷电交加,他还没回来。金生特别爱这个孩子,怕他被雨淋,又怕他饿到,闲着没事自己找两把伞,带着一些卤鸭腿跑出门。天色昏暗,路又滑,金生走到一个三岔路口,被一辆横冲直闯的货车碰倒在地。
好心人去搀扶跌倒的老爷爷。
金生的肋骨折断,伤到他的肺部。痛苦中,他挣扎着说:“送我到第二人民医院!”
第二人民医院发现是老院长被撞伤,立刻派出最好的医生,把他送进ICU病房救治。金生一辈子倾尽心血的事业回报了他,帮他延缓两天的生命,得以见到亲人朋友。
金生留下遗言,对子女说:“不用难过。我要和你们奶奶在一起,我很高兴。”
金生昏迷一阵,安详地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医护人员想办法给他做心脏复苏,没有用处。金生七十岁了,不再是年轻人。他顽强的生命走到尽头,一梦化蝶。众人为阮君铭举办隆重的追悼会,医学界人士、他的病人、政协的朋友纷纷来参加,当地市政府派人治丧,原籍所在地发布唁电。
子女们决定把他安葬在故乡的新宅里,因为父亲已经把母亲的坟墓移过去,做好合灵准备。关于如何给他书写墓碑,他们意见不一。金生获得过许多头衔,写哪些上去,怎么写是个问题。他们找叶鸿生商量。
叶鸿生认为:“金生不在乎虚名,应该写他喜欢的东西。”
金生喜欢什么呢?难道不是悬壶济世?
叶鸿生认为,金生喜欢徐志摩的诗。年轻的时候,他喜爱阅读浪漫而激情的诗篇,还常常摘抄下来赠送给自己的妻子。
宝鼎和宝铃感到有道理。
盛宝莹去世,金生感伤于她的夭亡,在墓碑上写一句诗,写道:
“她不在这里,她在澹远的新月里。”
经过一番讨论,他们用白石给金生立碑,墓碑上面写道:
“他只有那一闪的星光,但是从不问宇宙的深浅。”
大家立在碑前,站在还没有来得及盖好的宅子跟前,伤心地哭泣。这个时刻,阮君烈按理应该出现,但是他没有出现,只有他的女儿来了。她叫阮幼香,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表哥和表姐,忧愁地诉说一番。
阮君烈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越发厉害,准备明年做手术。接到噩耗后,他病情严重恶化,当天晚上被推进台湾三军总医院,医生建议他尽快手术,不能再拖延。阮君烈的大儿子在军队任职,不能随便走动;小儿子在美国,要照顾父亲。美国的技术更成熟,台湾方面负责安排,让他去旧金山接受手术。
这么一来,只有他女儿可以出门。
宝鼎和宝铃听了,悲声更甚,决定去美国探亲,乘早去看望叔叔,以免来不及。
叶鸿生悲伤得没有力气,不幸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但是他没有权利去看望阮君烈。他甚至不敢去看,他害怕一见到自己,阮君烈会死得更快。
叶鸿生只好哀求阮宝铃,希望她把自己的信笺带上,等阮君烈好起来,再交给对方。
宝铃答应了。
叶鸿生提起笔,心中有千言万语,不知如何写才好,最后他写了一首《行行重行行》。
叶鸿生在信纸上写: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钢笔在纸上发出沙沙声,他脑海中想起阮君烈曾经的音容笑貌,一种岁月无法磨灭的爱意在心底哭泣。
他一边写一边回忆,写到“……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的时刻,叶鸿生停下笔,在窗前看一会月亮,把自己的痛苦收起来一些。
月亮依然像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五十年前一样白洁。他回到桌前,写上最后一句,表示不再多言赘语,希望阮君烈能保重身体。
第 78 章
冬季过去,燕燕于飞,衔春而来。
年复一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叶鸿生拎着菜篮,看桃花在枝头上绽放,嫩红轻蕊。孙琳琳放学了,她爸爸用自行车推着她,妈妈给她拎书包。孙琳琳看到爷爷,快活地叫一声,跳下来,朝他扑去。
叶鸿生把孙琳琳抱起来。小姑娘又变沉一些,他抱一会就放下来,牵着她的小手,往家走。叶鸿生买回好几条鲜鱼,准备做鱼腹包肉给孙琳琳吃。
他们到家后,在媳妇的帮助下,叶鸿生把鱼料理干净,把肉糜塞到鱼肚子里,撒上姜片,上锅蒸熟。等鱼蒸熟,鱼腹中的肉团浸润了汁水。叶鸿生把肉丸剥出来,放到孙琳琳碗里。
孙琳琳还小,不太会挑鱼刺。她嚼着鲜甜的肉团子,满意地扒饭。
叶鸿生想起来,阮君烈也很喜欢吃这个。
阮君烈喜食“长江三鲜”,尤其喜欢吃鲥鱼。鲥鱼珍贵,他们到彭乡之后,没那么些鲥鱼给人吃。阮君烈对平常的鱼没耐心,不爱挑刺,又爱鲜美的滋味,厨房就做这道菜给他吃。厨房把菜端上桌,阮君烈把肉丸和鱼肚子吃掉,叶鸿生把剩下的部分吃掉。
叶鸿生想着,回忆着,思绪跑出老远。
孙卫国往他碗里放一块鱼肉,将他惊动。
叶鸿生笑着,拿起筷子。
吃过饭,他同往常一样,去看电视。
冬天的时候,阮宝铃与哥哥从美国回来。宝铃告诉叶鸿生,阮君烈病情稳定,过一阵就能出院。叶鸿生松一口气,问:“交给他了吗?”
宝铃说:“给他了。”
叶鸿生忍不住问:“他有没有说什么?”
宝铃为难地说:“我临走前给他的……”
宝铃和宝鼎都有工作,请了十天的探亲假,不能没完没了。临别时刻,阮君烈手术成功,恢复得尚好。宝铃把信笺和其他礼物一起交给叔叔,与他告别。
叶鸿生流露出失望。
宝铃不安起来,说:“我下回问问他?”
叶鸿生忙说:“不用了。”
叶鸿生表示不要紧,信送到就好。
宝铃听父亲说过,叶叔叔和自己亲叔叔是一对仇人,从前在战场上打到绝交。她跟叔叔并不熟,不怎么敢问,而且她父亲叮嘱过“你叔叔跟共|产|党的恩怨,你们千万不要管!很危险!”除了家事,他们几乎不与阮君烈谈别的。
宝铃对叶鸿生有些愧疚,安慰道:“等房子盖好,叔叔回来探亲。大家就能经常见面了。”
面对她的天真,叶鸿生只是微笑,没有说话。
今天想起来阮君烈,叶鸿生又睡不着觉。他跑到阳台,窗户在风中策策鸣动。叶鸿生把窗户闭上,坐进藤椅。夜色将天空涂黑。晚上散步的人跑出来,热闹一阵,又全部散去,地面上恢复平静。
叶鸿生依然坐在阳台,目光投向窗外。
他看着夜色一层层加深,暮色浸染窗台,又看白昼一丝丝绽开,把光明带回来。随着夜色加深,他心中好像有几千重的痛苦,他不禁要问自己:这份感情好像无穷无尽的折磨,他还有没有必要继续下去?
阮君烈在叶鸿生心里分量很重,根本难以割舍,但是他真的累了……
叶鸿生噙着泪水,在黑夜中枯坐。直到白昼来临,他才释怀。
晨曦中,大地看起来饱经沧桑,时刻都在改变;而苍穹依然广阔,像千万年前一样,用雾霭环绕着地面。
叶鸿生望着天空。
天空可以拥抱大地,始终温柔地拥住它,即使它们相隔千万里的距离。
他当然可以继续爱阮君烈,并比以前爱得更深沉。
想通之后,叶鸿生恢复宁静,不再忧愁,也不再期盼阮君烈会有什么回应。他自动割舍了让他苦不堪言的一部分想法。
接下来的两年,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叶鸿生同其他j□j党员干部一样,受到极大震撼。政治力量重新排列组合,世界格局在洗牌,发出巨大的回声,余音袅袅。
阮宝铃准备到香港去,临走又在犹豫。金生一对儿女,儿子弃医从文,女儿继承了他的衣钵。阮宝铃是个医生,听她父亲的话,没有跟政治有任何瓜葛。但是这一次,她想举办一场医学交流活动,与会人士涉及两岸三地,还有国际友人参加,她把场地设在香港。
宝铃没有政治背景,很多事情不能顺利,她来找叶鸿生。
叶鸿生义不容辞,要监护她,陪金生的女儿出门。
在叶鸿生的帮助下,交流活动如期进行,在香港顺利闭幕。当叶鸿生出现在闭幕仪式上的时候,尽管他只是坐在台下拍手,依然引起新闻界极大的关注。新闻记者对叶鸿生的兴趣远远超过医学活动本身。
叶鸿生这类高级将领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同时他还是富有争议的人物,机不可失。记者都很想采访他,奈何进不去门,只有一个香港记者通过关卡,借着采访医学专家的名义,坐到前排。
记者打招呼:“叶老!”
叶鸿生回头,笑道:“你好。”
记者操着粤式普通话,热情地说:“你好久没有出门咯!第一次来香港?”
叶鸿生说:“是,我出门少。”
记者跟他谈论一番本地风物,忍不住话锋一转,说:“叶老,我看你很少说话。”
叶鸿生笑笑,投诚的国民‘党将领离开大陆,多半要说点什么。他们不说什么,台湾方面和搞j□j的人也要骂他们。他们一说话,不是剖白就是吵嘴,说好话就是统战。叶鸿生更麻烦,他很早就是中|共的一份子,但是很多人认为他是国民‘党将领。
记者毛遂自荐道:“在香港朋友多吗?想去哪里看看,我可以做向导。”
叶鸿生笑笑,说:“没什么朋友。我认识的人很多去台湾了。”
记者眼睛一亮,重复道:“叶老,你对国民‘党怎么看?”
叶鸿生笑起来,说:“我父亲就是国民‘党,参加过武昌起义,受伤退伍的。你说我怎么看?”
记者很想再问又不敢问,抓耳挠腮,又说:“你如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叶鸿生说:“我选择走更贴近人民的道路。我与他们又没有个人矛盾。”
记者拐弯抹角地问:“你对曾经的上级、同僚,有什么想法或看法吗?关于他们的失败。”
接到这个问题,叶鸿生沉默一会,神色变得柔和很多。
叶鸿生对他说:“除了孙先生之外,国军里面,我最尊重的人就是我的上司。我们只是信仰不同。”
记者对他的回答不满,指出:“可你亲自击败了他。”
叶鸿生苦笑着,回答道:“好吧。我击败了他,我辜负了曾经的兄弟,无论别人怎么看。我走红色道路,我相信共产主义。”
叶鸿生柔和了眼,又讲:“我有对不起朋友的地方,但我心里没有坏意思。前一阵子,我看着窗外,还看到燕子回来了……”
记者怔怔地望着他,被他的风格所震撼,扶一下眼镜。不管是j□j还是国民‘党,军队干部很少有人是这种风格,太感性了一点。他不知道叶鸿生想到阮君烈自然柔和下来,遇到旁人未必这样。
记者说:“这条道路……”
记者很想说:这条道路前景不妙的样子,你为什么不想着改?想往回走吗?
他虽然没讲,但是问题呼之欲出。
叶鸿生笑起来,坦率回答道:“我们党犯过严重错误,干扰了人民生活,对不起他们。由于党内宗派主义对立情绪,错判了很多同志。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不可能有群众基础,会坚持走新的道路。”
记者若有所思地走了,回去写了一篇报道。
叶鸿生想想,应该给中|央|军委汇报,以免引火烧身。
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此事还是引起党内议论,一些人认为他措辞太软,但是没有原则性问题,另一些人认为,叶鸿生不该对重大问题表态,缺乏军人的纪律性,尤其是不该“谄媚国民‘党”。他们认为“你走红色道路有什么好对不起的?这是为了正义!国民‘党犯下的过错不少,有谁出来跟你认罪?”
叶鸿生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