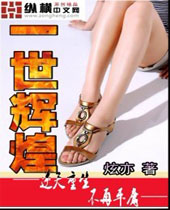һ��һ��-��1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Dz��ܣ����Dz��룬��Ψһ�Ķ��Ӹ������ˣ�������Ҫɱ�Ӳ�Ȼ����ɱ�����������Ҵ���˵�ͣ����ܸ����ӣ�ֻ�����ӳ������ٲ����£������Ҳ�����ײ��������ӣ�����ô����
�����׳���ͷ��ʾ���⣬�漴���ѵ������㲻�������ӣ�ȴ������Ů�����վ��������������Ⱑ����
���������ᣬ÷С���Ǹ���ƫִ�����ϵ����м��Ҳ�Ҫ��Ů�������DZ�ȫ�����ŷ����棬ͬʱҲ���ֹ��Ů��һ����Ը��������ʡ���Ҹ����鷳����
�����׳�Ц���ڽ����˵���һ�ڣ�����Ļ�����˼Ҳ���࣡��
���������ԲŲ���Ҫ�����˶��߱���������˼��ǿ�������У�ʡ��һ��ֻ�����ζ�����ǿ��̫���������ˣ���
����������Ұ���������Ѿ��ܹ����˺ðɣ����׳�˵�žͺ�������
�������ʲ�ͷ�����룬ҡͷ�����Ҳ���Ұ�ޣ���˵ʨ�ӽ���һ�γ��X��ʱ������ÿ�ξ���ʱ��������
��������˵�ˣ����׳����˵��ʵ��죬ָͷȴ�����ʺ�ס����ָ���������ֱ��С��������
�����������ˣ���÷Ů��һ�������׳��ŵ����뵥�ʵĻ�����ȴ�����������֣�һֱ���������ϡ�
����÷Ů���ij��ղҲ��̶ã����ϵ�����Ҳ���˲������ӣ��׳���������ҩ���������Դ�Ϊ������±�����÷Ů���ļ磬����ȥ�ɣ����������﷿Ѿͷ�����������߱�������������ƫ��С檣�֪��檵�ְ����ÿ��îʱ��������ҹ��֮����ϴ��ˮ������������ϴ����ٷ���������ʱ�Ⱥ������ĸ��ֵ��ѣ����ܸ����˴�����ܸ��������Ƿߣ�������ʮ��������㲡�������ƣ��Ȳ���ĸƾ�ӹ��һ�������������˽��������ο��أ���
����÷���³�����ͷ������һ����ɫ��ȭл����Ȼ���ܳ���ȥ�����ʸ������ӿɽ̵�Ŀ�����ͱ��������С�Ц�ö����ۣ���������§�ڻ���������ְ��ɻ�ʲô����ô��Ц����
�����׳�Ц���˲��ᴷ����һ�£���������˵Ц����֪����Ҳ��ϵþ���������֣�ص���ij�ֽǶ�����������ͦ��ģ���
����������Ȼ������û˵Ц����������������ģ���ϧ������û������檵����֣�����ʱ�Ű��꣬û�취���������ҿ��Ҷ��統ʱ���˻������ؽ�����˼����������үү�����ܣ�����үү�����ڹ���ijλ�����λ���������ʺ�����һ��Ҫ�Ҷ��������Ҵ��Ϊ�˱����Ҷ���Ͱ�����ң��Դ�����үү�����ϱ�˼�������쳣���ٺ����Ҷ�������ԩ������Ҳ�͵��˱���Ļ��ᣬ�����̲������ϳ�ʾ�˲�����үү��֤�ݣ�֮����үү��ն�ף����˽����ţ��������ң����Ƕ����ˣ��Ҹ����ﱨ�˳𡣡�
������������ƽ�������ڽ����������£��׳���Ǹ�ε��ᣬ���Ҳ�֪������������û�ģ��Բ��𡭡���
����������֮�䲻�õ�Ǹ��ֻ��������ˣ�������������ȥ����Ҳ�ϵ����������������Щ�����������Ժ��˴�����ͷ��ȥ����
�������ǣ����׳�ѧ÷Ů����ȭ������Ц��ȥ�˳��������ʸ������Ŀ�⣬�����DZ�����ѧϰ��ֵ����ȥ���¿���ѩ��С�����ű��������㣬������С�Ū���ij�����������С���֪����ѧ�����ܵ�С�������������ϵIJ���ͼ�棬��һ����ɫ���㣡
��������ʱ�����������ƣ��������˲��죬���Խӵ������Զ�ŵ���Ϣʱ�����ʺ���жְ��·����ͷ���׳��������˵Ļ�ϴ�·������ʸ����ˣ���������Ը�����һ���ˣ���
������һֱԸ��ģ�ֻ��Ϊ�˸���ͬ�У���������һ���¡����׳��۲쵥�ʵ���ɫ���ƺ�û�в����ˣ�����С��̹�ף��������Ұ�С����Ҷ���ˣ���˵��ԭ���ҵģ���������һ��Ҳ���ף����Ұ��������ģ���һ�������Ϳ��ܣ���������������������������ߣ�����������������ˣ�������Ҫ��Զ���չ˲���������������á�����
����������������Ҷ���ã��������ù����������߰ɣ���
�����׳���ͷ�����²鿴һ��Ÿ��ŵ��ʳ����ţ�ȥ��ݴ���Ҷ�������к���Ȼ��ǣ�����ǡ�
�����׳�����֪��Ҫȥ�Ķ�����ֻ֪������Ҫȥɱ�ˣ����ռ��̺��˷��ݣ��׳������е�ɱ��Ӧ�����ҹ�������ǵ��ʴ���ס���˹��䡣
���������������������룬����һ�Ӹ輧���ˣ����������������Ѳ�����ྴ������ʱ�����������������н����������������߲��ܣ����˽���ϻ�ӣ�§�˰׳�˯��ȥҲ���������������������
�������գ����ʴ��׳�������棬�����գ����ʴ��׳�������������������Ԫ�ڣ����ʲ������а��ţ����Ǹ��Ӱ׳�����Ը��������׳�ȥ��ɽ�����������������������ի����Żسǣ�������׳��źӵƣ��ص�������Ƕ����졣
�����׳��������ã�������ϴ�����˯������û�ϴ���������жԻ������ƺ������սӴ����ǵĸ���֮һ��ֻ��û�����յĺ���ɤ�ţ����ǵ��������������
�����׳����ҿ���͵���������������ϣ��������һ��ȴ����Ҫ�죬���Ǿ������ʣ�������˯��
�����������أ����Ⱥ�����˯�������������壬�׳�һ�¾������ۣ������У��ҽ���ի�䡭����
��������ի��ģ������ҵġ������ʰ���ѹ������������Ū��˭֪С��쳣��Խ������������������һ���⣬����ŭ��������Ҫ��ȴ���ڰ�գ�С���Ȼ���ˣ�����������㻹�ޣ���
�����׳�Ĩ���ݺݵ��ŵ��ʣ�������ŭ�ˣ�����˺�˰׳����·�����ϧ��û�����û�����£�ҧ�������С��õ���û�ޡ�
������˯�ɣ������ʳ������Ӻ��ҸǺã�������ȥ����С���������������ij�ҭ��Ҳ�����˵��ʵ��ģ��͵�ת����ȥ��С�§�����������ˣ���ֻ�Ǹ��˲���Ҫ�㣬�㲻�������ˣ������㣬��Ҳûǿ�����ˣ�������Ҫի��Ҳֻ����ͷ���أ�����������������
���������ʣ����׳�������ϣ��߷����ջ𣬡����̹��δ��ֱ̫���ˣ�ʱ����û�������ɻ䶼û�У������²���̨����Ц�Էǣ��������˵�Ҳ���ˣ�Ҫ�ǵ���Ȩ��С�������ǻ���������Ȼ��Щ�����㶼������Ҳ������ֵ���˼��ֻ�ǵ�����ΪС�������ֻ�����������죬���е����Ӧ�ԣ������ض�������Ҳ�ᵣ����ij�մ�©���������⣬������˵�����Ǽ��ˣ�����Ϊ����֮����˰����������Σ����öԷ��������ģ�Ҳ������֮һ����˵�أ���
������������˵���ˣ��һ�˵ʲô�������㵣��С��ʹ��������������죬�Ҹղ��Ѿ���С���Ծ����£������������������Ҿ�����һ�̣�����һ�����Ǿͻؼң��������ô��ֻ�����˵�����˵����Σ��������㣬Ϊʲô�����ң���
��������˵����ի�䣡���׳����յͺ�
����������ü������ի����֪����Ϊʲôի�䣬�Ҳ�֪������
��������Ȼ��Ϊ���ˣ����ռҼҼ����Ϸأ��������������»꣬ҲΪս��ɳ����Ӣ���̾���������ʲô�������ˣ�ֻ��ի�䣬���ꡭ����
�����׳����ʶ�ס����������һ����׳������ӣ��������ң���ʵ�����ң�������Ҫ��ȥ͵������ʱ������ʵ֪����Ҫ��ʲô����Ҳ֪���һ�������Ǽٱ�����������˵�������ǣ���Ϊ���������ʹ��������Լ�����������Ϊ������Щ��ʿի�䣬���𣿡�
�����׳�������յ��������Dz��ϵ��ᣬ�����Ѳ���Ҫ���ſ��׳���������ȥ����˯�ɣ������Ҳի�䡣��
�����׳��ںڰ��е�ͷ��Ȼ��Ҳ������ȥ��ͬ齶������������˵�һ�εֱ����ߡ�
�������գ�������˵����λ��Ա��Ȼ�Ծ��������ٴ�����Ϣʱ���׳��շ��³Ժõ��緹�룬������º׳���Щ����˼��ؿ��ŵ��ʣ�û�õ�Ŀ���Ӧ���׳��㲻�ҳ���ѯ�ʣ�ֻ����������Щ�����ˣ����ʲ���һ���ὣɱ�ˣ�˫���˵����������λ������ʵ������������Լ�Ҳ˵���ó�������˼��Ҳ����˵������ɱ�˵ķ���ǧ�������������
�����ѹ�С�Ǹ�粻ͨ��������ֻһ�ţ�����ȴ����ƫ�����Բ���ǿ��̫�࣬������ͼ�һص���������С�Ǹ�磬���ÿ���С�Ǹ��������ɣ���Ϊ�����ѱ���̫������������ߣ��������棬�����������˶�Ҫ�й��оأ��ڸ��ֳ����϶�Ҫ�������磬�Ǿ�ΨʣӢ����������·�ˡ���
������������Ҫ���ҵ���������ҲֻҪ�����ֽ�����Լ������������Ƨ���죬����ȴ���������ԣ���Ȼ�����������������ղ��⽵��ʱ����Ҳ����������ѣ������ң������������Ҷ�����ͬ�ڣ�
�����л�Ҫ˵������
������ڡ�22����
����������ǰ��˵�������Ծ��ĵڶ��죬���ʹ��Ű׳����������ݣ��ӷ��������Dz���ʱȴ����һ��С��������ʱ������һƬ���ֱ�ͣ�¡�
�����׳�����ѯ�ʣ�ֻ���ε��������������ߣ�����ʱ�㿴��һ�����㣬���Ͽ��顰˫��֮Ĺ����������̨�����½�����ĺۼ���
��������˫��������ɣ����׳��ૣ��ۿ���Ī�����͡�
�������ʲ������ḧ��������Ц����������Ϲ��ä�����ռ�����˫�ɵ������������Ҳ��������ŵ�ס��һ���������Ҵ����ҹ��̴����ݸ���������������ҹ�Ŵ��������������������ԭ��Ϊ�Ǹ�����������С����˭֪�Ǹ���������Ĵ���������
����������ô˵�����׳���ʮ���ۣ����Բ���˫�ᣬ���ʲ������㣬���������㲻���䣬��ʵ��Ҳ��ЩԹ�㣬��Ȼ�����������ɻҵİ��ˣ�������ͬ����ȴһ�еľ���������һ����û�õ����ʵ�ϲ��ʱ����Ҳ���������Ϊ���˵��ʣ���ֻ�����ˣ����Ǻ�������˫����Ҷ�������Ƕ����Ķ��Һã������Ҳ�����˽���ʧ�����������������Թ���ԭ��Ҳ�ǵ����������������ԭ���䲻�ң�ŭ�䲻�����ѣ����������������ŭ���棬ֻԸ��������٣�����ڤ������������������
�����׳��������ۣ�ȴ����һ����������ʶ���˵���һ�£������������ˣ�����ô����ʲô����
������������׳����°ͣ������Ȼ�������������Ȼ��Ϊ˫�ɺ�Ҷ����Ų��������أ���ѹ��û����Ұɣ�˫���������壬�����û��û�Σ�ȫ�������Ĺ������Dz��ǣ��ò����ҵ�ϲ�����ȥ��������Ϊ������˲��˹����������Ǹ������Ǹñ�����֣���
���������ģ���Ȼ��Ц�����ʲ���ؓ��˰׳�һ�£�������Ц���ֿ���Ц�����Ƿ�����������Ϊ��û�����֣������Ҷ����м��齭����ûȥ������ʱ���Ҿ��Ѿ��������ˣ���ֻ֪����Ȣ�������������ϱ�����뵱��ս������ȴ��֪��������Ҫ�����书�����Ҷ����ٲ����˴�����ҪŬ��һ����ɽ��������������ʳ���ǣ�������Ϊ�㲻���ˣ���˵Ϊ�������ģ��������������Ҷ�û�ܣ����Ϻ��������ĺ��ǣ��������Ҳ����㣬��ֻ����������»�Ȫ����֪�������أ�������Ϊ�Ҳ�ϲ���㣬���ȥ�����������Ĺ�����ʲô����Ϊ�㷢��ô����ķ�����ʲô��������ر�Ұ���ƵĻ�ñȹ�����������ʲô�������ޣ���
��������˫����ס�׳�������������Ĵָ�ݺ�Ĩȥ�׳����ᣬ�������������������ˣ���˵�Ҳ����ܲ�Ҫ�㣬����������ʧ�ķ�����������������������������㣬�㶼���Һúû��ţ��Ҷ������DZ����������о仰�����������Ų��������ܣ��⻰���㣬����ҿ�����������������ǣ���
��������˵�žͺݱ��˰׳�һ�£��յð׳�������Ϣ��ȴ�ð׳��Ҹ������ģ�����˰Ե��ݾ��ذ��ţ�˭���������У�������в��İ��
���������ֳ������ʸ�����������ۣ��׳����ΰ�ҧ�����棬����Ъ��ʱ�������������Ѫ������������ϴʱ�����ʿ�����Ȼ����ˤ�ų�ȥ���ܿ������ҩ����������������׳�ͿĨ���ַ������С�ġ�
�����׳�̹Ȼ���ܣ�Ϊ���Dz��������˭֪�����쳣��³�ذ����������ϣ����㲻������˵�˲�����㹴���ң������Ȼ�һ�����ܣ���ʲô��˼����
�������ҡ������׳����߳�ŭ�����Ҿ��ǹ�����Ҫ�������б�����������
���������������۵��ֲ����ң���
����������ˣ�����û��������ĥ�Ƶĵط�������ĥ����ײ���������µ����쳣���ͣ��ܰڳ��ü��ֲ������˴������ƣ��ߣ����㹴�������㲻��������������������������*��*��*����
�����ݻ����ĵף��������ж������µIJ��DZ��ˣ�������С�������һ��������С�Ǹ��ġ�����ϲ���ġ��������ġ���С���
������ҹʱ�̣��¾�����������û��������ϰ�ߣ���Ҳ���������������������׳�˯��̫���ϸ߲����������ڶ��굣�����µ�ϰ�ߣ�һ�¾���ֱ�ˣ�����ĥ�Ƶ��˴��Լ�ij������������ȻϮ�������ǰ����ˣ����ٻ����Ҹ����Σ�����������ÿ���糿������һ�С�
�������˿�ջ�ṩ�ķ�ʳ����������㻺�У����ʵ�ҩ�������׳����˴���Ͳ����ˣ�ֻ����Ȼ�������˲����ڵ�����ǰ����һƥ������ǣ�����У��ҿ���������·�ˣ�����׳����������ɣ�
����ֻ�в�������������Ů���Ż�������ϣ������Ǵӻ���·�ͻ������Ľ��ɹ����������ж�����
��������ô�ˣ�������ֻ�����һ�ʣ�Ȼ���˵����һ���£�������˫�ɣ�û��֪�������ʵ���ݣ�������λ��磬�Ҷ�û�������ǣ����֪��ԭ�ɣ���
�����׳���ͷ����������ɬ��������Ц������������Ĩ��Ƭ�μ��䣬��ϣ��˫���Ҳ��֪���ҵ����ݣ����������б��ʱ�㲻���ܵ�ǣ������֮������������Ϊ�˱������Ҷ����ġ���
�����������˰׳�һ�£������ڴ��ϣ����ʺ���������ǣ������һ�¼��Ǽν�Ҳ��Ǹ�⣬���������˸����DZ���֮�⣬�Ҷ��绹���˼��ţ�˵������㣬���һؾ��ˣ��Ժ�Ҳ��������������κ�һ����ԭ��ͬ�ϣ�Ҳ���ұ���Ӹ����ί����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