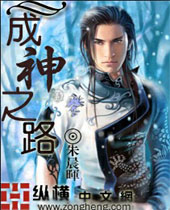闻香识妻路-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窝囊了。
“王爷,当年的事情虽然你也有错,但她本身就有问题,才会落得今日的下场。您就算是想赎罪,也没必要这么委屈自己。”
薛隐的脸须臾间风起云涌,“苏浅,你是想告诉本王,打断西门岸的腿虽然是本王的错,但他复原不了是他自己的问题,他的瘸是他应有的下场,是吗?”
苏浅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属下知错。”
薛隐厉声道:“自己去领二十军杖。”
“王爷……”
“再多说一句加十军杖。”
苏浅闭了嘴,摸着鼻子恭敬地退出去。
“我要见姚若麟。”
这是薛隐处理完公务回到王府,孟桐把她拦在梧桐轩外,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很显然,她是特地在这里等他。
薛隐头昏脑胀,挥手就说:“明日我就让高岭送他回京城。”
“你想让高岭送他的尸体回去吗?我听说他不肯进食,再这么下去,他会死的。”
薛隐挑眉,不悦地问:“你心疼?”
孟桐冷笑,“请允许我提醒您,姚若麟是您最爱女子的兄长,他们是一母所出,感情甚笃。他若是死了,到了九泉之下见到姚小九……”
薛隐受不了她的冷嘲热讽,厉声打断她,“我让苏浅带你过去。”
薛隐曾经下了命令,姚若麟一日不吃,高岭也休想吃饭。回来后不过是五日的光景,高岭已经和姚若麟干了无数次的架,不管她怎么打怎么骂,他就是不肯吃饭,打到最后他力竭倒地,高岭才强行灌了不少的米汤维持他的生命。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何一心求死呢?”赢的次数太多,高岭也觉得没意思,开始和姚若麟讲道理,“你想想啊,你是朝廷重臣,年少有为,想嫁给你的姑娘能从京城排到西南,你何苦喜欢那个孟桐呢?她贪慕虚荣,只想着荣华富贵,就算你们私奔了,她总有一天也会因为吃不了苦而离开你的。”
“不用你管。”姚若麟虚弱得连声音都发颤,“我要是死在西南,薛隐难辞其咎,杀害朝廷重臣可是重罪。”
“我真不明白,孟桐有什么好,能让你如此死心塌地地对她。”高岭自小就在军营长大,像是假小子一样骑马习武,对于男女之事她懵懵懂懂,虽已到了婚嫁之年,却没有敢上门提亲,她曾放言谁要是受得了她的拳头,她就嫁给谁,可至今没有人敢试。
“因为……”姚若麟冷冷地瞥了她一眼,似乎在鄙夷她的无知,“我愿意。”
高岭跳了起来,“你耍我!”
姚若麟干脆闭上眼睛,拒绝和她交谈,他真是受够了高岭像只苍蝇似的在耳边嗡嗡直叫。
“你就是欠揍!”
高岭抡起拳头就要打过去,被赶来的苏浅一把握住,“还打,再打出人命了。”
“殴打朝廷命臣可是重罪。”孟桐看到脸颊深陷的姚若麟,心如刀绞,“我不管薛隐对你下了何种命令,你都不该用如此粗暴的手段对待一位谦谦君子。”
姚若麟睁开双眼,唇边带着满足的笑意,“你来了。”
高岭受够了姚若麟的冷漠和白眼,从来没见到他展露如此惬意自在的笑容,气更是不打一处来,“姚若麟,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她是长平王的人。”
“是吗?”孟桐面无表情地扫过高岭那张气急败坏的脸,“你可曾知道,长平王若是不幸归天,我就不再是他的人。”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苏将军,麻烦你把她带出去,我和话要和姚侍郎单独说。”
高岭打不过苏浅,所以她很认命地自己走出去。没有高岭的喧哗,屋子里变得好安静,静得只剩下姚若麟粗重的呼吸声。
孟桐缓缓落座,“五哥,我方才说的话,你应该明白。”
“你要我做什么?”
孟桐轻哼,“薛隐是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你能做的就是好好地爱惜自己,回到京城去做你的礼部侍郎,步步高升,和那些反对薛隐的人为伍,给他制造一些麻烦,好让他放了我。”
“你的意思是,要杀了他?”
孟桐摇头,“他还没有十恶不赦的地步。他虽有错,但错在他爱上不爱他的人,说到底他也是可怜之人。找些不利于他的证据和他做交易,让他放了我就好。”
作者有话要说:
为毛都不喜欢老薛呢,多耿直的汉子啊。。。。
第28章 第九章(2)
由于连日的绝食,姚若麟在交州的第一餐只有熬烂的米粥。他对食物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似乎只是为了生存的本能而进食。他吃得很慢,动作舒缓,小口慢咽,有着属于百年门第特有的优雅举止,丝毫不见这几日来与高岭剑拔弩张的粗暴之气。
高岭非常的不服气,气冲冲地踹门进来,“姚若麟,孟桐到底对你说了什么,你怎么不绝食了?”
姚若麟依旧缓慢地进食,“爱一个人要活着才能爱,我若是死了,还如何去爱她?岂不是便宜了薛隐。”
“你到底想怎么样?”
他抬眸,属于世家子弟轻佻的笑容回到他的脸上,“自然是比你的薛隐哥哥活得更久一些。”
高岭的脸色陡然一变,从袖中抽出一把寒光凛凛的匕首,“你信不信我会先杀了你?”
姚若麟不为所动地点头,“我信。但是,你得陪我一起死。”
高岭握刀的手收紧,抬步就要往前,可那个男人依旧专注于他面前的粥,动作缓慢而优雅。他的侧颜是高岭见过最完美的线条,相比薛隐的冷硬,他更驱于柔和,像是浓雾弥漫的山峦,每一道线条都被浸润打磨,那份美好让人不忍等到云开雾散。
高岭移开目光,小心翼翼地问道:“姚若麟,除了孟桐,你不会再爱别人了吗?”
姚若麟沉默半晌,直至他把碗里的粥吃完,才回道:“或许吧。”
高岭若有所思地轻噘起唇,“既然如此,我要禀告薛隐哥哥,让我到京城监视你,以免你做出什么缺德事来。”
见过姚若麟之后,孟桐回到梧桐轩,彼时夕阳正好,斜影疏朗,她搬了一方竹摇椅置于树下,静静地享受这份偷来的静谧。
姚若麟是聪明人,他总有一日会对现实低头。她不是真的想让他与薛隐为敌,而是给他活下去的希望。姚家这两兄弟都太感情用事,他们把自身的感受看得比家族和名利还来得重,若她再对他说决绝的话,只怕他会更加地极端,此时只能剑走偏锋。希望有一日,姚若麟意识到他不可能是薛隐的对手,知难而退,亦或者他找到另一个让他心动的女子,而把她当成一场不诉离殇的回忆。从姚府退婚起,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夫妻,不是姚家不能回头再议亲事,而是孟谦的骄傲不允许他最珍视的女儿被人如此糟贱,且不说姚孟两家如今是政治上的死敌。
她不是那种怀抱不切实际的希望过活的人,寄希望于薛隐被人弄死,还不如脱光衣服往薛隐的床上钻来得更容易一些。
三年前,她认为薛隐不过是一介鲁莽武夫,显然是错误的判断。他能带领二十万的薛家军从漠北到西南,并悄无声息地渡过漫长的三年,根本就不是一个鲁莽武夫能做到的事情。今上在这些年里赐下多少绝色女子,都被他一一赐于部将为妻,从此消声匿迹,再无任何消息传回京师。此一路行不通。孟谦又收买了不少流民回到故乡,原意是从中作梗,煽动百姓对付薛隐,令他重建西南的计划搁置。可依旧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回到故乡的流民都不再离开,没有人愿意为朝廷卖命。是以,当今朝堂对这个重建后的西南以及二十万薛家军的动向非常的好奇,皆因当年薛隐拒绝朝廷的援助,一力承担重建的银两和全体薛家军的军饷,朝廷自从再无过问的权利。
现下,西南的重建业已完成,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物产,宜人的气候,都让这一片曾经被水患困扰的土地重建生机。世人只知道这里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而关于薛隐和薛家军的一切却已成谜。
而她如今正身处于这个谜团的中央,并且有可能与这个看似简单却琢磨不透的男人共渡一生。她真的有些后悔,在京城随便找个男人嫁了,也比和薛隐朝夕相对要来得轻松许多。
今日的晚食是用各色香木和药膳烹调的香食,刚端起院中,就已经能闻到满溢的花草之气。
孟桐昏睡一天一夜的消息已经传遍长平王府,华太妃探视过几次,但因为春日湿气太重,行走困难,而不得不让离春来回打听消息,听到孟桐已经安然无恙,她才安了心。午后,她去太妃处请安,说起她研制的香食,太妃兴致甚高。于是,孟桐就让沉香和松香亲自下厨,备下这一桌的香食,回报太妃多年的爱护之情,也顺便请了西门岸,酬谢他救命之恩。
关于孟桐因何昏睡,薛隐下了封口令,府中上下皆有不同的猜测,有的说是因为初夜承欢,有的说是因为孟桐自不量力触怒薛隐,被崇尚武力的王爷打昏了,而不管是哪一种猜测不外是闺房的那些事儿,隐秘而暧昧。
但是华太妃无疑是最高兴的一人,因为薛隐总算是开了窍,破天荒地搬到梧桐轩,估摸着抱孙有望。抱孙这件事是华太妃的心病,她和华太后争了一辈子,可人家的儿子是皇帝,薛隐的本事再大也是臣子。今上大婚已经六年,东宫至今仍无所出,急煞了朝中大臣,华太后不知选了多少美貌女子进宫,可东宫依旧专宠椒房,无人能撼动其皇后之位。从孟桐来了之后,华太妃就把全部的心思放到抱孙这件大事上,倘若能比华太后早抱孙子,她就算是死了也能笑着阖上双眼。
“来,桐儿,多吃一点,你太瘦了,这样下去不行。”华太妃的心思都放在孟桐身上,“身子太弱不易受孕。”
孟桐尴尬地陪着笑,“义母,我……”
“别不好意思,你是隐儿第一个收进房的妾……”华太妃顿了顿,“虽然是妾,但他没有正妃,你若是生下薛家长孙,这长平王府还不是你说了算。”
“义母,我才到西南,等过些时日再说。”
华太妃想想也对,“新婚燕尔,耳鬓厮磨,我不该催得太急。倒是岸儿啊,你时常过来给桐儿把把脉,开些调理的方子,她看着太瘦了。”
“华姨说得是,我会时常过来的。”西门岸礼貌地陪礼,“倒是华姨的腿,不宜经常走动。”
“我这老太婆自然要听大夫的,才能抱上长孙。”华太妃扶着离春的手起身,“我吃好了,你们聊着。”
华太妃走后,孟桐命人撤去菜肴,沏了一壶消食的普洱上来。
“先生,请。”
西门岸端起茶碗抿了一口,“我听说夫人是孟相府上的千金。”
孟桐不禁讶道:“我曾与先生说过,难道先生三年前不是到孟府求助的吗?”
“这个……”西门岸目光飘浮,“在下对朝廷之事向来没有关注,并不知道夫人所说的孟府是哪家府上,是以当年我找的是薛隐去救夫人,难道夫人没有看到薛家军的令旗吗?”
“原来如此。”孟桐不疑有他,“怪不得这些年来,我送到府上的礼物都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来。”
西门岸道:“内子善妒,不敢收旁的女子所赠之物。”
“先生爱妻之心,孟桐有愧。”孟桐突然想起西门岸之妻已经病故,歉然道:“先生,节哀。”
西门岸摆摆手,“我娶她时,她已有恙在身。都怪我这只腿不争气,让她家里家外地奔波,以至于病情加重。”
孟桐见过他行走的样子,有时与常人无异,有时步履蹒跚,颇为艰难,“先生的腿何故如此?”
西门岸忙道:“此事说来话长。”
“孟桐愿闻其详。”
西门岸放下茶碗,目光投向帷帷夜空,新月如钩,皎洁似水。
“我幼时随父亲在军中长大。”他开始娓娓道来,“他治病救人,我骑马习武,舞枪弄棍,对西门家世代相传的医术并无多大的兴趣,父亲也就随了我。我有一个兄长叫西门堤,他的医术精湛,被祖父钦定为西门家的传人,而不是长子长孙的我也就没有太过严格的要求。岂料,十三岁那年,兄长上山采药滚落山崖而亡,身为嫡次子的我不得不弃武习医,回京潜修医术。”
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随性而为的次子,继承家业的长子,但总是会有不幸发生,不受拘束的次子变成长子,责任随之而来。
“就在我要回京的那一日,我的玩伴,也是我最好的兄弟,把我踹下马,打断了我的腿。”
孟桐吃了一惊,“为何?”
“因为我背叛了曾经的誓约,我们曾经说过要一起上阵杀敌,一起戌边守土,然后一起马革裹尸,同看长河落日。可是我违背誓言,在他眼中就是背叛,他不能容忍这样的遗弃。”
“后来呢?”
“后来?”西门岸苦笑,“我也有我的责任,我就算是爬着也要爬回来。他等着我服软,眼睁睁地看着我错过医治的最好时机,直到我昏过去,他还是固执地不肯让我医治。最后我变成了瘸子,再也不能骑马,不能练武,他才放过我。”
“你和你的朋友一定是很好的兄弟,所以他才不能忍受你的离去。”孟桐虽然不能认同这种残忍的行为,但是她能理解那个人的心情,因为太孤独了,想要有一个人陪,这么多年她也是如此,只可惜她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忙有没有时间交付真心。
西门岸似乎不想深谈,“或许吧。”
“那个人呢?他现下何处?”
“他……”
“是我。”薛隐从阴影处走了出来,负手而立,目若朗星,身姿挺拔。
孟桐突然沉默,心想自己竟然会同情他。
“时辰不早了,我也该走了。”西门岸起身告辞。
“西门先生的故事似乎还没有说完呢。”薛隐大步流星,须臾间已经在孟桐对面落座。
“已经说完了。”
西门岸扶着病腿,一瘸一拐地走远,只剩下相对无言的两个人,共享一轮明月。
“你认为自己错了吗?”孟桐幽幽地开口。
薛隐说:“我只能尽力弥补。”
“倘若弥补不了呢?”
“所以我说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