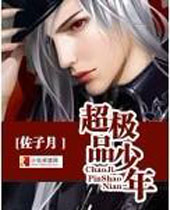陛下的藏品-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才刚蹲下,身后就传来另一把声音,声线不同,语调倒是一模一样的。
“霍克特先生,游泳虽然是一项不错的运动,但是身体欠佳时,还是不要进行的为好。” 侍从在身后一板一眼的说道。
又来了。
霍克特按了按太阳穴。
其实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不是一回两回了。在他还只能如同蜗牛一般在屋子里到处磨蹭时,感觉还不太强烈,状况稍微好转一些,他可以自如走动后,这些侍从就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他跟前,而且他们的说辞惊人的相似——霍克特先生你不能做这个,再不然就是霍克特先生你不能做那个——老天知道把这些都刨除后,他还能做点什么。
就好比说游泳吧,就算他立马跳进这个泳池里又会怎么样呢?他是会淹死在这不足三米深的游泳池里吗?
霍克特有点哭笑不得。
事实上,无论是花园散步,还是泳池游泳,他都谈不上多有兴趣,前者有点乏味,至于后者,相对于他之前的游泳经历而言,太过平常了,毕竟他曾游泳的地方不是冰冷潮湿的地下河道,就是拥有什么危险动物的热带湖泊。
游泳池,还真的就跟玩具一样。
霍克特蹲在那儿叹气,侍从则动也不动的站在他身后,两人僵持过半分钟后,霍克特站起了身。他放弃了向这位侍从描述一下他曾经在身中两枪的情况下横渡了一整个海峡的念头——别说是一个海峡,即便那是一整片大海,也不会让身后这位忠诚的侍从走开的。
在这栋别墅里的仆人,只听“某人”的命令,这点他还是清楚的。
所以,霍克特还能怎么办呢?他只好回屋子里去了。他让仆人给他拿一瓶威士忌,自己则走到客厅沙发旁,把自己甩进去后,两条腿交叠着搁到茶几上。
仆人去的时间有点久,久到霍克特觉出一点困意。于是他把牛仔帽拖下来盖到脸上,刚闭上眼睛一会,就听到有脚步声朝这边过来了,不过来的人不是先前领命而去的女仆,而是兰帕特。
兰帕特半弯下腰,把手里的托盘递到霍克特面前。托盘最中央是一只精美的白瓷杯,杯沿上烫着细腻的玫瑰金线,而杯子里——霍克特盯着它看了三秒钟。
“……这是什么?”
“霍克特先生,这是牛奶。”
“……我的威士忌呢?”
“我恐怕不会有威士忌了,霍克特先生。”兰帕特毕恭毕敬的回答,他把牛奶放到茶几上,再毕恭毕敬的鞠一个躬:“请趁热饮用。”
“……”
见你个鬼的趁热饮用!
这下,我们的霍克特先生终于不干了,如果说之前那些他还不是太在乎的话,那么擅自更改他的饮料表单,把威士忌换作牛奶这种匪夷所思的事,就委实太出乎他的接受范围了。以一种尽量不会捏碎它的别扭姿势,他拿起牛奶杯,从一楼笔直往四楼走去。
第五十九章
四楼,洒满阳光的房间内,“某人”正在听音乐,流水般的钢琴声倾泻在各个角落,他斜斜的倚靠在宽大沙发上,单手撑着下颚,双眼微闭。阳光落在他暗红色的长发上,泛出的光泽明亮耀目,几近透明一般。
而在他的手边,细长弧形杯中的红葡萄酒,就像颜色纯澈的宝石。
哈!
霍克特挑起一边的眉毛,同样身为病患,他得说,他们两人的待遇可真是太不公平了。
他走过去,长毛地毯完全消去了他的脚步声,卡俄斯也并没有睁眼,仍然一副要听不听的模样,却在霍克特走近他时,唇角勾出半个微笑的弧度。
他就知道,这人类会要憋不住,来找他理论的。
他睁开眼,正对上霍克特递到他面前的牛奶杯。他不以为意,伸手取过那杯子,凑到自己唇边喝了一口。这其实是一杯相当美味的牛奶,醇厚香浓,温度刚好。
“我觉得味道还算不错,你说呢人类?”
“我想我更宁愿要一杯酒,陛下。”
“这恐怕暂时不行——不过我想,你迟早会习惯的,你说是不是?”
霍克特终于觉得有点头疼了,到底是什么让这家伙以为,他会习惯这种软绵绵丝毫抓不住口感和味道的东西呢?
把霍克特既烦恼又困惑的表情看见眼里,卡俄斯唇边的笑意渐渐加深,他拉住他的手,示意他坐到沙发上。接着他举起牛奶杯,再喝上一口,凑过去,覆盖上他的嘴唇。
唔。
意识到卡俄斯的意图,霍克特想要躲,可惜有点太晚,硬生生的被灌进了一口牛奶,温滑的液体瞬时流淌过舌尖——比起水,要厚实的多,但是又说不清究竟厚实在哪,这种不确切的有点诡异的感觉,令霍克特僵硬了好一会。
他无力的向后仰躺进沙发里,彻底放弃了。
算了,随你高兴吧。
“怎么了?没精打采的样子。”卡俄斯把牛奶杯放到酒杯旁。
“原来陛下看的出我没精打采。”
卡俄斯禁不住微笑,他伸出手,半带安抚的摸一摸霍克特的下颚。
“再过几天,我就把你的枪还你。”
是的是的,自从霍克特睁开眼,意识清醒以后,他就发现自己的枪不见了,不仅是他的枪,所有武器都被从他的视线范围里拿开,恨不得连叉子都给他一把塑料制的。对此,卡俄斯的说法是:“在你的手能安稳的拿住一只餐盘以后,我会把它们都还给你的。”
这话霍克特觉得一点都不客观。毕竟,你看,他现在不仅能拿起一只餐盘,甚至他的手还能稳定的,咳,做某些运动——这一点卡俄斯亲身体会过,应该能够明白才是,可是他的枪仍然毫无下落。
没有了枪、又不被允许接触其他武器的霍克特,无聊到几乎无法可想,他甚至都为此愿意去进行花园散步了——当然,还是被阻止了就是了。
“再过几天,陛下愿意把枪还我?”霍克特问的有气无力。
“这就要看你自己了,人类。你看,如果你的恢复情况足够理想,我当然是愿意随时把它们还给你的。”
又在骗人了。所谓的“足够理想”,还不是这家伙说了算?
虽然这样想,但我们的霍克特先生还能怎么办呢?他最多只能凑过去,吻住他的嘴唇用牙齿咬一咬,当然,这样毫无杀伤力的泄愤举动,除了让卡俄斯笑意加深外,没有半点实际作用。
——不过,好吧,兴许还是有一些的。
“既然你这么急着想要恢复身体,你知道,我总是乐意配合的。”说着,卡俄斯伸手就要去碰他的脖子。
“……谢了陛下,其实我忽然觉得暂时没有武器的日子也挺好的。”霍克特忙不迭的往后一退。
卡俄斯终于笑出声来,他倾过身,亲一亲他的唇角:“好了,别这么担心,精神交融一天最多只能两次,否则作为人类的你会撑不住的。”
霍克特的眉毛抽搐一下,是啊是啊,真该多谢自己人类的“孱弱”体质。他顺着卡俄斯的意思,半躺过去,把头搁到他的大腿上,自己的两条长腿则顺势翘到沙发扶手上。
房间里,钢琴声还在继续,旋律优美,节奏舒缓,只可惜两位听众,一位先前就已要听不听,现在大半的心神更是不知飞去了哪里,至于另一位则是自从踏进这房间起就没注意过音乐声,至于现在么,有了这么舒服的躺卧姿势,他更是已经半只脚踏入了梦乡里。
他没滋没味的听着流淌在耳边的旋律,毫不感兴趣的挑挑眉,什么音乐,在他听来远远不如——
“那回,你给我唱的那首歌是什么?”他模糊的开口,整句话几乎都含在嘴里,“就是在死灵部队的那首。”
“那是一支歌谣,很古老,写给一朵玫瑰的。”
“玫瑰?”
“啊,是的,玫瑰——喜欢么?”
霍克特点点头。
于是播放的钢琴声中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空灵而柔情的旋律。随着这近乎耳语的吟唱,卡俄斯俯下身,两人的嘴唇若有似无的轻触,有时接触的稍深了一些,偶尔的几个音节,便透出几分模糊。霍克特被他这样轻吻了几次,只觉得嘴唇丝丝发痒,他索性伸手勾住卡俄斯的脖颈,把他扯下来,咬住他的嘴唇重重的亲吻过去,把嘴唇上的痒意磨蹭掉,顺便也把最后的几个音节吞进了嘴里。
“是朵什么样的玫瑰?”他可有可无的问。
“那其实是个传说,”卡俄斯略退开一些,“——在克罗那大陆上,很久以前有一个人,他十分喜爱玫瑰,他的花园里除了玫瑰,没有其他任何的花朵。然后有一天,他的花园里一朵最美的玫瑰盛开了,他爱上了那朵玫瑰,无法自拔。他用自己的血肉灌溉它,并在最后,连同自己的灵魂,一并献上。”
霍克特顿了几秒钟。
“听上去——有点血腥?”他有点犹豫的开口。
血腥……
卡俄斯不由的笑了:“我宁愿你将它称之为浪漫,人类。”
浪、浪漫吗?
霍克特仔细的把故事再回想一遍,实在没有看出它和浪漫之间的关系——不过,话说回来,他对于浪漫也不太了解就是了,这两个字比起卡俄斯的非科学力量好理解不了多少,甚至在说这两个字时,他还得注意别咬到自己的舌头。
还是换个话题吧,霍克特困扰的想。他的目光无意识的往旁边偏开,正落在卡俄斯的衣领处。卡俄斯今天穿着一件黑色衬衫,领口下开着三颗纽扣,袒露出精致凹陷的锁骨,和锁骨下方几许浓烈的暗红色。
霍克特顿了顿。
“陛下。”
“嗯?”
“德曼——我是说那个人,克罗那大陆上的那个,是叫德曼吧?”
“的确,不过你突然提起他做什么呢?”
这可不是个令人感到愉快的话题,比起与霍克特谈论什么德曼,卡俄斯倒更宁愿他能闭上眼,好好休息一会,这人类的身体虽然已经恢复不少,但与他之前的状态仍相差的太多。
霍克特显然没能接收到卡俄斯的想法,他正在整理自己脑袋里的思绪。
“不,没什么……”他边想边说,“我只是有点疑惑,我是说——他当初为什么要费那么多功夫封印你?”
霍克特也是突然想起来的,毕竟在克罗那大陆上,有这么好用的印记,那个叫德曼的完全可以这样做,何必非要费那种功夫做什么封印呢?而且就霍克特所掌握的为数不多的信息来看,比起将卡俄斯封印在看不见的地方,印记也应该更为符合德曼的心思。
——当然,对霍克特而言,“封印”这两个字,与“印记”同等诡异就是了。
卡俄斯则半叹了口气,他不是不知道这人类对印记没有半点兴趣,却不知道直到了今天,他脑子里的概念仍然如此模糊。
“你以为印记是什么呢,人类?随随便便就可以画在对方胸膛上的油印吗?我恐怕它可实在不如你想象中的这么容易。印记可以被订立的前提,唯有其中一方的意志被彻底摧毁,却仍然还有强烈的存活欲念,印记才会成功——而这一状态,并不能由本人自我控制。”
“德曼虽然蠢笨,不过还没蠢到如此地步,他至少知道什么是有可能的,而什么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的事。”
的确。
抬起手指,霍克特勾上一缕卡俄斯用墨色发带绑缚住的长发,要摧毁这个克罗那人的意志,还不如摧毁这个世界来的更容易一些。
但是这样说起来的话……
“那么,你为什么会和我订立印记?”霍克特禁不住问道,“我记得你以前曾经说过,你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印记是什么时候的事——真的一点印象也没有?”
卡俄斯的眼中,露出几分沉思。
自从来到这个低等空间,大多数的时间,他都是在沉睡的。与这人类之间的印记,他确实没有太过明确的记忆,不过硬要说的话,也许他不是一点点印象都没有。
“情感。”红唇掀开,他说了这么两个字。
“什么?”霍克特一怔。
“很强烈的情感。”卡俄斯垂下视线,拨开他额前的头发,露出他的额头,“它向我索求一些东西。”
“索求什么?”
“力量。”
“……力量?”霍克特的眉心打了个结。
“是的,摧毁一切的力量。”
那感情是如此的强烈,强烈到暂时唤醒了他,它愤怒而又悲伤,如一把利剑笔直插入他的心底。
它在哀鸣。
他想他当时或许是被震慑到了的,所以他在意识朦胧中做了一些允许——现在想起来,他那离完全清醒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的脑袋并不确定自己允许了一些什么,不过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来,应该就是这个印记了。
手里的长发柔韧又泛着潋滟的光泽,霍克特把它们在指间里绕出十八道弯,松开几道,再绕上。其实卡俄斯说的这些,他完全没有线索。真正说起来,他的记忆分成两半,后面的那一半,像个没有标签的垃圾桶,里面的东西删删减减的连他自己都连贯不起来。
至于前面的那一半,他则完全记不起来了。
他只记得自己睁开眼时,看见的军事医院天花板,还有他自己的名字。他们说他昏迷了三年,可是那三年之前的事,没人可以告诉他。
都是空白。
不出声的叹一口气,卡俄斯交叠起双腿,垫高了霍克特搁在他腿上的头颅,他用指腹抚摸过霍克特的额头,再细细的抚摸过额角,然后他的嘴唇代替了手指,在那里轻轻吻一下。
霍克特则散开了卡俄斯的头发,在发带飘落的同时,凉滑的发丝也漫上了他的指尖。他抚入那些发丝里,慢慢的,他说。
“我想给文森打个电话,你有能直接联络到他的方法吗?”
巴美尔帝国军事大楼的办公室内,文森正坐在办公桌后。窗外已是暮色沉沉,他却坐在那里,如同一尊雕像。就在几分钟前,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没有说他是谁,只给了他一个坐标。
“你如果有空,可以去那里看看。带上杜松子酒。”
“——什么意思?”
“去查一下死灵部队,你会明白的。”
对方挂断了电话。这更像是一个恶作剧电话,假如文森听不出他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