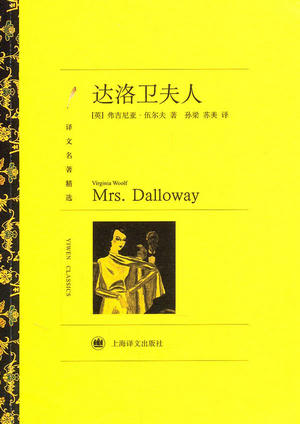达洛维夫人-达洛卫夫人-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必须向全世界宣布,赛普蒂默斯举起了手(当穿灰衣服的死者向他走近时),大声呐喊,恰如一个巨人,多年来独自在沙漠里悲叹人类的命运,双手压住前额,面颊上刻着一道道绝望的皱纹;眼下他却望见沙漠的边缘闪现光明,光点越来越大,照射那黑憧憧的鬼影(赛普蒂默斯从椅子上欠身而起),他背后匍伏着千百万人,而他,这巨人般的哀悼者,在一瞬间,露出大慈大悲的脸容……
“我苦恼极了,赛普蒂默斯,”雷西娅说,试图让他坐下。
千百万人在哀伤,千百年来众生都在悲痛。他要转过身去,片刻之后,只要再过片刻,他就会告诉人们这种慰藉,这种欢欣,这一惊人的启示……
“几点钟了,赛普蒂默斯?”雷西娅又问:“几点了?”
他却自言自语,他显得惊慌失措。那陌生人肯定会注意到他的举动,他在盯着他俩呢。
“我会告诉你时间的,”赛普蒂默斯带着神秘的微笑,缓慢而困倦地对穿灰衣服的死者说。他含笑坐在椅上,当下,钟声敲响了:一刻钟——十二点差一刻了。
彼得·沃尔什从他们身旁走过,心想,年轻人就是这样嘛,早晨刚过去一半便吵得这么凶——那位可怜的姑娘看上去心灰意懒,可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心中纳闷。那个穿大衣的青年跟她说了些什么,使她的脸色变得那么难看?在这样美好的夏日早晨,两人却都显得那么沮丧而绝望,他们卷入了什么难以摆脱的困境呢?有趣的是,阔别五年重返英伦,一切都变得新鲜了,好像他以前从未见过似的;无论如何,回国最初的几天里总有这种感觉:恋人们在树下口角,公园里弥漫着家庭生活的气息,伦敦从未如此迷人——向远处眺望,景色柔和、丰美、翠绿,一派文明的气象;从印度归来,这一切显得分外魅人;他在草地上边漫步边沉思。
毫无疑问,这样敏感是他失败的原因。在他这把年纪,却还像个少女,易于情绪波动,莫名其妙地时而欢乐,时而颓丧,看见漂亮的面孔便会感到幸福,看到一个丑女人就会痛苦不堪。诚然,在印度住过后,碰到每个女人,他都会倾心。她们身上散发出一种朝气,即便最穷的女人也肯定比五年前穿戴得整齐多了;在他看来,当前流行的时装式样最惬意了:长幅的黑斗篷,纤细的身材,优雅的姿态;而且,人人显然都有化妆的习惯,真令人心醉呀。每个女人,甚至最受尊敬的女人,都有温室内玫瑰般的面颊,殷红的嘴唇,好似被刀子割过似的,加上黑色鬈发,处处都显示出艺术加工;无疑地,国内发生了一种什么变化。青年们在想些什么呢?彼得·沃尔什思索着。
他揣想,那五个年头——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在某种程度上是关键的五年,人们变得异样了,报纸也和过去不同了;譬如,现在竟有人在一张正经的周报上公然谈论厕所。要是在十年之前,绝对不允许——这样公开地在有名的周报上谈论厕所。还有,在大庭广众之间,竟然掏出口红或粉扑,涂脂抹粉起来。在回国途中,船上有许多青年男女——他特别记得贝蒂和伯第——居然当众打情骂俏;年迈的母亲却兀自坐在一旁打毛线,看在眼里无动于衷。那姑娘竟会当着大家的面,在鼻子上扑粉哩;况且他们并未订婚,只是逢场作戏,双方都不伤感情。那个叫贝蒂什么的,真够老练呐;不过,在他看来,不失为一个好姑娘。到她三十岁的时候,她会成为好妻子的——在适当的时机她会嫁人,嫁给某个阔佬,住在曼彻斯特(46)附近的一所大厦里。
是谁这样做了呢?彼得·沃尔什思量着,拐弯走到大路上——是谁嫁了个有钱人,住在曼彻斯特附近的一所大厦里?那人最近给他写了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大谈了一通“蓝色的绣球花”。她是看到了蓝色绣球花才想起他和往事的——噢,当然是萨利·赛顿喽!是她——那个任性、大胆、浪漫的萨利!无论谁也想不到她竟会嫁给一个阔佬,去住在曼彻斯特附近的一所大厦里。
但是,在过去的那些人中间,在克拉丽莎的那些朋友中间——惠特布雷德·金德斯利一家、坎宁安一家,以及金洛克·琼斯一家——萨利可算凤毛麟角。不管怎么说,她试图从正确的角度去看待人事,她总算看透了休·惠特布雷德的为人——那位令人钦佩的休——当时,克拉丽莎和其余的人都对他五体投地哩。
“惠特布雷德一家吗?”她的话好像仍在彼得耳边回响。“他们是干什么的?煤商,可尊敬的生意人。”
由于某种缘故,她厌恶休的为人。她说,休只想到自己的外貌。他应该是个公爵,那么他必定会娶个公主呢。诚然,在彼得认识的人中间,休对英国贵族怀有最特殊的、最本能的、最崇高的敬意,甚至克拉丽莎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喔,不过他真是个好人呀,那么忘我,为了母亲的欢心而放弃打猎——还记得她姨妈的生日,等等。
说句公道话,萨利没有被这一切蒙骗。有一件事彼得记忆犹新。那是个星期天上午,他们在布尔顿争论女权问题(那个老问题),当下萨利勃然大怒,指责休代表英国中产阶级的一切最卑鄙的东西。她对休说,她认为,他对皮卡迪利大街上“那些可怜的女子(47)”的境况负有责任——休,可怜的休,这位十足的绅士!——从没有人显得像他那样震惊!事后她告诉彼得,她是故意冒犯休的(那时她和彼得经常在菜园里会面,交换记下的信息)。“他不读书,不思考,麻木不仁。”彼得耳边又响起萨利用十分强调的语气讲的这些话。这种语气表达的内容远远超过她了解的情况。她说,小马倌也比休更有生气哩。他正是那种私立学校培养的典型,她说,只有英国这种国家才可能产生像他那样的人。由于某种原因,她确实对他鄙视透顶,对他怀有某种怨恨。曾经发生过一桩事——他记不清什么事了——是在吸烟室里。他侮辱了她——吻了她吗?真不可思议!当然,谁也不相信对休的任何坏话。谁能相信呢?在吸烟室里吻萨利!天晓得!如果是什么伊迪斯贵族小姐,或者什么维奥莉特夫人,那倒颇有可能,但决不会是那个衣衫不整、一文不名的萨利,何况她还有个父亲(兴许是母亲)在蒙的卡罗赌博呢。因为在他的相识者中间,休为人最势利——最爱拍马——其实他并非十足的马屁精。他这个人过于一本正经,不可能老是阿谀别人。把他比作第一流的侍从显然更合适——就是那种跟在主人背后提箱子的角色;可以放心地派他去发电报——对女主人来说,他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况且,他找到了差使——由于娶了个贵族小姐伊芙琳为妻,他在宫廷里得了个小差使:照料陛下的地窖,擦亮皇家用的鞋扣,穿着短外裤和有褶边的制服当差。在宫廷里干一份小差使!生活多么无情!
他与那位贵族小姐伊芙琳结了婚,就住在这儿附近吧,彼得想(他注视着俯瞰公园的宏大建筑),因为有一次,他曾在其中一座房子里用过午餐,那里面有些陈设就同休所有的财产一样,在别人家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可能是放床单、毛巾等的柜子之类。你不得不走过去观赏一番——无论那是什么东西,你不得不花许多时间赞美它——不管是放床单的柜子,还是枕套,老橡木家具或者图画,休选择这些是从一首古老的歌谣得到的启示。不过,休的太太有时会露出马脚。她是那种不起眼的、胆小如鼠的女人,一味崇拜强有力的男子汉。她几乎被人忽视。然而,她会突然出人意表地讲起话来——讲得挺尖刻。或许,她还留着一丁点儿高贵的气派呐。燃煤的蒸汽使空气混浊,对她不太适宜吧。反正,他们就住在那儿,连同他们的床单柜、名画,以及配上地道花边的枕套,一年约莫有五千或一万英镑的收入;可是我,彼得思忖,尽管比休大两岁,却为找职业而困扰呢。
他已五十三岁了,可还得求他们设法给他一份秘书的职务,或给他找个教孩子拉丁文的代课的工作,去忍受办公室里某个小官吏的差遣,仅仅为了一年能挣上五百英镑;因为,他要是娶了戴西,即便加上抚恤金,他们的收入也不能低于这个数目。惠特布雷德大概能帮他一把,达洛卫也能办到,他并不介意请达洛卫帮他忙。达洛卫是正人君子,只是有点狭隘,脑子不怎么灵活;这些都是事实,但他是彻头彻尾的正人君子。无论什么事,他都以同样刻板的理智去处理,没有半分想象力,也没有一丝才气,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优点,这是他一类人所共有的。他应该是个乡绅——搞政治完全是浪费他的精力。在野外养狗骑马,最能发挥他的长处。譬如有一回,克拉丽莎的长毛狗掉入陷阱,有半个爪子都撕裂了,克拉丽莎晕了过去,而达洛卫却把一切都办得妥妥帖帖——给狗儿扎上绷带,安上夹板,安慰克拉丽莎,叫她别惊慌失措。敢情这便是她喜欢达洛卫的缘故——她需要的正是这个:“啊,亲爱的,别傻了,握住这个——把那个拿来。”一边又不断对狗说些什么,好像它也是人哩。
然而,她怎么能全盘接受他那一大通关于诗歌的议论呢?她怎么能听任他大谈特谈莎士比亚呢?理查德·达洛卫气势汹汹地大放厥辞,说什么正经人都不应该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因为念这些诗就像凑着小孔偷听(况且他不赞成诗中流露的那种暧昧关系(48)),还说什么正派人不应当让妻子去拜访一个亡妇的姊妹。简直莫名其妙!唯一的办法是用杏仁糖塞住他的嘴——他是在晚餐桌上说的这番话。可是,克拉丽莎把他的谬论照单全收,认为他非常诚实,颇有独到之见。天知道她是否认为,达洛卫是她遇到的最有思想的人呐!
这一点,又成了彼得和萨利之间的一根纽带。他们常到一个花园里散步,园子四周有围墙,栽着玫瑰花和大棵的花椰菜——他还记得萨利摘下一朵玫瑰,止步赞叹月光照耀下卷心菜叶多美(他好多年来从未想过这些往事,奇怪的是,昔日的情景竟然这么历历在目地涌上心头);此外,萨利又恳求他把克拉丽莎带走(诚然她是半开玩笑地说),把她从休和达洛卫之流“不折不扣的绅士们”那里拯救出来,他们只会“扼杀她的灵魂”(那时萨利写了许多诗歌),只能使她成为一个主妇,滋长她的世俗感。不过,对克拉丽莎也应当公正。无论如何她不会嫁给休,她很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她的情感全部露在表面,而在内心深处,她却十分机敏——例如,在判断人的性格上,萨利远远不及她,这种能力完全出自一种女性的直觉,她具有女性特有的天赋,不管在何处,她都能创造个人的小天地。她走进一个房间,站在门口,周围簇拥着一大群人,就像他常看到的那样,但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却是克拉丽莎。并非是她与众不同,她一点也不美,没什么动人之处,谈吐也从不显得格外机智,尽管如此,她却令人难忘,令人难忘。
不,不,不!他不再爱她了!不过,今天早上看到她拿着剪刀和绸片准备宴会之后,他无法抑制自己对她的思念;他的心头不断浮现她的倩影,仿佛坐在火车里,总是感到枕木的颠簸;诚然,这不是爱情,只是想念她,也批评她;事隔三十年,一切又重新开始,他试图剖析她的性格。显然她很世故,过分热衷于社交、地位和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都是真实的,她本人曾向他承认过。(只要你不厌其烦,总是能从她那儿了解到真情,她不会撒谎。)她会说,她讨厌衣衫不整的女人,讨厌思想保守和一事无成的人——大概就像他那种人吧;她认为,人们没有权利游手好闲,懒懒散散,无所事事;人必须干一番事业,出人头地;在她看来,在她的客厅里见到的社会名流、公爵夫人和白发苍苍的老伯爵夫人,象征着某种实际的权势,而他却认为这批人毫无价值可言。有一回她说,贝克斯巴勒夫人体态轩昂(克拉丽莎本人也同样,她决不会懒洋洋地斜靠着,总是挺直身子,其实有点僵硬)。她说,那些名流体现了一种勇气,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敬佩这种勇气了。当然,其中不少是达洛卫先生的观点,诸如热心公益、大英帝国、关税改革、统治阶级的精神,等等,所有这些对她潜移默化,熏陶颇深。尽管她的才智超出达洛卫两倍,她却不得不用他的眼光去看待事物——这是婚姻的悲剧之一。虽然她自己也有头脑,却老是引用理查德的话——好像人们读了晨报以后,还无法确切了解理查德在想些什么似的!譬如说,举行这些宴会都是为了他,或者可以说,为了她理想中的他(其实,替理查德说句公道话,他要是在诺福克(49)乡下务农会更愉快些)。她把家里的客厅变成一种聚会的场所,在这方面她简直有天才。彼得曾屡次看见她庇护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摆布他,转化他,教他觉醒,送他踏上人生的历程。诚然,无数干巴巴的人都聚集在她周围。但是,也会突然冒出几个意想不到的人物:有时出现一位艺术家,有时是一位作家,这类人同那种气氛格格不入。并且,这一切后面还有一整套的探亲访友,留赠名片,待人以礼,带着一束束鲜花与小礼品到处奔走;比如,某某人要到法国去了——就得送只气垫给他;像她这种女人投入的无休止的社交活动,确实令人身心交瘁,她却真心诚意地乐此不倦,乃是出于天性吧。
奇怪的是,在他熟识的人中间,她是最彻底的无神论者,也许(她在某些方面令人一眼见底,在另一些方面却十分难以捉摸,以前他惯于用这种想法去解释她的为人)她对自己这么说:既然我们的民族被锁在即将沉没的船上,注定要灭亡(她少女时代最爱读赫克斯利(50)和廷德尔(51)的著作,两人都爱用海上生涯的比喻),既然这一切只不过是可怕的笑话,就让我们至少尽一份力吧,减轻我们同室囚徒的痛苦(又是赫克斯利的语言),用鲜花和气垫装饰地牢,尽可能保持体面吧。那些凶神恶煞,不能让他们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