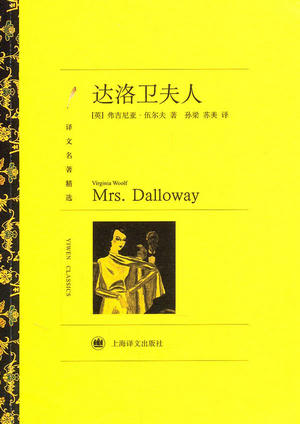达洛维夫人-达洛卫夫人-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埃文斯,埃文斯,”他呼唤着。
史密斯先生在大声自言自语,年轻的女仆艾尼丝在厨房里告诉菲尔默太太。当她端着托盘进去时,他高声叫道:“埃文斯,埃文斯!”她大吃一惊,吓得跳起来。她跌跌撞撞地奔到楼下。
雷西娅走进来,手里捧着鲜花。她穿过房间,把玫瑰花插入花瓶中,阳光直射在花朵上,雷西娅在室内欢笑,雀跃。
雷西娅说,她不得不从街上一个穷人手里买下这些玫瑰;不过,花儿差不多凋谢了,她说,一面插好玫瑰花。
唔,外面有一个人,肯定是埃文斯;至于雷西娅说的几乎凋谢的玫瑰,则是他在希腊田野上采撷的。互通信息意味着健康,幸福。互通信息,他轻轻地咕哝着。
“你在说些什么,赛普蒂默斯?”雷西娅问他,心中恐惧万分,因为他在喃喃自语。
她吩咐艾尼丝跑去请霍姆斯大夫。她说她的丈夫精神错乱,几乎连她也不认识了。
“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畜生!”赛普蒂默斯骂着,因为他看到了人性,也就是霍姆斯大夫,走进房间。
“哎,这一切是怎么回事?”霍姆斯大夫用人世间最温和的语气问他。“胡言乱语吓唬你的老婆吗?”霍姆斯会给他服一些药,让他安睡的。如果他们很有钱的话(霍姆斯冷嘲地扫视一下房间),如果他们不信任他的医道,那么,他们满可以上哈利街(64)去求医;霍姆斯大夫说这几句话时,不那么和颜悦色了。
时间恰恰十二点正,大本钟敲响了十二下,钟声飘荡至伦敦北部,同其他钟声汇合,又与云彩及烟雾飘渺地交融,终于在蓝天翱翔的海鸥之间消逝了——当克拉丽莎·达洛卫把绿色衣裙放在床上,当沃伦·史密斯夫妇一走上哈利街,就在此时,正午的钟声敲响了。十二点是他们预约的时间。雷西娅望过去,心想,那也许就是威廉·布雷德肖爵士的寓所吧,门前停着一辆灰色汽车。(一圈圈沉重的声波在空中回荡而消融。)
果然——是威廉·布雷德肖爵士的汽车,那辆灰色汽车,车身低、功率高,嵌板上只简朴地刻着他的姓名缩写,字字连缀;似乎他认为,不宜刻上贵族的纹章,因为他更高贵,乃是神灵的助手,传播科学的大法师。正因为汽车是灰色的,为了同这庄重与柔和的色泽相配,车内层层叠叠铺设灰色毛皮和银灰色毛毯,这样,爵士夫人在车中等候时就不会受风寒侵袭。威廉爵士经常驾驶六十英里甚至更长的路程,到乡间去为那些有钱的病人出诊,恰如其分地索取高额诊金,因为这些病人付得起。爵士夫人背靠座位在车中等候一小时或更长一些时间,膝盖周围用毛毯裹住,心中有时想着病人,有时想着一堵金墙;就在她等待的时候,金墙每分钟都在增高;她这么想是有道理的,因为金墙能使他们俩摆脱所有的变故和忧患(她曾勇敢地忍受忧虑,他俩曾苦苦奋斗)。她这么想着、想着,感到自己置身于宁静的海洋上,那里唯有香风吹拂;她受人尊敬、赞美、羡慕,她的愿望好像都已实现,尽管身子肥胖不免令她遗憾;每星期四晚上,他俩都要设盛宴,招待同行;偶尔为义卖市场剪彩,还觐见过皇族;可惜她和丈夫相聚的时光过于短暂,因为他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他们有一个儿子在伊顿公学(65)念书,学习很出色;她还想生一个女儿;她的兴趣很广泛,儿童福利啰、癫痫症的病后调养啰,她都关心;此外,她也酷爱摄影,要是正在兴建一座教堂,或者一座教堂行将倒坍,她就会在等候丈夫的时候,买通教堂司事,拿了钥匙进去拍照,那些照片几乎能和职业摄影师的作品媲美呢。
威廉爵士本人年纪不轻了。他曾拼命工作,他的地位完全由于他的能力(其父是个小店主);他热爱自己这一行,善于在大场面上显露头角,又有雄辩的口才——当他受封爵位时,多年的辛劳使他显得滞重、倦怠(川流不息的病人简直永无休止,名医的重任和特权那么艰巨),这种倦怠的神色配上白发,使他的形象更显得与众不同,并且带来一种声誉(这对于治疗神经科疾病尤为重要),说他不仅具有闪电般的绝技和几乎万无一失的诊断,而且富有同情心,手腕高明,洞察人心。当他们俩(沃伦·史密斯夫妇)一走进房间,他便一目了然;一看到赛普蒂默斯,他就断定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病例。他在几分钟内就确定,这是精神彻底崩溃的病例——体力和神经全面衰竭,每个症状都表明病情严重(他在一张浅红色病历卡上记录他俩的回答,一面小心地喃喃自语)。
霍姆斯大夫给他治疗了多久?
六个星期。
开了一点溴化剂吗?他说什么病也没有吗?噢,是的。(这些普通开业医生!威廉爵士心想,他一半时间都得花在纠正他们的错误上,有些根本无法弥补。)
“你在战争中表现很出色吗?”
病人迟疑地再说了“战争”一词。
病人给词汇赋予象征性的含义。这是个严重迹象,应记入病历卡。
“战争?”病人问。欧洲大战——是小学生用火药搞的小骚动吗?他在服役期间表现很出色吗?他真的忘了。正是在大战中他失败了。
“不,他在战争中表现非常出色,”雷西娅肯定地告诉医生。“他得到了晋升。”
“在你的办事处,人们对你的评价也很高吗?”威廉爵士扫了一眼布鲁尔先生那封充满赞美之词的信,低声问道。“那么,你没什么需要担忧,没有经济问题,什么问题也没有,是吗?”
他犯了一桩可怕的罪,被人性判处了死刑。
“我……我曾经,”他开始说,“犯了罪……”
“他什么过错也没有,”雷西娅向医生保证。威廉爵士道,如果史密斯先生不介意的话,他想和史密斯太太在隔壁房间谈一谈。你的丈夫病情很严重,威廉爵士告诉雷西娅。他是否扬言要自杀?
是的,他是这么说的,她答道。不过,他不是当真的,雷西娅说。当然不是。问题只是他需要休息,威廉爵士道:休息,休息,再休息,长期的卧床休息。乡下有一所令人惬意的疗养院,她的丈夫会在那儿得到充分照料。要叫他离开她吗?她问。威廉爵士道:没有别的办法,他必须离开她;当我们患病时,最亲近的人对我们并无好处。不过,他没有发疯吧,不是吗?她问。威廉爵士从来不提“疯狂”这个词,他称之为丧失平衡感。她又说,她的丈夫不喜欢医生,他会拒绝到疗养院去的。威廉爵士简短而耐心地跟她解释病情。他曾扬言要自杀。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可供选择。这是个法律问题。他将在乡间一所美妙的屋子里卧床休息。那里的护士很出色呐。威廉爵士每星期会去探望他一次。假如沃伦·史密斯太太真的感到没有其他问题需要问他了——他从不催促病人——那么,他们就回到她丈夫那儿去。她说,没有什么要问了——没有什么需要询问威廉爵士的了。
于是,他们回到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跟前,这个人类中最崇高的人,他是面对法官的罪人,绑在高处示众的牺牲者,亡命之徒,溺死的水手,写下不朽颂歌的诗人,撇开生命走向死亡的上帝。他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在日光照耀下,谛视着布雷德肖夫人身穿宫廷服装的照片,含糊地咕哝着关于美的字眼。
“我们已经简短地交换了意见,”威廉爵士道。
“他说你病得很重,很严重,”雷西娅说。
“我们认为你应该到疗养院去,”威廉爵士告诉他。
“霍姆斯办的疗养院吗?”赛普蒂默斯嗤之以鼻。
这家伙给我的印象极坏,威廉爵士自忖;因为他的父亲是个生意人,他对教养和衣着怀有本能的敬意,衣衫不整使他恼怒;而且,更隐秘的原因是,威廉爵士内心深处嫉恨有教养的人,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时间读书,而那些人来到他的诊所,暗示医生并非受过教育的人,尽管这个职业需要才智高超的人时刻绞尽脑汁。
“不错,是我办的一个疗养院,沃伦·史密斯先生,”他说,“在那里,我们将教会你休息。”
最后还有一桩事。
他深信沃伦·史密斯先生复原以后,世上没有人会比他更温存,决不会让妻子受惊吓的。不过,他曾扬言要自杀哩。
“我们都有消沉的时刻嘛,”威廉爵士道。
你一旦失足,人性就会揪住你不放,赛普蒂默斯反复告诫自己。霍姆斯和布雷德肖不会放过你的。哪怕你逃入沙漠,他们也会去搜索,哪怕你遁入荒野,他们也会尖叫着冲过来,还用拉肢刑具和拇指夹(66)折磨你。人性残酷无情哪。
“他有时会冲动吗?”威廉爵士问雷西娅,把铅笔搁在浅红色病历卡上。
那是我自己的事,赛普蒂默斯在一边说。
“没有人只为自己而活着,”威廉爵士道,同时瞟了一眼他妻子穿着宫廷服装的相片。
“你还有远大的前程哩,”威廉爵士道。布鲁尔先生的信就放在桌上。“前途无量嘛。”
假如他吐露真情呢?假如他实言相告呢?霍姆斯、布雷德肖会不会放过他?
“我……我……”他结结巴巴地说。
可他究竟犯了什么罪?想不起来了。
“什么?”威廉爵士鼓励他说下去。(时间可不早了。)
爱、树木,没有罪行——他给人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想不起来了。
“我……我……”赛普蒂默斯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
“尽可能少考虑你自己,”威廉爵士善意地劝他。说实在的,他这样的身体根本不宜走动。
你们还有什么事要问我吗?威廉爵士道。他会作好一切安排(他低声告诉雷西娅),他会在当天傍晚五点到六点之间通知她的。
“一切都托付给我吧,”他说,接着打发他俩走了。
雷西娅出生以来从未感到如此痛苦,绝对没有!她祈求医生帮助,却遭到了冷漠,敷衍了事!他辜负了他俩的期望!威廉爵士不是个好心人。
当他俩走到街上时,赛普蒂默斯说:光是保养他那辆汽车就得耗费不少钱吧。
她紧紧攫住他的手臂。他俩被人抛弃了。
其实,她对医生还能有什么奢望呢?
他已给了病人三刻钟时间。如果在这门精确的科学中,一个医生丧失了平稳之感,就不成其为医生了,何况这门科学涉及的是我们一无所知的领域——神经系统,人的大脑。我们必须有健康的体魄,而健康就意味着平稳。当病人走进你的诊所,宣称他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个常见的错觉),还说他要给世人启示(病人大都这么说),并且扬言要自杀(他们经常这么扬言),那医生就得运用平稳的手段:命令病人卧床休息,独自静养,安静和休息;休息期间不会见朋友,不看书,不通信息;休息六个礼拜,直到病人的体重从进院时的七点六磅增加到十二磅为止。
平稳,神圣的平稳,乃是威廉爵士的女神。他获得这一概念是在巡视病房之时,在垂钓鲑鱼之时,在布雷德肖夫人于哈利街生儿子的时刻。布雷德肖夫人也钓鲑鱼,而且,她拍的照片同职业摄影师的不相上下。由于他崇拜平稳,威廉爵士不仅自己功成名就,也使英国日益昌盛;正是像他之类的人在英国隔离疯子,禁止生育,惩罚绝望情绪,使不稳健的人不能传播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也接受他的平稳感——如果病人是男子,就得接受他的观念,如果是女子,就接受布雷德肖夫人的观念(这个贤妻良母绣花,编织,每星期有四天在家陪伴儿子);正因为如此,不仅同行尊敬他,下属害怕他,而且病人的亲友对他怀有最深切的感激,因为他坚决主张:那些预言世界末日或上帝显灵、自命为基督或女基督的男男女女预言家们,统统应该遵照威廉爵士的命令:躺在床上喝牛奶——这是威廉爵士根据三十年来治疗这类病例的经验,以及他那一贯正确的直觉得出的结论。这,便是疯狂——这种观念,他那平稳的观念。
然而,平稳还有个姊妹,不那么笑容可掬,更令人敬畏;这位女神此刻正要冲下圣殿,打碎偶像,代之以她自己那严峻的形象——在炎热的印度沙丘上,在泥泞的非洲沼泽地里,在伦敦的贫民窟;总之,只要不正常的气候或魔鬼引诱人们放弃自己的真实信念,她便会在那里出现。她的大名叫感化,她尽情地蹂躏弱者的意志,热衷于引人注目,发号施令,强加于人,把自己的容貌刻在民众脸上而得意扬扬。在海德公园的自由论坛上(67),她站在一个桶上宣讲;她身穿白衣,装出兄弟般仁爱的面貌,在工厂和议会里走动,带着一副忏悔的模样;她提供援助,但渴望权力;她粗暴地惩罚异己分子或心怀不满的人;她赐福于驯良之辈,他们仰望她,卑躬屈膝,从她的眼神里看到自己的光明。这位女神(雷西娅·沃伦·史密斯看透了)也存在于威廉爵士心中,尽管她披着似乎合情合理的伪装,潜伏在冠冕堂皇的名称之下:爱情、职责、自我牺牲,等等;在大多数场合,她不露真面目。威廉爵士一直多么辛勤地工作啊——多么努力地筹措资金,宣传改革,创立机构啊!但是,感化,这位爱挑剔的女神,更喜欢鲜血,而不爱砖瓦,并且极其微妙地尽情销蚀人们的意志。譬如布雷德肖夫人吧,十五年前她屈服了,拜倒在感化女神的脚下,这是完全无法解释的:没有当众争吵,没有厉声申斥,只是潜移默化,她的意志渐渐消沉,被水淹没,转变为他的意志。她带着甜蜜的笑容,很快地顺从了;在哈利街宅子里准备八九道菜,宴请十至十五位专家,她都应付裕如,礼数周全。不过,那天晚上,她露出一些呆板的样子,兴许是忐忑不安,神经质的抽搐,笨拙的摸索,支吾其辞,困惑不解;这一切证明这位可怜的夫人说了谎——要相信这一点真叫人痛苦。曾几何时,她为人机灵,轻而易举地钓到鲑鱼,而如今,却为了满足她丈夫追求控制与权力的强烈欲望,那种使他眼睛里闪现圆滑而贪婪的神色的欲望,她抽搐,挣扎,削果皮,剪树枝,畏畏缩缩,偷偷窥视;她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缘故使那天的晚宴不太愉快,为什么人们感到头昏脑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