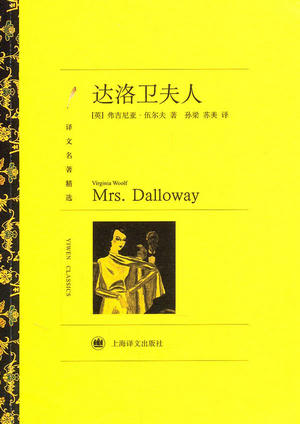达洛维夫人-达洛卫夫人-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头昏脑涨(很可能由于医学专业的话题太严肃了,或者由于主人身为名医,过于忙碌而疲乏不堪;布雷德肖夫人说,一位名医的生命“属于他的病人而不属于他自己”);总之,晚宴沉闷乏味;所以,当钟声敲响十点,散席之后,客人们呼吸到哈利街上清新的空气时,真感到如释重负;不过,这种安慰却不是那位名医的病人能享受的。
在那墙上挂着图画、陈设着贵重家具的灰色诊所里,病人们在毛玻璃反射的日光下,了解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他们蜷缩在扶手椅里,瞧着他为了他们的利益,挥舞手臂,做完一套奇怪的动作。他突然伸出胳膊,又猛地抽回来,从而证实(如果病人顽固不化)威廉爵士完全能控制自己的行动,而病人则不能。就在那诊所内,有些软弱的病人经受不住,放声啼哭,低头屈服;另一些人,天知道他们受了什么过于疯狂的刺激,竟然当面辱骂威廉爵士是个可恶的骗子,甚至更为狂妄地怀疑生命本身。人为什么要活着?他们问。威廉爵士答道:因为活着就好。对于布雷德肖夫人来说,活着当然是美好的;她那幅戴着鸵鸟毛装饰的画像就挂在壁炉之上的墙上,而他的收入呢,一年差不离有一万二千英镑呐。可是对于我们这种人呢,病人责问道,生活并没有给予这些恩惠。威廉爵士含蓄地表示赞同。他们缺乏平稳的观念。也许,归根结底,人世间并没有上帝吧?病人又问。他耸了耸肩膀。总而言之,活着还是死去,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吗?在这一点上,你们错了。威廉爵士有一位朋友住在萨里(68),有人在那里教授一种十分艰难的艺术(威廉爵士坦率地承认)——平稳的观念。此外,还有家庭温暖,荣誉,勇敢,以及光辉的事业。威廉爵士对这一切都坚决拥护。万一这些终于失败,还有警察和社会力量支援他。他们将在萨里注意压制那些不利于社会的鲁莽举动,威廉爵士沉静地说。这些举动主要是由于出身低微而滋生的。到那时,那位女神便会从她潜伏之处悄悄地踅出,登上宝座;她的欲望是镇压反抗,把自己的形象永不磨灭地树立在他人的圣殿内。于是,那些赤身裸体、筋疲力尽、举目无亲、无力自卫的人们便受到威廉爵士的意志的冲击。他猛扑,他吞噬,他把人们禁闭。正是这种决心和人道的结晶,促使他的牺牲品的亲属对他感到如此亲切哩。
然而,在哈利街上彳亍的雷西娅·沃伦·史密斯却说,她不喜欢那个家伙。
哈利街上钟声齐鸣,把六月里这一天又剁又切,分割又分割,仿佛在劝人驯服,维护权威,并齐声宣告平稳观念无比优越,直到繁杂的钟声愈来愈减少,最后只剩牛津街上一家商店上面的商业钟,亲切而友好地敲响一点半,似乎那商店(里格比—朗兹公司)为了能给大家免费报时而感到荣幸。
抬头望一下,看来那招牌上的每一个字母代表某一个钟点;人们不由得感谢里格比—朗兹给公众报时——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这种感激的心情自然会促使他们以后去买那家商店的鞋袜。当惠特布雷德在橱窗前闲荡时,转着那些念头。他就是这样转念头的。这是他的习惯。不过,他想得并不深。他总是浮光掠影,一忽儿念陈腐的古文,一忽儿又搞当代语言,还轮流地向往巴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69)的生活;以前还喜欢骑马,射击,打网球呢。有人谑弄地声称:如今他在白金汉宫当警卫,穿着丝绸长袜和短裤,看守着不知什么东西。不过话得说回来,此人异常干练。他在伦敦上流社会混了五十五年,结识过几位首相呐。据说,他的感情却很深挚。如果说他从未投入当代任何伟大的运动,也没有出任显要的官职,至少他参与了一些不那么重大的改革,诸如改善公共房屋喽,保护诺福克郡的猫头鹰喽,保障女佣们的福利喽,等等。此外,他曾屡次写信给《泰晤士报》,要求人们捐助基金,呼吁公众维护公益,清除垃圾,减少乌烟,禁止公园内的秽行;这些信末的署名令人肃然起敬。
当下,一点半的钟声渐次消逝,他在橱窗前逗留一会,挑剔而庄重地审视那些短袜与鞋子,看上去仪表堂堂,衣冠楚楚,一副殷实而无瑕可击的模样,好像他居高临下地俯视人间;同时又意识到,这种人财两旺、满面红光的气派必须有适当的举止,因而,即使在不太需要的场合,他也拘泥于小节,彬彬有礼,一派古风,平添了一份雅致;这种风度是值得摹仿并且记住的;例如,每当他跟布鲁顿夫人(他和她已有二十年交情了)进餐时,他总是捧着一束康乃馨花,双手递过去献给她;同时向夫人的秘书布勒希小姐致意,问候她在南非的那位兄弟近况如何;可是不知怎的,布勒希小姐尽管毫无女性的风韵可言,还是会恼羞成怒,便说,“谢谢,他在南非过得挺好哩。”其实,在过去六年中,他是在朴茨茅斯(70)勉强混日子罢了。
至于布鲁顿夫人嘛,则更喜欢理查德·达洛卫;他与惠特布雷德同时到达,事实上是在门口碰面的。
布鲁顿夫人当然会更喜欢理查德·达洛卫。他这块材料好得多呢。然而,她不愿使可怜的亲爱的休相形见绌。她一辈子也不会忘却他的好心肠——他的心肠实在好,好得出奇——她记不清究竟在什么场合,可他的确是——出奇地好心肠。无论如何,一个人同另一个之间的区别算不了什么。克拉丽莎·达洛卫却惯于剖析这个和那个人,评头论足的——把他们解剖、分析,然后再缝起来、合拢来;布鲁顿夫人可看不出这有什么意思,不管怎样,到了六十二岁这把年纪,对此更觉得无聊了。当下,她接过休送的康乃馨,一面强作笑容,露出阴森森的棱角。她说,没有别的客人了。她是找了个借口,要他们来的,想请他们帮她解决一个难题……
“可是,咱们吃了再谈吧,”布鲁顿夫人说。
于是,罩着围裙、戴着白帽的侍女们轻盈地穿过旋门,川流不息,了无声响;这辈侍女们并非日常所需,而是训练有素的老手,帮着梅弗尔区的主妇们,从午后一点半到两点钟,举行神秘的、梦幻似的盛宴;那时,一挥手之间,车水马龙停止了,宾主入座,闪现出深深的幻觉,首先是佳肴——据说并不花钱;一会儿,餐桌仿佛自动地摆满金银餐具、细巧的衬垫、盛着红果的碟子;展现出涂奶油的棕色比目鱼片,蒸锅里遨游着鸡块;色彩缤纷的火焰燃烧着,并非家常炉火;美酒加上咖啡(据说也不花钱),喝得大伙儿目眩神迷,眼前晃动着美妙的幻景,目光都显得柔和而沉思,恍惚觉得生活是神秘的,洋溢着音乐之声;此时此刻,亢奋的目光惬意地谛视着嫣红的康乃馨,美极了;那鲜花被布鲁顿夫人撂在菜盘边(她的动作老是带有棱角);充满美感的休·惠特布雷德心旷神怡,觉得整个宇宙一片和谐,同时对自己的地位蛮有把握,因而搁下刀叉,问道:
“那花儿要是衬着您的花边,岂非更可爱吗?”
这样亲昵的唐突却使布勒希小姐反感之极。她认为他是个没教养的贱胚。对于她的想法,布鲁顿夫人一笑置之。
这位老夫人举起康乃馨花,握在手里,硬邦邦的,恰如她背后画像上那位捏着纸卷的将军;她毫不动弹,出神了。看她这副模样,理查德·达洛卫不禁自忖:此刻她像什么呢?那将军的曾孙女?敢情是玄孙吧?嗬——活像罗德里克爵士、迈尔斯爵士、塔尔博特爵士。真奇怪,那个家族里都是女人逼肖祖先。她本人就有资格当龙骑兵的将领哩。理查德愿意愉快地在她麾下服役,他对她极其崇敬;对于名门世家德高望重的老夫人,他怀有罗曼蒂克的想法,并以他惯有的和善的性情,想带几个热心肠的朋友来赴宴,跟她结识;似乎像她这样的贵夫人可以由脾气温和的、热心喝茶的人来培养呢!他熟悉她的故乡。他了解她的亲人。她那庄园里有一株古老的葡萄树,仍然活着;据说洛夫莱斯(71)或赫里克(72)曾在这棵树下憩息哩;尽管老夫人从未念过一句诗,这一传说照样流传至今。此时,布鲁顿夫人却在思量:还是等一会再跟客人商议吧,等他们喝过咖啡再讨论使她烦心的问题吧——是否要向公众呼吁,措词如何,等等。这么盘算着,老夫人就把那束康乃馨重新撂到菜盘边。
“克拉丽莎好吗?”她蓦然问道。
克拉丽莎一直说,布鲁顿夫人不喜欢她。确实,大家都知道,布鲁顿夫人感兴趣的是政治而缺少些人情;她讲起话来像个男子汉,曾在八十年代一桩臭名昭彰的阴谋中插过手,这一事件在新出的回忆录内逐渐披露了。无疑地,她的客厅里有个凹壁,其中嵌着一张书桌,上面放着一帧已故的塔尔博特·摩尔将军的照相;正是在那桌子上(在八十年代的一个夜晚),当着布鲁顿夫人的面,经她默契(或许还出了些点子),那将军写了一份电报,下令英国军队在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挺进。她保存了那支笔,而且讲述了这桩轶事。所以,当她随意地问一下“克拉丽莎好吗”之时,难以相信她竟会关心什么妇女,男人们也难以劝说自己的妻子相信这一点,其实,不管他们对老夫人如何忠心,私下里也感到怀疑呢;那些太太时常阻碍丈夫,不许他们到海外上任;议院休会期间又常患流感,必须由丈夫陪着去海滨疗养。然而,对于女子们来说,老夫人这一问候(“克拉丽莎好吗?”)肯定是善意地表示关怀;她几乎是妇女们的一位沉默寡言的伙伴,兴许一生中只有这么五六次问好,但这些话反映出,她承认自己同其他女性有姐妹般的情谊;尽管她以宴席款待男子们,骨子里却对女人怀着更深的情谊,它使布鲁顿夫人与达洛卫太太奇异地联结起来,虽然两人难得见面,而且偶然相处时,彼此显得淡漠,甚至好像怀着敌意呐。
“今天早晨,我在公园里碰见了克拉丽莎,”休·惠特布雷德说,一面猛地把叉子插入蒸锅,急于让自己尝一下美味;事实上,他只要一到伦敦,便会碰见所有的熟人;布勒希小姐看他这副样子,就自忖:馋鬼!他是她见过的最贪吃的家伙之一;布勒希小姐一贯以毫不动摇的严正态度观察男子,但也能始终不渝地忠诚,特别对于女子;她本人则历经生活的磨练,瘦骨嶙峋,没有丝毫女性的风姿了。
“你知道谁到了伦敦?”布鲁顿夫人忽然想起了这个秘书,“咱们的老朋友,彼得·沃尔什。”
大伙都会意地微笑。彼得·沃尔什!布勒希小姐又自忖:达洛卫先生听到这消息真的高兴,而惠特布雷德先生一心只想吃鸡哩。
彼得·沃尔什!三个人(布鲁顿夫人、休·惠特布雷德、理查德·达洛卫)都勾起了同样的回忆——彼得怎样热烈地陷入情网,遭到拒绝,流亡印度,变成种植工,潦倒不堪;理查德·达洛卫却非常喜欢那亲爱的老朋友。布勒希小姐看出这一点,窥见他那褐色的瞳仁里含有深情,看出他在踌躇,考虑;这引起了她的兴味,实际上她是一直对达洛卫先生饶有兴味的;此刻她心里在嘀咕:他对彼得·沃尔什究竟怎么想的呢?
大约他在想:彼得·沃尔什曾爱过克拉丽莎;他要吃完午餐后立即回家,找克拉丽莎谈一下;他要滔滔不绝地说他爱她,爱她。真的,他会那样说的。
布勒希小姐一度几乎爱上了那些沉思默想;而且达洛卫先生总是那么可靠,还是个非常文雅的君子呐。如今,米莉·布勒希已四十岁了,所以只要布鲁顿夫人点一下头,或突然微微转过脸来,她便心领神会,虽然她一直深深沉湎于那些冥想中;她以超脱的态度和无瑕的心灵沉思着,生活无法欺骗她,因为从未给过她一丁点儿有价值的玩艺儿;她天生没有纤毫妩媚之处,无论嘴唇、脸颊或鼻子,都不会含笑地曲传风情;因此,只要布鲁顿夫人点一下头,她就立刻叫珀金斯赶快端咖啡。
“不错,彼得·沃尔什回来了,”布鲁顿夫人道。所有在座的人都有些得意。因为,他受尽磨难,功不成名不就,终究回到他们中间,仿佛回到安宁的海滩。不过,他们又考虑:实在没法帮助他,由于他的性格有一种缺陷。当下,休·惠特布雷德说,当然可以向某个要人提起彼得。他说自己将写信给执政的大臣们,为“我的老友彼得·沃尔什”疏通,但一想到这种信,他便皱起眉头,露出郑重其事而又无可奈何的神色。因为这种推荐信不会有什么效果——不会产生一劳永逸的结果,由于彼得的性格有缺陷。
“他跟某个女人有些纠葛呢,”布鲁顿夫人道。在座的人早已揣测那话儿是麻烦的根源。
“不过,”布鲁顿夫人急于撇开这话题,“咱们还是听彼得本人怎么讲吧。”
(咖啡还没端来,慢得很。)
“眼下他住在哪儿?”休·惠特布雷德喃喃地问道;这一问立即在仆人中引起一点反响,犹如在灰蒙蒙的潮汐中激起一丝涟漪;那些仆役像流水一般,昼夜不息地围绕着布鲁顿夫人,为她收集需要之物,挡住可厌的人,宛如用精致的纤维织成的一张网,卫护着老夫人,替她抵御冲击,减少打扰;这张网笼罩着布鲁克大街上这幢屋子,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安放得井井有条,需要时由头发灰白的珀金斯拣出来,丝毫不差,他已跟随布鲁顿夫人整整三十年了;当下,这老家人写下了彼得的地址,交给惠特布雷德先生,于是他掏出笔记本,抬一下眉毛,把那纸片夹在最重要的文件中间,随即说,他要叫伊芙琳请彼得来吃饭呢。
(仆人们在等惠特布雷德先生夹好纸片。)
布鲁顿夫人自忖:休的动作实在慢。她还注意到,他发胖了。理查德则始终保养得神清气爽。老夫人等得不耐烦了;她的整个身心绝对地、无可否认地、甚至专横地倾注于一项计划,急于甩掉这桩微不足道的琐事(彼得·沃尔什和他的私生活);那项计划使她全神贯注,不仅如此,而且占据了她的灵魂,渗入灵魂深处,那是她的命根子,倘若没有它,米利森特·布鲁顿就不成其为米利森特·布鲁顿了;这计划乃是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