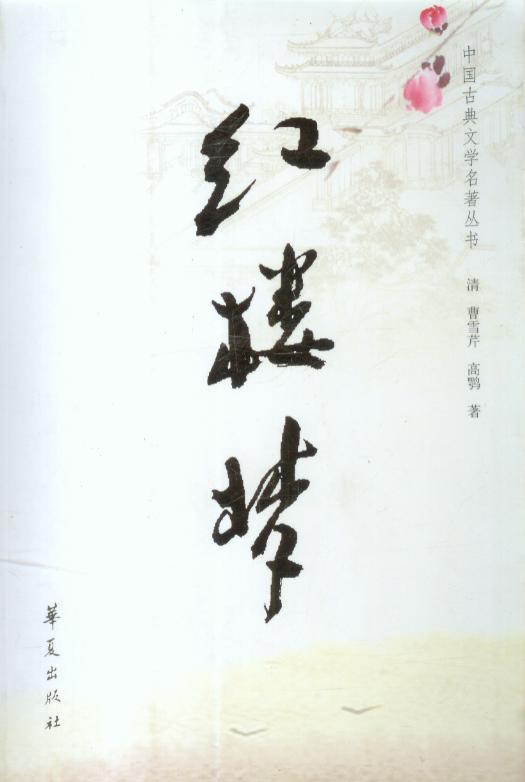红楼之林氏长兄-第15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耪乒竦囊馑迹窃僮鲂┐废隳抑啵庑┒饕膊还螅桶醋懦杀臼招┤斯ぃ辞肜弦氖鞠隆!绷帜溃骸肮蓬E的弟弟也是今年下场?教他别太累着,有空顾些家里。”
林可咧嘴:“古顺知道了,一定自己来给老爷磕头。”闻歌是林可家的干女儿,当年给了古頔,没给主子当屋里人,林可家的还偷偷说过这丫头有福不享,偏要出去当市井妇人。不过若是古顺有了出息,倒也是古家的造化。
“兰柯伶牙俐齿的,我也有些时日没查他的功课了。”林沫摸了摸下巴。林可道:“可不是呢,前阵子闻歌不是进来,说是老爷现如今是崇安王的师傅了,他不敢妄自高攀,不过是博个运气罢了。”林沫想了想古顺的文章,笑了笑:“他啊,只要不出大褶子罢。”
也才几年以前,他也是在考场上赌自己前程的,不过那会儿豪情万丈,心里头自信满满,倒不是现在年轻人不知自己斤两的以为天下都在自己脚底下,他寒窗苦读数十年,许多年里一直连吃饭喝水都握着书,他出自文礼之乡,曾与数十名名扬天下的大儒舍辩三日,志得意满地入京师来时,心里也在苦笑,他在这十年里,曾经咳血三次,简直是因此得折去十年寿命,而他也不是那些剑走偏锋的清高文人,会写那些离经叛道的文字,末了再感叹自己空有满腹经纶不得赏识——他的文章、学识,都极其符合君主的喜好。即使年纪资历还不足以做科举主考,他的眼光也准。
是以当花霖问到科举之事时,他笑道:“总有人觉得下场一试,方知深浅,这些人大约两耳不闻窗外事,把书读死了,自己困在井底,从未见识外面,才有此一说。平日里与人多说说,见见别人的文章,比对比对,自己有多少墨水就该知道才是。我听说周翰林当年被称为神童,然中举后连续六年不曾下场,到他觉得自己能中时方才一试,高中榜眼。可惜这世上读书读死了的也不少,自视清高的更有。”
花霖道:“兴许不叫自视清高,只是人人自爱。我每日瞧着自己,也觉得我很好。”林沫听了不觉大笑:“可巧,微臣闲时揽镜,也觉得自己很是不错。”
他们二人念书累了闲聊两句,轻松轻松,可有人非得躲后头听见了,觉得“自视清高”四个字十分刺耳,叫他浑身不舒服。
本来谁都没把这事当回事。
如果没有那场“意外”的话。
“我一直觉得这个年纪的小孩子是非常可怕的,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做事不计较后果,还小肚鸡肠。”那时候他是这么跟容嘉评价遂承的,“我可不敢管教他,我劝你要是没有把他打老实了的信心,也不要趟这个浑水,交给姨夫最好。”
可是有些小孩子,他们将来是国之栋梁,甚至把握重权,可他却不能管教。
险些酿成大错。
皇孙们需得不忘祖训,除了念书习字,骑马射箭的功夫也不能忘。不过他们年纪还小,能在马上小跑的,已经算是很不错了。皇帝虽然自己不爱好这些,但是对孙儿们要求却也不宽松,没多久就叫他们换下温顺的小马,试着驾驭黄骠马驹。
到底是一群小孩儿,个个身娇肉贵,武师傅也小心谨慎地,替他们拉着缰绳也不敢松手。不过也有并不惧怕的:“这样的小马驹儿都这般拘束着,咱们先前也白学了。”要自己跑动起来。
林沫并不在现场。
大考在即,本来素来是礼部主持的,不过玉征文偏巧这时候家里孙子不争气,容嘉倒是管着仪制清吏司呢,他不过是个郎中,品级不够,他哥哥还要下场,礼部侍郎也没什么名声,怕不能服众。故而任命陈大学士为主考,端王、玉征文为同考,本欲任命林沫为提调,但他实在是分身无力,前几年累得吐血的事儿还吓得出动了御医,他的风头出得足够了,实在不必如此劳累。于是户部的何侍郎就任了提调。
林沫也因此接管了何侍郎的事儿。
也因此,错过了校场的那一通变故。
崇安王的马受了惊吓,暴起狂奔,花霖几乎跌下马来,幸得四五个侍卫舍身上前,又有离得最近的瑞文强行堵住了那匹马的去路——倒是自己也跟着被甩出去了老远,头磕到了石头,生死不明。
皇帝盛怒。
当日的武师傅、侍卫统统被发落了一通,纵然有不少侍卫是出身名门的,亦有救主之功,也没逃得过板子,然而细究下来,结果却叫人心寒。
齐王之子惊崇安王之马。
如何惊,为何惊?外人无所得知。
林沫亦不得而知,他只知他素来文静的学生瑞文,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舍身拉住了那匹马,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第235章
水烨尧懵在那里。
他并不是刻意。花霖读书习字算是兄弟们之中的打头的;但骑马射箭的本事却平平。虽说年纪小,看不出来;但是当初拿着马驹小跑时,烨尧总是能胜过他的。然而也只他一个能胜便是。瑞文到底年纪大些,在马上平衡得更好;可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拉着缰绳,不让自己越过花霖去……不独瑞文,许多兄弟都是这样。于是在师傅们口中,崇安王越发地文武双全;聪明伶俐;事事都盖过其他兄弟。
烨尧不是傻子;久而久之,心中的愤慨就越发地积累。
但他到底也才六岁,六岁的孩子,偷偷踹一下堂兄的马匹,想要看到他惊慌失措的模样,让平时那副高高在上的脸面撕开——他并没有想要做多可怕的事情。
直到那匹马不受控制地狂奔起来,直到瑞文被撞了出去,满脸满脸地血,他才尖叫一声,不可自控地几乎晕了过去。
他是几乎晕过去,听到消息的皇后两眼一花,是真要倒下去了,亏得是黛玉在一边扶着,太医眼明手快地掐着人中弄醒了,一叠声地问:“花霖如何?瑞文怎么样?”
都不怎么样,花霖伤了腿,瑞文更是怎么也醒不来,脑子里有淤血,再不见清醒就大约真没命了。
虽然都是亲孙子,但心里的轻重缓急自然是有所倚重的。瑞文伤得更重些,已非人力能补,一切听天由命。花霖贵为崇安王,自太上皇起都对他抱了十二分的希望,他若是腿上落下了残疾,对前程可就实在太不利了。
说道腿伤,不免会有人提起林沫来。
靖远侯腿伤了好些次了,没病没灾的时候就说骨头冷,受不得寒气,后来又是从马上摔下来,又是跪伤了膝盖,不少人都要扼腕叹息的时候,他却是瘸也不瘸,拐也不拐,走起路来照例挺拔利落,连仪态都比别人好上几分。
太医院也有林家弟子。只是花霖年纪还小,林家的羊胆接骨膏并不敢用,先有老太医复位,敷上南星散,再用复古散等小心敷着,佐以五色散等。独活、秦艽等也罢了,百草霜却是花霖这么个娇贵公子从没用过的,太医言道,崇安王还小,延胡不能多用,这百草霜去不得,皇后道:“只要能治好崇安王,也罢了。良药苦口。”
林沫捂着脸,趴在桌上想着瑞文。
多少人都奇怪为何什么他会偏爱瑞文。但事实上,他也没有多偏爱,他能怎么去宠爱一个皇家贵胃?不过是念书时候多提点两句,觉得他握笔的姿势不对,纠正纠正。瑞文是个极聪慧又敏感的孩子,他在写字作画上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天赋,甚至骑术也学得不错,总能叫他想起柳湘茹来——他虽没有柳湘茹的文采,却健康得多。
林沫有时候想,若是自己没有被丢弃,是不是也是过着这孩子一样的生活呢?被厌弃、被无视、被打骂、被指指点点。
太医守了瑞文一个晚上,终于摘了顶冠去向皇帝告罪。
这孩子的出身实在是太不好了,然而不管怎么样也是亲孙子,谁也不高兴眼见着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小孩儿就没了。
离大考只剩五天了。离皇帝的五十万寿,也不足一月。
当日马场教授他们骑术的师傅自然是不要想有命活下来了,进贡、挑选马匹的负责人也被连根追究起来,而罪魁祸首却有些难办。
容嘉心有戚戚。
他小时候经常挨揍,但最严重的一回还是因为他把林涵踢下了河,那河水也不深,林涵会凫水,不过是冻了些,染上了伤寒,咳嗽了几日,林白氏、林涵都没放在心上,容明谦却把他捆进了祠堂,结结实实地打坏了三根鞭子,打得他趴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
没有人会因为他纵容玉庄辙就训斥他,没有人告诉他要亲近兄弟,齐王倒是教他不要去招惹崇安王,用的却是不忿的口气,还对自己的妾室许下了不像话的承诺,叫那个女人和他的儿子一样沾沾自喜着飘飘然了。
想要欺负一下一直都压在他头上的堂兄,这本来在寻常人家里是极其普通的一件事。然而由齐王的庶长子对着秦王的嫡长子做出来,还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就复杂多了。
水瑞文再怎么不受宠,他是韩王的亲儿子。
水溶大半夜地想去打探打探消息,末了叹道:“罢了,太医院他的人比我多。”又是一怔,想着无论如何自己这时候应该要去打听打听韩王、齐王、秦王府上的动静,怎么竟跟着林沫想起一个小孩儿的死活了。只是苦笑完了,又有些担忧。
林沫却没他担心得那般伤心难过。他穿衣起来,叫了最亲近的侍卫去陈也俊家里传了他的一封手书,告诉他周家因族旺而出齐王妃,屡出大儒,百年根基尚在,切勿因一些流言就对未来妻子无礼。又叫聆歌待天亮静娴起身了就告诉她一身, 闭门谢客,进宫请安的折子也不必上了。
“公主怎么办呢?”聆歌忧心忡忡地问。
“没她什么事。”林沫阖眼道,“只是要变天了。”他摇摇晃晃地往床边儿走。聆歌看着他闭着眼睛走得歪歪扭扭,吓了一跳,忙上来要扶。然而林沫只是挥了挥手让她走远一些,自己慢吞吞地走到了床边,然后一头栽进了被子里。
聆歌觉得自己简直忘了怎么呼吸,妙荷已经低声惊叫了起来——再怎么惧寒,现在也到了晚春十分,床上被褥并不厚重。而林沫这重重地一摔,要是磕着哪儿可怎么办。
可是林沫像是没什么事儿一样蜷了蜷身子,就沉沉地睡去了。
他看起来不打算脱了身上的衣裳,也不打算换个舒服的睡姿,甚至不打算把被子拉好,几个丫头面面相觑,替他脱了靴子,摘了玉佩项圈等膈着的硬物,盖上了被子。
林沫一动不动的,仿佛感觉不到丫头们在做什么,他既没有阻止她们,也没有稍稍起身让她们做得更顺手一些的意思。
他觉得黑暗像一只无形的手,力大无穷,把他扯进了越来越深的梦境里。
“是你害死了瑞文,就像当年害死申宝一样。”
梦里,有个人这么跟他说。
他冷笑了一声,陷入无边的睡梦中去了。
水瑞文没了的时候,林沫刚从那一场睡梦中惊醒,一摸自己的脑门子,一头的冷汗,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又干又痒,愣是说不出一句话来。闻琴担忧地凑了过来,问了声:“老爷怎么了?”
人没了。
林沫苦笑着倒了回去,想想不对劲,伸出了手:“替我把衣服换了,我今儿个轮休,再睡一会儿。”静娴正听着闲话匆匆到他屋里来,见他这副模样,亲自上来替他换了衣裳,忧心忡忡地问:“老爷心里不好受?”
林沫一头埋在枕头里,声音闷闷的:“我中午想吃煮豆腐。”
“好好好。”静娴像哄修航一样柔声应道。若是和惠大长公主在,听见孙女儿如此语调,简直得老泪纵横。她又问,“早膳呢?你也不用了?”
林沫又睡着了。
静娴推了推他:“咱们家不见客,北静王见是不见呢?”
“我困。”林沫拖长了声音喊道,“我想睡觉。”
林沫最不讨人喜欢的地方就是每逢出了什么大事,他家里头就闭门谢客。似水溶这样身在局外,却有千丝万缕的眼线的人,自然逃不过一番追问。他是什么出身?打太极打得炉火纯青,谁也不知道北静王是什么心思,然而人嘛,只要开了口说了话,心里的想法总能够窥得一二,不管对还是不对,横竖让别人心里头有个想头。林沫就不同,他明明身在局里,却一个也不见,别人不知道他知道多少,更不知道他心里百转千回的是什么念头。
却不知林沫只是在躲罢了。
他不愿意在瑞文生死不明的时候被叫过去看花霖的腿,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被人求着去给烨尧求情。他怕自己控制不住,冒出许多恶毒的念头,对着一个六岁的孩子开火,因而也只能昏昏沉沉地睡着。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吓了一跳。
水溶自顾自地坐在他床头,也盖了条被子,手里既没有捧书,也没有什么打法时间的小玩意儿,就支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呵。”林沫嘟哝了一声;“我不是说了不见客。”
“你知道你睡了多久?”
“嗯?”
“中间太医都来了一次。”水溶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景宁郡君也不进宫去,林公主急得没法,拉着我母亲说,如今宫里乱成这样,她是不敢打搅皇后娘娘,求恩典回来看你,只能叫我母亲传个信儿给景宁郡君——我这不是带公主口信来的?”
林沫道:“找什么借口呢。公主传口信不会叫太监?你大可以直说想我了。”
水溶大大方方地一点头,同时道:“你这没羞没臊的样儿,真该叫你想想自己刚考上状元那会儿道貌岸然的正经模样。且起来洗漱罢,饿了这么多顿,胃里哪受得了。”
林沫笑着起身,问了一句:“天放晴了?”
水溶抿了抿嘴:“瑞文……陛下着礼部拟他的封号去了。”
林沫“哦”了一声,不再说话。
第236章
林沫睡了三天,不慌不忙地洗漱、沐浴;梳头更衣;就着粳米荷叶粥吃了半只盐焗小野鸭,还嫌腌得手法不地道,咸味过重;盖过了鲜味,吩咐往厨房去看看他们是不是睡着做的,叫妙荷一阵笑:“老爷可不能这么说,这是北静王带来的,要罚也该罚他府上的厨子去。李妈伺候了老爷十几年,可从未有过差池。”
林沫心里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