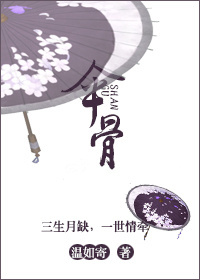伞骨-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嫂说的是。”
申屠衍跟着穆大友穿过一片柿子林,才看见隐于林中的茅屋,院落里挂着几串火红的辣椒,是北方传统的院落。
穆大嫂进厨房去了,申屠衍和穆大嫂便坐在院落里说话。
“你当年不是……被敌军俘虏去了,之后就一直没有你的消息……”申屠衍道。
“将军,我对不起你们大伙儿,当年我被拓跋凛的军队掳去后,他们几次三番让我投诚,我都不愿,他们将我拘禁在奴隶场中整整一年有余,我本来这副样子,苟延残喘,死活也没有什么大用,本想了此残生,唯一的缺憾就是不会回家再见你嫂子一面……到了来年开春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北靖军中易帅,拓跋三皇子被急招回京,他手下的大将任光弼却是有勇无谋的料子,我也在那时突然开了窍,想着横竖一死,你嫂子也不是死心眼的人,我回不去她便改嫁,不如赌上一赌,假意投诚,等待时机……谁知,没有等来这时机,却等来全军覆没的消息,将军,你且告诉我,他们究竟是什么死的?”穆大有说着,激动难以自持,指尖颤抖,眼圈也不知觉红了。
“他们……甚至是平日里最胆小的二狗子,都是堂堂正正战死的,临死一刻都是脊背挺直的,他们都很勇敢……是真正军人的模样!”申屠衍字正浑圆的说着,神情里俱是骄傲。
“那便好,那便好。”他反反复复说着,仿佛这样才能够安心。
他们二人又说了许多,说了那场战役,说了这些年的造化。暮色渐渐褪去,这远离市镇的边陲小镇竟然是难得的清净,各色人群生息在这里,大晁人,胡狄人,甚至是南疆漠北的人民,构成独特而富有生气的民俗画卷。熙攘而喧嚣的声音从远处传来,送至耳廓,竟然是申屠衍的心绪也柔和了许多。
他有时候这样想,这便是他保卫了十一年的土地,大晁的土地,大晁的子民,而,那个人,也是其中之一。他本与这片土地没有什么纠葛,却因为一个人想要拼命守住。
猛然,他霍的站起来,“我去带他回来。”
既然公理,礼法,线索统统都救不了他,那么,就直接去把那个人带出来。
——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法。
穆大有也站起来,“将军要救谁,兖州大牢可不是说闯就闯的……况且,今日来,这境上很不正常。”
“怎么不正常?”
“多了大量高头大马的胡狄人,按理来说,不应该啊,靖晁两国势来如同水火,而如今胡狄人却在兖州境内如入无人之境……”
“你是说有地方官员与北靖暗通款曲,肆意放纵?”
“我不确定。”穆大有摇头,“不过将军的那位朋友出狱也不是毫无办法……”
申屠衍的眼睛瞬间亮了。
☆、第四支伞骨·转(下)
钟檐在监狱的这几日,已经将附近的犯人认得七七八八,这个地方密不透风,常年充斥着人间最浓烈的情感,挥散不开。
这里的犯人,都是有一段前尘的,爱恨嗔痴皆是一种苦。可是到了这里,富商老爷也好,贫贱长工也好,都不过是死牢里的一个犯人罢了,唯一不同的是,有的人还能重见天日,有的人再也不能出去。
而钟檐属于第三类,马上要出去,不过是去见阎王。
隔壁的光头匪爷是个碎嘴子,整日揪着那偷嫂子入狱的秀才骂骂咧咧,“整天娘不拉几的,你烦人不烦人!圣贤书都读到屁股眼里去啦。”他凑着大脸又朝一旁的瘦弱书生凑了凑,“嘿嘿,还是说圣贤书里有教人偷人的?来,给爷瞅瞅!”
那书生“蹭——”的转过头去,不搭理他,匪爷火腾的上来了,“娘的,还蹬鼻子上脸了,你看这牢里,谁入狱的由头不是相当当的,就你看,那边蔫不拉几的那家伙,也是宰了太守老爷进来的,你看看你那点出息!”
钟檐摸摸鼻子,说得可不就是他么,苦笑道,“再英勇也是砧板上的鱼肉了。”
那光头匪爷嘿嘿笑,“英雄,我着实佩服你,想当年我在寨子里的时候,顶多就宰过师爷,那太守老爷……俺真是没想过哈。”
钟檐阴沉着脸,勉强道,“还……好。”
光头匪爷却起了兴致,一个劲的缠着钟檐讲述他是怎么样起了杀机,又是用哪把大斧劈开了那狗官的头颅,说得跟金子还真,连钟檐都要相信犯了案的不是他,而是他口中的那位好汉。
“你倒有几分说书的天分。”钟檐淡笑。
“可不是,俺如果出了去,那土匪窝早被端了,俺就说书去,也是一个好营生……可惜啊可惜,兄弟你是出不去了……”他这样想着,连声叹惋,“嘿嘿,俺是顶敬重你的,你若是真没日子了,你还有什么牵挂的事,俺都可以去帮你办,放不下的人,俺也替你照看着……嘿嘿,特别是你那个如花似玉的妹子。”
这妹子指的当然是秦了了,钟檐想,带她来兖州也算带她回了家,以后嫁娶生死,总不是自己能够做得了主的……还有什么,他上半辈子的亲人早已不在了,一房媳妇也跑了,老光棍一个。要有真舍不得的东西,就是他在云宣的铺子,一亩三分地,还有他藏在腌菜缸子里的碎银子,他还真真舍不得,可人死了计较着这些黄白之物做什么呢?
十年年少功名,十年蜗角虚利,再十年病骨孤鸾,这日子儿也就到了头,世间的荤腥浮华,他都沾了个遍,也算不得遗憾了。
光头匪爷见钟檐忽然禁了音,大老粗的性子也觉得不对劲,想着是触了人家的伤心事,忽然,歪在稻草中的男人却无声息的笑了,凉薄得好似冬日冰河里的那一层薄冰,道,“没有,光棍一条,又有什么好牵挂的。”
幽冷的地牢里,白日与黑夜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他窝在稻草里,伤口发了炎,脸颊因为低烧变得滚烫,与周围凝滞的空气一接触,只觉得又冷又潮。
很多年前他也是这样接近死亡的,在犯人塔里的第二年,他们一家受尽了各种折磨与奴役,他的父亲和母亲终于没有熬过那个早春,他们的尸体被丢到了冰天雪地里,他知道的时候,已经那雪地上已经只剩下几根残骨和一滩血迹了。
——给我血肉,授我魂魄,到最后,竟是连他们的尸首都不能保全。
那时的钟檐站在城墙上望着一片皑皑白雪中触目惊心的红,听着远处不是传来的豺狼的狼嚎声,竟是哑然失音。
他的身后是不停用鞭子麻木鞭笞的狱卒,眼前是和他一样背着矿石向上攀爬的冷漠的人群,那时与他们统统无关的死亡。
一整天钟檐都是怔怔的,谁叫他都听不见,一直到了天黑劳作结束,小妍从纷扬的大雪里跑过来,小手便揽住了钟檐的后背,喊了一声,“表哥。”
钟檐机械掰开小妍的手,温和道,“别,我身上脏。”
“哥哥,舅舅和舅母都不在了。”小妍的手却固执地箍得越发紧。
——她叫的是“哥哥”,而不是表哥。
她说,“哥哥,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
钟檐质疑着转过头来,想要用手去拭去妹妹脸上的泪痕,却忽然停住了手,再抬头,眼眶已经变得通红。
北地的雪密密匝匝,以一种无可抗拒的姿态席卷了这片荒原,雪本质洁,可是又有谁能够知道这一片雪白下埋葬了多少了荒魂。
以后,也会有小妍,也会有他。
跪在雪地里的青年一直脊背挺直,隐忍不发,他很想不管不顾的“哇”的一声恸哭出来,宣泄他心中的伤心和害怕,可是他是哥哥,是一个女孩儿的脊梁,所以他不哭也不能哭。
在犯人塔的那段岁月里,时时刻刻都要与死神擦肩而过,好几次,钟檐也会忍不住奢侈的想,他会看我一眼吧,哪怕一眼。
三十岁的钟檐却再也不会这么想,失望过一次,再也不想失望第二次。
所以他说他了无牵挂,可是那人偏偏出现在他的面前。
谁也不知道是他是怎么进来的,或者说知道的人现在都已经被迷香迷倒,牢笼是出奇的安静,静得实在是不正常。
钟檐觉察出这一点时,申屠衍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小声说,“我来带你走。”
钟檐起初觉得是幻觉,后来了解到不是,挑眉淡讪,三分玩笑三分不是,“想不到你还没有卷了我的银钱跑了?”
“说得什么混话,我是来带你走的。”申屠衍说着便伸手来拨他的衣襟,才触到他的肌肤,就觉得不对,阴恻恻的,竟是死人的温度。
申屠衍猛的缩回手,仔细看去,两双手又红又肿,肿得比萝卜还大,他骇然,钟檐却是冷淡不以为意,“不过是废了双手,再也做不了糊伞这手艺活了。”
申屠衍点头道,“没事,我们还有在云宣还有产业。”说着,试图要把他背起来。
可是瘫坐在地上的人却迟迟没有动作,只冷冷的着他,那眼光,好似黑暗里的一把如雪匕首。
“你怎么了?”申屠衍停下动作,不解的问。
钟檐的脸上根本看不出什么,或者来说根本没有表情,许久轻轻的哼了一声,看如那人的眼中。
“申屠衍,你究竟是什么人?”他一字一顿,轻描眉淡写的一句话,竟然掺上了三分鸩毒。
申屠衍回过神来,没有怒容,反而笑了,“钟檐,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人。”
申屠衍暗暗想,他是什么人?是元宵夜里被他买回来的胡狄奴,是他拒婚以后披着新娘礼服疯跑的大傻子,是早春巷子里固执的说着“我陪你不正常”的大木头……原来,他一直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钟檐继续说,“我想你也知道,王乾一来了,他们又怎么能轻易放过我,这地牢里如铁桶一般,可是,你的腰间却別着牢房的钥匙……我刚才一直在想,什么人有这样的神通,刚才我突然想到我去见赵太守的时候,你故意找理由不去,原因只有一个,腹泻,你怎么不说你来了葵水?赵太守认得你,而那时你不过是我们的一个家奴,认不认得,又有什么要紧……我时常想,从你重新回来那日起,那些前尘旧账就纷至而来,怕也不是巧合,而你现在,又要把我带出牢去,又到哪里去,黄泉还是人间?”
钟檐顿了顿,“申屠衍,这十一年来,你究竟是做什么营生去了?”
申屠衍愣了好半响,才回过神来,面容缓和了七分,到了最后,竟变成嘴角若有似无的笑意,他说,“我早就盼着你这样一句。原来你也不是全然不在意的。”
——我从来没有不告诉你,只是因为你没有问罢了。
☆、第四支伞骨·合(上)
——你究竟是什么人!
钟檐记得,当年想要问申屠衍的也是这样一句。
钟檐站在自家的庭院里,柳荫池水暖,绿肥海棠瘦,才发觉,永熙十三年的春日终于到了尽头。
这一年,迁都议案被撤,无人再敢提起,其实,谁都知道,这样的结果却不是杜荀正殿试抗旨的结果,杜荀正不过是被人摆上案头的那个人,而谁都知道,这不过是缙王与萧党斗争妥协的结果。
皇权中幺子独大,绝非福音,皇帝需要一股势力来平衡这朝局覆倾,而萧无庸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在皇帝的视野中,此人圆滑得体,可是该狠下心肠时便是神佛屠尽,皇帝看到这个人时,如同一个迷途的人在茫茫夜色中寻到了一盏灯,无论这盏灯照亮的夜色是断崖也罢,是歧路也罢,也不得不走下去了。
可是另外有一个传言,从庭院宫苑深处传出,流传在宫女和太监的交头接耳和窃窃私语中,成为大晁皇宫中众多秘闻禁忌中的一桩。
永熙十三年,钟檐的父亲再遭贬,百吏之末,已是不能再贬,钟弈之自嘲,若是那一天这顶乌纱真被摘了去,就还乡去做教书匠去。
“我记得当年还同你姑父戏言,如果不中,就一起办个私塾谋营生,我的字,守廉的画,还愁什么桃李疏落?”
钟檐知道父亲嘴上虽然这么说,可文人,千古文章总是讲究“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到底是意难平,也不戳破,“父亲文章风流,要是我,没了这两俸禄,倒正是身无长物了。”
钟父笑嗔,“那还不学些傍身的伙计去。”
那是大浪滔天之前东阙城中最后的宁静时光,父严母慈,小妹嫣然可爱,倒真是偷来的和乐时光。
再睁眼,梅雨已至。
密密匝匝的时光交织在梅雨细密的雨水中,钟檐嫌这雨水喧嚣,唤了一声,可话到了嘴边,竟成了那人的名字。
申屠衍从外屋赤脚而来,转眼已经守在床前,俯下身来,轻声问,“被雨吵醒了?”
钟檐望着他认真的脸孔,仿佛下一秒便要上天入海捉来龙王商量着能不能不落雨了,噗嗤笑道,“你还能让这雨停住?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本事?”
申屠衍窘到一处,道,“行云布雨的本事我是没有,但是我却知道你睡不安稳是因为心中装着事……”
钟檐一愣,发现那人的脸已经无比逼近他的脸,大骇,“没事了,还不快去睡。”见那人慢慢撑起身体离开,忽的又抓住了他的手,“我的意思是躺倒我旁边来。”
申屠衍听闻,果真安安静静的躺在他的身边。
雨滴答滴答沿着屋檐落下,扯成将断未断的银线,他们的发丝细细交织着,双手交叠着,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暮春时节虽然不算顶人,却有一股扰人心绪的燥热,血气方刚的青年男子,总是免不了纠缠一番的。可是终究不敢弄出声音,他的父母的寝居就在不远处。
虽然申屠衍与他躺在一处,从小便是司空见惯的,可是终究还是不同了,本来光明正大的事情也非要欲盖弥彰一番。
良久,才分开。
他伸出手去擦男人额头上密密匝匝的汗水,忽的道,“喂,大块头,我们这样算不算是在偷情?”
戏文里边都是这么写的,红衣婢女相中了羁旅投奔的谋士,便是一个托乔之盟,唐玄宗遇到了杨贵妃,便要许一场连理比翼,古寺里的女鬼遇上了寺庙避雨的书生,便是一场兰若遗梦,可是两个大男人,不知道算什么?
许不了花好月圆,也许不了白头齐眉,能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