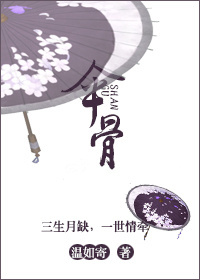伞骨-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每一日,她穿过市集,总会捎一壶酒,几斤羊肉回去。
申屠衍身上的伤都已经结了痂,只是动作不协调,反应能力也很差劲,时常会打翻盘子,跌倒,她进门时候,他正望着一地的瓷碎片皱眉。
“大哥,我来吧。”秦了了接过扫把。
“我以前也是这么笨的吗?”申屠衍疑惑抬头。
秦了了不知该如何回答,勉强笑道,“怎么会,大哥的武功很好,以一敌十都不在话下,一定是因为伤了筋骨才会这样,会好起来的。”
男人还是继续看着自己的手,努力回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秦了了想着昔日申屠衍的模样,忽然鼻中酸涩,勉强的笑道,“大哥,我给你刮一刮胡子吧。”
申屠衍此时想起自己已经很多天没有照过镜子,摸了摸脸上胡乱生长的络腮胡子,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秦了了找来矮板凳,让申屠衍坐在上面,又打了一盆清水,用水沾湿他的脸,用小刀细细的刮了起来。
申屠衍任凭姑娘摆弄着,忽然想起什么来,终于憋不住问,“姑娘,你是我的亲妹子吗?”不然,怎么一口喊他一声大哥?
秦了了笑了笑,摇摇头,有将男人的发髻散开来,用梳子梳得光滑,“大哥,我是你最好的兄弟的妹子呀。”
申屠衍应了一声,缄默了一会儿,“能不能给我讲讲以前的事情吗?”
秦了了点点头,“大哥是一个英雄,就是大哥把我救出来的呀。我很小的时候,我的阿哥就死了,阿哥临死前告诉我会有大哥来接我,那时候我被人贩子拐卖,就一直等啊等,终于等到大哥来接我,我们翻过围墙,一起逃了出来,然后来到这里,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
申屠衍想了想,似乎有点印象,“我们就没有到过别的地方吗?”
“没有。”秦了了将男人的脸掰了过来,去刮另一边的胡子。
申屠衍仍然皱着眉头,一点也没有注意他身后的姑娘已经涌出了泪水。
她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甚至连自己都要信以为真了。
她想,如果这样一个虚构的故事是真的,该有多好?
☆、第九支伞骨·承(下)
每一日;秦了了都要给申屠衍讲一个故事。
那一些故事,秦了了心里,认定了都是发生过的。如果那个时候她知道有平行空间这一种东西,那么那些故事她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解释为另一个世界里的申屠衍和秦了了所经历过的。
比如她四岁的时候一个人逃出,因为太饿了;偷馒头被打个半死;而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他们从奴隶主手里逃出;在雪天的大晁都城一起分一块馒头;
比如那一年主人的乐坊看中了她,只要留下来,就可以不用再挨饿受冻,却没有人问问她一句愿不愿意;而另一个世界的少年跑了十里的路;去告诉她;如果她不愿意,也不要勉强自己。
比如她在城墙上跳下来,那个男人接住她,却最终放弃她,而另一个故事,他们一齐骑着一匹马,就这样一直跑一直跑,然后再也没有卷入政治的漩涡中。
她讲着这样一个个故事,信以为真是她,入戏的也是她。
“你怎么哭了?”
秦了了含着眼泪笑,“大哥,没什么,我只是心里太高兴了。”
申屠衍想着这个姑娘真是太奇怪了,又哭又笑的,秦了了终于给他刮好了胡子,清清爽爽的模样,真是好看,只是……她瞅了瞅他破烂的衣服。
秦了了便说要给他添几件新衣裳,也不顾他愿不愿意,拉着他往街上跑,黄昏的街头,余光将人的影子拉得颀长,秦了了就像一只蹦跳的麻雀一般,小摊上有什么物件,都要在申屠衍身上试一试。
她给申屠衍购置了一身胡狄人的衣物,穿在他身上,倒是有模有样的,她又把一把胡狄人的佩剑在他身上比了比,皱眉,“不好。”
“怎么不好?”申屠衍摸着那兵刃,隐约有种熟悉的感觉。
秦了了却把他拉到一边,“大哥,前面好热闹,我们去看前面的。”她知道离拓跋凛规定的期限还有两天,不到最后一刻,她还是不想面对。
申屠衍被推推攘攘送到了人群的中央,这么热闹,原来是在征兵。秦了了脸白了,想要拉男子走,却怎么也拉不动,她早该想到,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真正的桃花源的,战争的余火终于还是波及到这个边陲小镇了。
申屠衍跟一个木桩子一眼,终于被挤出来,他望了一眼秦了了,那眼神让秦了了陡然一惊。
他知道这个姑娘对他似乎是有所保留的,有些事,似乎是可以不让他接触到的,他不知道是什么,最后淡淡问了一句,“你很怕打仗?”
“怕,当然怕!我的阿哥就是死在战场上的。”秦了了眼低了低,余光却望见隐没在人群中拓跋凛的眼线。
她退后了几步,却知道退无可退,她慢慢抬头,额头渗出细小的汗珠,“大哥,如果说有一个贵人赏识你,想让你去他的兵营,你愿不愿意?”
申屠衍一愣,大笑说,“就这事啊,好啊,你不是说我以前是万人敌吗?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如果我说不许呢?”秦了了虚弱地看着他的眼睛,半响,才扯出虚弱的笑来,“骗你的!要好好的呀!”
那个小孩儿在伞铺子里待了两天,那小孩儿有时候乖的跟一只兔子一样,有些时候却讨人嫌的很。
这个小孩儿讨人厌的地方在于,你以为他什么也不懂,却发现小孩儿原来是什么都明白的,这样就很没有做大人的尊严。
谁家养这样一个小神仙精儿,指定被气死。
比如小孩儿专心致志看一本书,皱着眉,应该是不知道是怎么念,钟檐正要教他怎么念,小孩儿居然扯出了一堆连钟檐也没有听过的子经典籍出来;
又比如,小孩儿大眼珠子一眨不眨望着钟檐干活,钟檐放下手里的刻刀,望了望手里的小木马,引诱道,“喜欢吗?想要吗?”小孩点点头,又马上摇摇头,“没有我阿爹送我的好看……”然后从脖子里拉出一只纯金的貔貅。
又比如钟檐将十一支伞细心妥帖的收拾起来时,就看见小孩儿不停往这边瞥,“你看什么?小孩子家家的?”小孩儿将眼一撇,冷哼一声,“哼,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懂,一定是被你老婆甩了,你老婆跑了,所以你才抱着她的东西哭哭唧唧!你这个弃夫!”
小孩儿奶声奶气,自然被钟檐狠狠的虐了一顿,于是钟檐晚上连饭了也顾不上吃了,只和小孩儿两个干瞪眼,比赛鼻子通气。
因为喝了几盅酒,钟檐睡了很早,到了后半夜,竟然神奇般的睡不着了。
他去瞅了一眼那小白眼狼,正呼呼睡得正香,轻轻骂了一句,小白眼狼!
三更半夜的,钟檐却精神的不行,特别想拉了一个人秉烛夜谈,可是大晚上的,别说个人。连只鬼都没有。
钟檐眯着眼,跌跌撞撞就往桌子上撞,撞了个大包,哎呦哎呦直叫,他抬起头,看见桌子上的灵位牌子,抖了一激灵,指着它骂骂咧咧,“好呀,你也用桌子绊我,你也欺负我!”
他作势就要打那灵牌,却忽然改变了力道,抱起那灵牌,捧在怀中,将脸贴在上面,木质的纹路硌的他难受,冰冷冷的,没有任何温度。
就在他都要以为自己都要睡去了的时候,他忽然睁开了眼,缓缓发出几不可闻的声音,“申屠衍,连你也敢不要我了,是吗?”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吃得惯你的做的菜了?
——你是不是最近我不打你,埋汰你了,你就骄傲了?
——你以为你有多重要?我才不会为你难过,一点点也不?
他一遍一遍的埋怨,他其实记得的,今天是那个人的头七,他应该是会回来的吧,所有他要把他过得不好都告诉他,让他在天上,也不能够安心。
所以他应该是听得见的吧,可是那又怎么样呢?两个男人,越过了兄弟的界,圆不了福气的缘,他们之间还能有什么纠葛呢?想到这里,他忽然很是难过起来。
他忽然弯了眉眼,笑得很好看,“喂,我们,还没有成亲呢?”
——喂,我们成亲吧。
这样我就有理由了吧。
他的眼里,仿佛盛了星光。
冯小猫是被声音吵醒的时候,揉了眼睛睁开,发现屋里变了模样,一对龙凤喜烛将屋内都笼上一层光晕。
小孩儿有些呆,看着那个古怪又毒舌的叔叔穿着一身红,将另外一身红放在椅子上,椅子上孤零零的摆在一个灵位。
钟檐笑了,是冯小猫不熟悉的温柔,他说,“当时让朱寡妇改衣服,没想到现在改合适了,反而没关系了。”
他转过身来,看见冯小猫,并不惊讶,反而招呼他过来,“小孩儿,我们都没有高堂和亲人,你愿不愿意见证我和我媳妇儿的婚礼?”
小孩儿点点头,坐在宾客的高高的坐席上,成为这场婚礼唯一的宾客。
——也是这场特殊婚礼唯一的见证者。
钟檐抱着灵位牌子睡了一夜。
清晨,却是被朱寡妇的大尖嗓门喊醒的。
“钟师傅,快起床!你不知道谁回来了?”
钟檐睡的脑袋有些懵,推开阁楼上的窗户,清晨的雾气迎面而来,他打了个哈欠,没什么精神地低头问,“谁回来了?”
朱寡妇站在清晨的街上,身后是早起忙碌的人们,她站在正中央只是一个小点,可是钟檐却似乎能看到她眉飞色舞的脸,“还有谁?你媳妇!你媳妇回来了!”
作者有话要说:冯小猫童鞋只是穿错了片场,俺就让他爹把他接走
☆、第九支伞骨·转(上)
钟檐站在窗户边上;睥睨着低下的街道,云宣街道纵横错杂,一眼看去,一座牌坊后面是另一座牌坊,他顺着目光数过去;终于到了尽头的牌坊。
隐没于晨光;一片寂寥。
——那下面站着的人;是他吗?
钟檐回过神来,轻轻的“哦”了一声,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他又将这轻巧的发音回到舌尖绕了一遭;仍旧品不出什么滋味。
朱寡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前些天哭丧着脸,现在人回来了,跟没事人一样,拖了钟檐就往城门的方向跑,嘴里还不停的叮嘱着,“我说小钟呐,现在人好不容易回来了,你可要好好待人家了,别一张嘴不饶人了,偷偷跑了是他的不对可也别太苛责了,说说就行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吧……”
钟檐走了大半个云宣城,脑袋还是懵的,他说不上来这种感觉,好像与他擦身而过的风,好像什么也抓不住,又好像它一直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就像他一生遇到的很多事物。
——那么这一次是不是可以试着抓抓看?
他一路跑,跑的气喘吁吁,离着城门外的牌坊几百仗的时候,终于站定,来来往往进出城门的人有那么多,却没有他想要找的那张脸孔。
“愣着干什么呀,快过去呀,你媳妇!”钟檐终于在朱寡妇的推搡中看到了来人。
“你是?”钟檐有些懵。
裹着蓝花头巾的妇人望着钟檐,咬了咬唇,那表情好不精彩,巴巴的望着,珠圆玉润的脸庞好似一轮斗大的玉盘,却非要演了一出王宝钏寒窑苦守。
钟檐被那女人看得全身发麻,她才开口。
“相公,你不认得我了?”对面的妇人双眼干涩,挤了半天也没有挤出几滴泪来,不好意思,开始大声呜咽,“罢了罢了,你如今财运亨通,记不得我也是应该的。”
朱寡妇忙上去拉住那个女人,朝着还迷瞪着钟檐使眼色,“你老婆,蒋明珠,你该不会不认得了吧?”
他望着那布裙荆钗的女人,想了很久,印象中隐约记得,自己是大概,也许是娶过这样一个女人的。
那时钟檐来到云宣的时候,北边的战乱已经平息了,他衣衫褴褛的站在被雨水打湿的牌坊下,看着周遭忙碌的人们,他是置身事外,格格不入的外乡人,也不知怎么的,他忽然想要留下来。
他那时不过二十来岁,真正走出来的也不过这样一年,十五岁读的书,二十岁走过的路,都比不上真实的日子来得深刻。
刚开始他初来乍到,在异地活下去,其实什么不容易的,索性还有一门手艺,起初他是扎了纸伞,挑着担子挨家挨户去吆喝的,官家出来的少爷起初磨不开面,生意惨淡,维持生活很难,可是终究还是要活下去,即使收起所有的逆鳞。
走街串巷过了小半年,他终于有了自己的铺子,正好那时隔壁家的王媒婆刚金盆洗手,在家里闲得十分难受,看见钟檐这样一个未婚人士,简直要冒亮光,一来二去,把她手上那点资源统统要说给他。
那时钟檐有了一间毛坯房,想着要有一个家,也是需要一个女主人,就应了一门婚,蒋氏他在婚前不曾见过几面,只隐约记得是一个喜爱大红衣裳的姑娘。洞房花烛夜他喝得昏了头,更是没有看清,等到想要好好看清自己媳妇的时候,她媳妇已经跑了。
只是这体型……大概变得有些忒出格了。
已经从当年爱穿红衣服的小姑娘变成风中摇摇晃晃的大灯笼,真是女大十八变,临老了她也要变三变。
钟檐舔了舔唇皮,有些尴尬,也不知该叫她什么,“你怎么会来了,你不是跟那个大盐商走了吗?”他的第一个老婆是跟着来云宣进货的大盐商跑的,他记得很清楚。
蒋氏这才停止了抽泣,“相公,以前是我错了,我对不住你,那家伙太不是东西……”她抽抽搭搭,好久才把事情说清楚了,原来在年初的时候,那盐商翘了辫子,把财产全留给他的儿子,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把她赶出来了。
“我以前不懂得,现在才知道,只有相公才对我最好……”她一口气没缓过来,竟然晕了过去,钟檐无奈,在朱寡妇的殷切眼神下,只能暂时把蒋氏领回家。
而这个女人一沾床,就没音了,钟檐没法,领着在门口探头探恼的冯小猫出门去。
钟檐低头干了一会儿活,却听见对面坐在竹椅上的小孩儿哼哼唧唧,闹个没完,钟檐抬头,好笑,“我说你是屁股里长刺还是鼻子上扎了针啊?怎么光学猪猪嗷呢?”
冯小猫将脸别过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