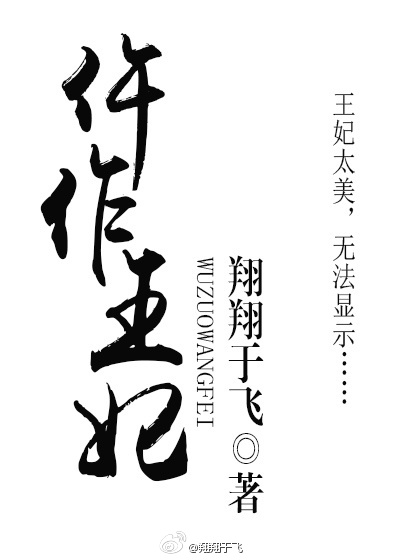滴尽半面妆-第7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快会倾覆整座楼。”
“我不懂力学。”
“《芙蓉扣》是我师傅写的,音调和技巧都是按照一个男旦的要求,我可以压低成男人声线,在这个基础上拔高,所以就算那些戏曲大师也发现不了我的性别。但是下阕《合欢漏》是我自己撰写,必须由女旦才能唱出,而就算溯世五大花旦功底和天赋未能企及。”
“我不懂戏腔。”
女神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气息萦绕:“易恕,不要跟我说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听不见了,你也不用多费口舌狡辩。”
我整个人都茫然了,除了紧紧抱住她,我没办法思考任何事情:“事情是怎么会到这一步的……你是怎么让自己走到这一步的……”
女神只是微笑,她的世界已是一片安静,再听不见只字片语,她重复道:“十秒之内,放开我,滚向任何一个通道,你都可以出去。”
“我不……”
“还有五秒,我也可以扔你。”
“你没有力……”
“还有三秒。”
“滴尽妆!”
她猛地扯开我的手,一个甩身将我推到前方,随后一声高亢带着数次冲击波的尖啸在这逼仄的空间炸破!
什么东西轻微破碎的声音。
黄粱木轰然坠下,溅起一地尘埃!
在那隔绝生死的黄粱木那一侧,她一如既往微笑,面容清绝,意态从容,懒散地靠在一边,露出一个此生此世我难忘的笑容,灿烂一生的光华:“打开手机录音,这将是我此时最后一曲《合欢漏》,也将是世上唯一惊世著作。”
我泪流满面从缝隙中探出手,她却将我回绝,只是淡淡说:“我答应带你去珠峰的,那是个好地方,很漂亮,也很遗憾,原本我给自己准备的墓地,就是那里。”她似乎在摸索着什么,半晌,终于流露出一丝如释重负,递给我一柄圣檀木的掏耳勺,仵官王令,是她最随身的刀剑,“带珠古去吧,然后把它埋在那里。”
我嘶声力竭:“我不要去!我不要去!你自己去!你有本事自己去!”
“我听不见你说的话。”
我嘶吼起来:“你出来啊!你跟我走啊!”
“我说了,我听不见啊。”
“我让你跟我走!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求求你不要死……”
“我什么都听不见。”
言语之残酷,不亚于跟池佼社说的那一句我不爱你。
我将额头磕在黄粱木上,硬燥的树皮划伤了我的额头,血混合着我的泪流淌在我大张的嘴里:“你怎么能这样……滴尽妆你……”
“乖孩子,记得要一直跑,你将是新的仵官王。”她笑容似乎下一秒就无法维持而崩溃,“所以就要像天险缆车那次一样,不要管我。”
整座古楼都在剧烈动荡!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曾经那一曲红遍大江南北的《芙蓉扣》的《钗头凤》起声,惊艳了岁月,抚平了光阴,尘埃弥散间,那个绝代风华的妆女神浓妆妖娆,却又清冽如酒。
她仰望着古楼之顶,乌浓的眼睫如黑羽,如同我初见她的时候,她从宿妆残的顶楼伴随红纱落下,明艳又悲黯,洒下风情万千。
我泪如泉涌,转身离开。
“独酌瘾,难怅景,往来曰破茅檐酩。孤身晾,今宵眠,不堪犹醉,那时然弘。纵、纵、纵!
仇需候,别难就,夜雨滴尽三千漏。斑驳酿,浑浊香,京都长誓,何言坟冢。重、重、重!
白衣卷,佩里雪,吹萧则为衣冠敛。邰秋岁,何期回,今生弃楚,来世偿抛。报、报、报!
鬓边创,颈留戗,筑中为故霜天将。流云散,清风局,九千荼满,朝夕作袍。缪、缪、缪!”
黄粱木一根接着一根,在这绚丽的唱腔之下崩溃砸落,尘埃四散。
我听见遥远的拍子声,一声一声,悠长清雅。
她在默默倒数着自己的生命,冷静的,从容的,漠不关心的。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起声唱腔再度拔高!
这完全陌生的词谱,却高唱出舟过万年的凄厉,那一曲《合欢漏》竟是如荆棘鸟一般充斥着万劫不复的血啼。
这最后的一首绝唱,蕴含着那四年的痛苦,这九年的愤怒,如同妖魔的悲鸣,在这翻天覆地的坍塌中抨击着整个天地!
“知交曲,枯荣惧,且尽尘缘无所欲。几疏狂,越贪光,轻弹雨迹,眉间无殇。伤、伤、伤!
烹茶调,荏苒料,芳情再难委以笑。近清绛,千年香,穿梭百丈,无处说捺。那、那、那!
凝眸处,蒹葭祝,不朽万古长空固,饮屠苏,渡巫溯,金戈铁马,把酒邀户。孤、孤、孤!
兴亡有,癫狂拗,图穷霁月扶乩流,殁曾俎,愿来否,难知缟素,踏破流骨。哭、哭、哭!”
光风霁月,长空万里,我扫开了一切的尘埃,将古楼抛在身后。
那一声尾音,冲破了无数横梁屋檐,刺透了整个时间空气,划裂了遍天乌云雷雨!
世间所有声音都无法达到那一次的震撼,绝死之时的悲鸣,用尽全力的疯狂!
天地共震!
下一刻,宿妆残最高处的衡量木在这声波中猛地砸下!轰然一声响后,最后的声音被霎时掐灭,一片安静。
寂地一般的恍若隔世。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手机按了储存键,却还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芙蓉扣》与《合欢漏》,我恍若未闻地望着漆黑的万里苍穹。
什么是命运?什么是人生?什么是爱?
太晚了,我还是太晚了,这一场姻缘的起始,我就来晚了。
滴尽妆的人生已经被毁去,以她不可原谅的方式。
你们明知道她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她的骄傲比宫妆更甚,已经刻在了她的骨头里,可你居然做到了将她挫骨扬灰。
……难道不是在逼她死么?
我直到现在才知道,原来我在最初遇见她的时候,她就已经在设计自己的死亡。
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一个人,可以这样为了骄傲而忍辱负重,而竭心尽力,而执迷不悟以致于死却不悔。
她为骄傲而活,也为骄傲死去。
我忽而放声大笑,背后十里废墟,万丈火光。
笑着笑着,就再度流下泪来,我伸手一摸,满脸的辣痛,直锥入心脏。
江山如画,锦绣河流,与昨日此时并无不同。
可这茕茕孑立的秦淮河畔,谁能再为我唱一曲滴尽半面妆?
作者有话要说: 射射能看到这里的看客们,坚持追到这一章也挺不容易的。
接下来放预告:第一百章,易恕后续收尾工作
第一百零一章,滴尽妆17岁至28岁(高戴约视角番外)
第一百零二章,宫半面4岁至15岁(应水卿视角番外)
第一百零三章,姐姐随记(宫妆视角番外)
☆、黑白人生
宿妆残古楼已经完全变作废墟,天亮后孟婆亭的人马完全包围了这里,所有人脸色的肃穆,在风中长久地伫立,呼吸萧索。
高戴约良久地沉默,他的肩膀上围了一圈黑纱,在风中被吹起落下,仿佛是娇柔的花瓣。
“彻底封锁宿妆残古楼。”他最终挥手说道,“五月气温还略寒,快些请出妆爷吧。”
乌云笼罩着秦淮,沉闷的空气仿佛包裹着雷雨,几十台挖掘机拼命清除着废墟的边缘,努力开辟出一条道路来。
我茫然看着所有的画面,却停止了一切的思考。
核层四人一一到场,他们静默着,清点着楼内挖掘出的宿妆堂杀手尸体,一共十一具,刚刚好,宿妆堂全军覆没。
马路边突然传来撕裂耳膜的刹车声,随即岱尔尔出现,她罕见的一身白色,素面朝天,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交给了旁边的高戴约:“女神的遗嘱。”
高戴约怔住了:“她对每个人都安排好了,怎么还会有遗嘱?”
“关于宫妆的,她要求器官捐献。”
“万岁爷得了什么病?”
“咽喉癌。”
紧接着又是一个车队,小己背后的医师团站成了一排,他低头仔细消毒自己的手,然后抚过那一柄柄真空包装的手术刀。
“我先去了。”小己抬头,面容是万寂后的冰冷。
然而他去过后,不到一会又返回,在高戴约耳边说了什么。高戴约微微蹙了眉,随后看向我,突然走了过来,掀起风衣下摆,单膝跪地,低声道:“仵官王大人,我们不敢对妆爷肆意动作,劳请您出手。”
我被那一声仵官王惊得后退,半晌怔怔道:“什么?”
“妆爷的手覆在咽喉处,我们不敢强行取下。”
我一生都不敢相信我能看到那么残酷的场景。
那个逼仄的空间已经有一面被搬开,中间的那个身影没有靠在任何一面上,却依然站立,一根尖锐的横梁斜刺入她的心口,贯穿,再牢固地掷入地下。
她低垂着眉目,清绝恬淡,浓妆艳绝,一如曾经。
但她的嘴唇是浓烈的暗红,大片大片的血将浅绯色淹没,流入黑色的衣襟,蔓延开大朵的血污,像是繁花绽放。
“仵官王大人,请吧。”
我虚浮着脚步走上前,手指触碰到她的脸上时,颤抖得不成样子,我凑过去轻轻吻着她的嘴唇,哀戚地轻唤:“女神……”
她再也听不见。
她再不会说我听不见。
我摸索着她扣在自己颈处的手,努力温暖,慢慢撇开手指,缓缓将之放下。随后小己就上前,向我恭敬而疏离地行礼后,旁边医师们都备好了阵势,开始完成她曾经的嘱托。
手术快捷而迅速,医用保温箱中很快取够了移植用的部位。高戴约跪在我身边,轻声道:“仵官王大人,妆爷生前曾有过谕令,要求火化,请您松手。”
我猛然一惊:“火化?”
“是的,请您松手。”
“不!”
“请您……”
“戴约,你先去找人把这横梁截断吧。”岱尔尔忽然出声,随后她蹲在我面前,面无表情,“易恕,女神有段话给你,就在遗嘱里,你跟我来。”
“我不去。”
“好,我拿来给你看。”
岱尔尔拿来一方便戈,递给我,最上面是曾经有过的一句对话,发生在不久前,那时天光明媚,医院外的绿化带还是初见茵茵。
——你要逼着自己相信我,那么最终,你一定会活得比我久。
——我相信你是因为我爱你。
“爱情是什么?”
“我感受过爱一个人和被爱,但从来都不明白爱情。”
“也许爱情只是一种依赖,你失去了我,但终会习惯,于是你不再依赖我,爱情就会慢慢淡去。”
“从今后,你要开始逼着相信自己了,易恕。”
“学会爱自己。”
岱尔尔居高临下看着我:“你抓不住她的——她如果想走,谁都抓不住她。”
她的话语那么轻柔,却如此残酷。
“你抓不住她的,所以烧了吧。”
烧了吧,白骨溶沙,握不住,留不下。
烧了吧,泥流入海,再不见,再不念。
洒向这锦绣山河,融入这孑孓世间,只闻故友遗留哭三遍。
粉墨苍生。
一别天荒。
… …
一代当红戏曲大师滴尽妆逝世的消息几乎炸翻了全国各地,所有人在极度震惊之下几乎都是不相信的——这是一个当代最美丽的传说,传说怎么会死呢?
同时我将那卷背景音仅为断木轰响的绝唱录音递交给了中国戏曲界,没有鼓瑟伴奏,只有房梁倒塌的重响,但那唱腔带着令人窒息的美感与绝望。
“绝世之作!这就是《芙蓉扣》的全曲么?”
我垂眸看向自己的手,轻声道:“不,它名为《滴尽半面妆》。”
不多时,宫妆从美国回归,我见到她是在G。BMZ集团的司戎大厦的董事长办公室。
听到我的这一声开门响,那背对着高背椅转了过来,上面坐着的人一身雪白,长发散落,抬起的脸映照在阳光下如同玉石。
即便她的面容带着冰冷,声音嘶哑如斯,我还是出神了很久。
宫妆冷冷问:“宫半面在哪里?”
我微笑道:“我知道女神在哪里,但是我有点怕你,你做个手术,植入一个东西,我就带你去找你最爱的那个人。”
宫妆沉默地看了我很久,同意了这个手术。
走出司戎大厦后,我通知了小己:“我搞定了万岁爷,接下来的,就看太医的本事了。”
迟溶是在五月六号清醒过来,妆女神逝世的后两天。她醒来就面对着一个全新的迟家,没有池家的暗算,也没有单家的侵蚀,独属于她的溯世和迟家。
可惜她的六七个月的孩子并没能长大,死于五号,仅是她醒来的前一日。
迟溶整个人都消瘦了一圈,面容憔悴,她惶惶然地找到我,问道:“妆爷……妆爷怎么了?我是不是又惹她生气了?我不是故意的,我……我签了和单继谅的离婚协议书……”
“这和单继谅没关系。”
迟溶又茫然又惶恐:“怎么都变了……我只是睡了一觉……怎么醒来都变了……”
“世界总是在变的,你睡得有点长。”
“她……”迟溶忽然低头,揪住自己的衣角,眼泪啪啪地落下,声音都被泪水浸得含糊“妆爷她……她没有话跟我说么?”
“没有。”
女神仅设有一处衣冠冢,濒临宿妆残古楼的遗址。
当这座衣冠冢建成后,应水卿曾经过来,他形销骨立,大病初愈,仿佛承受不住那套庄重衣饰。
“我记得如果按血缘来说,你算她表兄。”我走向应水卿,看着他的眼睛,“那你还记不记得曾经那个叫做宫半面的人?”
应水卿喑哑道:“我记得。”
“那你还记不记得曾经倾倒众生的滴尽妆?”
“我记得。”
“可是现在你看看女神,你看看她,可还能找出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