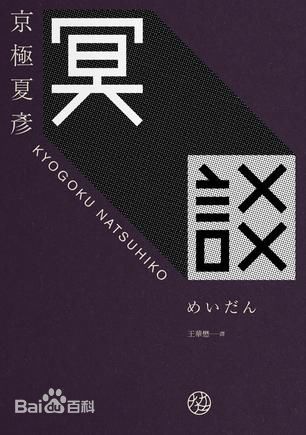冥谈-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嗳,是啊。可是那应该也在一瞬间就结束了。你先生或许……”
连自己死了都没发现。
“他在最后看到了什么呢?”
什么也没看到。
我是这么想的。
就算看到了什么,他在理解到那是什么之前,也已经死了吧。愉快、欢喜、悲伤、空虚,应该都在一瞬之间消失殆尽。就像电灯泡熄灭那样,倏忽消失,一切变得漆黑。
这间和室怎么暗成这样?现在不是还是大白天吗?简直跟傍晚没两样。
佐弥子很白,所以我看得到她,要是土黄色的小山内,可能已经融入黑暗看不见了。这是内就是暗成这样。
“如果看得到什么,应该是回忆吧。”我说。
像是怀念的景色、心爱的人、美丽的花朵,这类东西,这样不是比较好吗?
“我以为他看到的是自己的血。”
“自己的血?”
“因为被压碎了嘛。”
那个人的头——佐弥子说,
“头都没了啊。头盖骨破碎,里头的东西全跑出来了。我一想到他在那瞬间是不是看见了这一幕……”
就难过死了。
“看到自己脑袋里面的东西,看到那么肮脏的东西,然后死去,不教人伤心?不教人害怕吗?我怎么样就是无法克制自己不去想那种事。你怎么想呢?西宫兄?”
没……
“没那种事的。”
“没那种事吗?”
“你先生应该不觉得痛,也没看到什么脏东西吧。因为他是毫无预警地突然就过去了啊。”
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佐弥子这次以极端沉稳的音调说。她身子歪靠在一旁的姿势非常妩媚。
那白皙的脖子。
纤细、通透的颈脖。
“哎呀,对不起,说什么连茶也没端,招待不周,却连我都没好好招待。真不像话。”
“不,不用麻烦了。我只是临时起意,碰巧过来看看而已。可以像这样和怀念的朋友说说话,我就很满足了。”
好怀念。
“话说回来,哥哥也真慢呢。”
“医院很近吗?”
“我不清楚。”佐弥子歪着头,“哥哥状况满糟的。我要他住院,要不然至少请医生过来出诊,他却怎么样都不听劝。都这种时间了,还没回来。”
“这种时间?”
太阳已经西下了吗?
“很冷呢。”
“很冷吗?”
会冷吗?
“家里没有生火,非常冷啊。待在这屋子里……”
——会冰得像条鱼似的。
那……
不是因为你已经死掉的关系吗?
“佐弥子,”
隔壁房间有什么人在休息吗?我问。
“有人在休息?可是这个家里……”
只有西宫兄跟我两个人啊。
是啊,只有我跟尸体两个人。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我这么想着,将不知为何一直别开的视线拉回来,看见佐弥子不知何时坐到了房间角落。
“怎么了?”
“没事,我来泡茶吧。”
佐弥子说,打开铺有被褥的房间纸门,消失在漆黑的邻室里。纸门关上的时候,我好像瞥见了被褥的一角,也闻到了线香的味道。
又变回一个人了。
我就这样坐了一会儿。
小山内怎么了?他平安地抵达医院了吗?他的病况果然很糟糕吧。
不知为何,我用双手按住自己的头。
万一被压碎或掉下来就不得了了。
我应该活着吧?
我望向庭院。庭院里山茶花绽放,一旁放置盆栽的木台是黯淡的灰。台上空无一物,缺了角的盆栽排放在地面,稀稀落落地生着杂草。山茶花娇艳欲滴。叶片厚实,色泽浓重,花朵赤红得近乎艳毒。木台曝露在风雪吹袭中,已经破损,似乎一碰就会分崩离析。腐朽,也褪色了。被雨打湿、被阳光烤干、被风吹刮、被雪侵蚀,已经命在垂危。
像那样慢慢地腐朽也不错吧,我想。
与其突然结束,那样要好多了。小山内嫉妒山茶花,但我不怎么羡慕仿佛倏然断首般迎接死期的山茶花。我想慢慢地逐渐老朽。
外头还很亮。
是大白天。
即使如此,家中已是一片漆黑。
我,
得在这里看家到什么时候?
佐弥子会送茶过来吗?不,不会,她不可能来。线香的味道。弥漫整间屋子的尸臭。鱼一般冰冷、苍白、透明的皮肤。
佐弥子死在隔壁的房间吧。
她的哥哥小山内都这么说了,错不了。
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
庭院里的山茶花,
一口气全掉了。
“啊啊。”
小山内也死了呐,我想。
我得在这里看家到什么时候?
小山内会回来吗?
我回得了家吗?
从这栋有庭院的家。
注释:
①纸门上框与天花板之间用来采光、通风的镂空板。
第二章 冬天
蔺草的香味对我来说是冰冷的。
低温,还有那股香味,我总是成双成对地一块儿忆起。天气一冷,我的鼻孔就嗅到虚幻的榻榻米香;一嗅到榻榻米香,尽管天不冷,我却会依稀感觉到寒凉。
对我而言,榻榻米就是冬天。不是模糊的冬季印象,而是以相当具体的感觉连结在一起。
那种冰凉,是脸颊的冰凉。
更进一步说,是右脸颊的冰凉。右脸颊感受到的粗糙榻榻米纹路那冰凉干燥的触感,就是我的冬天,是冬天本身。这是极为逼真的记忆。我无法清楚地以言语形容,但它是种极为细腻的感觉,甚至还伴随着身体感受令我忆起。有时候我甚至会有股皮肤被扎刺的错觉。而浮现在鼻腔深处的蔺草香,就像我真的在嗅闻榻榻米一样。
然后……
这种记忆,同时也伴随着相当蒙胧的视觉与听觉的记忆。
不过它们的触觉及嗅觉不同,模糊不清,极不牢靠。我不会清晰地想起,而是仿佛隔着雾面玻璃窥看一般。
就像隔着墙壁聆听一般。
那是暧昧模糊、遥远的记忆。是的,与其说不清不楚,更接近遥远。
遥远的记忆宛如梦境。
对……就像是梦的记忆。
虽然记得,却不记得。
细节异常清晰,整体却一团蒙胧,毫无现实感。
因为是梦,不是现实,当然没有现实感;但是做梦的时候,不会觉得这并非现实,刚醒来的阶段应该也无法区别梦境与现实。
尽管如此,梦的记忆却无端遥远。
就像那种感觉。
可是那段记忆绝不混浊。
没有掺杂其他记忆,也没有任何沉淀难辨或是隐晦之处。那是非常透明,而且澄澈的记忆。只是……似乎相当遥远。
那是少女的脸孔。
还有少女的声音。
少女——我觉得应该是少女。我记得那张脸,但我没办法画下来,而且她长得不像任何人,她和我认识的任何一名女性都不像。
我也想过,那会不会是我根据小学或中学同学的印象在脑内塑造出来的虚构脸孔?我当时翻出了相簿试图确认,但记忆中的那张脸,还是与任何一个同学都毫不相像。那当然也不是邻近孩童的脸,更不是在电视或杂志上看到的模特儿或艺人的脸。
那张脸不像任何人。
声音也是。
我从来没听过那样的声音。不……听是听过,但和我过去听过的任何人的声音都不同。我从未听过一样的声音。
只有这一点,我可以确定。
那张脸不是任何人的脸,那声音不是任何人的声音。
可是我能够确定的其实只有这些,此外的一切全都模糊不清。没一样清楚的,等于毫无任何具体的记忆,所以我才会说不像任何人吧。因为如果我记得一清二楚,即便有所不同,应该也说得出像谁吧。
所以,
我现在认为,那或许是一场梦。
可是我也十分相信那不可能是梦。
我会强烈地如此感觉的理由,就是残留在脸颊上的榻榻米那冰凉的触感。
既然在根本之处伴随着如此逼真的记忆,我实在无法认为那只是一场梦,而且那也不是仅只一次的记忆。如果是梦,不可能有那么多次。
我在某一段时期,反复记住了这个事实。
换言之,我看过那张脸好几次,还听过她的声音。
不。讲得更精确点,我确实有着“去年也看到了”的记忆,还有“之前是这样的”,“在更之前是那样的”的记忆。最早是何时看见的,我已不复记忆,可是我一年至少会看到那张脸一次。
好怀念。
怀念得教人心痛。
怀念得就像忆起了死别的家人。
然后,
可怕极了。
我的外婆有许多兄弟姐妹。外婆是家中长女,每年一次,外婆家的族人会在外婆的娘家——也就是外婆的大哥,舅公家众会。
这是惯例了。聚会的日子似乎不固定,但大抵都是在年关将近的时候。除夕和过年时大伙会各自回家,所以应该是圣诞节前后的三四天,也就是寒假期间。
会错开过年,大概是因为家族中有许多像外婆那样的女性。外婆一族似乎十分团结,也没有大家族常见的勾心斗角,每个人感情都很好;但也因为是个老派的家族,认为过年就是要在各自的夫家过吧。因为外婆和所有妹妹都会在过年前返回夫家,而兄弟就留在老家过年。
我出生后的十几年间,每年都被外婆和父母带去舅公家,在那里住上几天。开始上学以后,就配合寒假的时间过去。不过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也有不少年没有去。
外婆的娘家是栋非常宏伟的日式房屋。
外婆家是财势兼具的豪农。不,过去曾是。
我想豪农这个名词,在人们的心目中还具有真实性,应该只到昭和中期左右。至少在我的感觉里是这样的。现代当然也有大农家,但我们不会称他们为豪农。现在的大农家只是有土地、有钱,或是生产量大一些罢了,我觉得这样就叫做豪农,似乎不太够格。从我还是幼儿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么想了。
外婆的娘家从这个意义来看,也是个旧时代的人家。
旧时代的人家又大又古老。
有前院,有中庭,甚至还有后院。有宽阔的木头地板地房间和大客厅,有地炉,还有泥巴地房间。前院再过去是田地,后面再过去是山峦。玄关也很大,我清楚记得偌大的玄关摆满了鞋子的情景。
大批亲戚会聚集在这幢古老的房子里。我到现在还是不清楚,大家集合在一起做些什么。可能是举办类似法事的活动,不过我不会看过侩侣出入家里。
年老的兄弟姐妹带着各自的家眷齐聚一堂,人数当然也非同小可。光是小孩就有十五人左右吧。
我当时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众在一起了,事到如今,更是无从知晓。
长大之后,我也曾经问过母亲有多少人在场,但母亲说她没数过,不清楚。我找出以前的合照确认,人数最多的照片有四十六人。不过并不一定每年都会合照留念,而且有些年的成员变动似乎相当大,无法确定;但我想每年差不多都有这么多人。
将照片依年代排列,幼儿变成儿童、变成少年少女,再变成青年和姑娘。相对地,大人渐渐衰老,然后一个、两个,从照片上消失。
我记得某些人,
也有些人我完全没印象。
有些亲戚,我只记得他们年轻时候的相貌,也有些人,不知为何我只记得他们晚年的模样。大舅公的女儿相当于母亲的表姐妹,年纪比起外婆,应该更接近母亲,我却一直喊她奶奶。我记忆中的她是个老婆婆,但从照片上看来,抱着尚是幼儿的我的她还相当年轻。而我总是喊“大哥哥”的外婆么弟,那张脸怎么看都是个中年男子。
真是不可思议。
我的表兄弟姐妹——也就是以前的那些孩子——也是一样。有些人给我的印象是中学生,也有些人我只清楚记得他们还是幼儿的模样。有些人,我只记得大家一起玩的事,也有些人,我却只留下雨人独处的记忆。有些人不是特别亲,我却记得名字,也有些人一起玩耍的记忆非常鲜明,却怎么样都想不出名字。
真的很不可思议。
似乎到了中学毕业的年纪,孩子就不参加这场聚会了,照片上找不到所谓的年轻人——高中生或大学生的他们。
我也是上高中以后就不去了。有一阵子好像是母亲和外婆两个人去,但外婆过世之后是什么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总而言之,外婆的娘家辽阔极了,大到能够轻松容纳这么多人住宿。
话虽如此,我也从来没有俯瞰过整栋房子,完全不清楚整体的状况。而且也没有平面图,不知道房间数目和大小、占地的多寡。
那是生活空间拘束狭窄的都市人的感受无法掌握的规模,广阔得甚至没办法把它当成是一户人家。
或许是因为孩童身形矮小,感觉更是巨大了。
不管是走廊还是房间,一切都很大,非常大。
像天花板就高得离谱,简直就像体育馆。
可是即使处在这种不合身形的格局中,看到和摸到的毕竟都还是伸手可及之物。
除了广阔的印象以外,玄关的模样我几乎全忘了,但我还想得起来脱鞋处的木框那油亮亮的黑色木纹。嵌在雪见纸门①上的玻璃透花图案是乘在船上的人,还有奇形怪状的茶柜里面装着黑色的茶托等等,这些我都没有忘记。
那栋屋子好像在十年前拆掉了。
家族轮替了两代,可能也有遗产税之类的问题吧。好像重新改建成一栋和土地相比还算大的房子,土地则是分割出售,现在也盖起了公寓。田地也不见了。
就在房子拆除前后,亲戚也不再众会了。
最后一次的家族集会,我想应该是外婆么弟的丧礼。外婆么弟是她那一代最后离世的,从此以后,即使亲戚中有人过世,好像也不会连年轻人都参加了。
说是年轻人,但辈分从底下算起来还比较快的我也已经年过三十了。当时的孩子到了现在,完全没有往来,到了他们的儿辈,我想更是彼此完全没见过。
这些是有关于那栋古老大宅的回忆。
日式房屋很冶。吸湿和排湿性虽然优异,但无论在材质上或结构上,保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