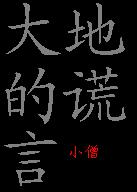安德的代言-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回我的工作站去。”
“出了这种事,可不能让你一个人待着,再说这么晚了。”波斯基娜说。
娜温妮阿受不了别人的陪伴、同情与安抚。是我杀了他,你知道吗?我不该得到别人的安慰。不管多么痛苦,我都应当独自承受,这是我的忏悔、我的赔偿,如果有可能,也是我的救赎。除此之外,我用什么办法才能洗清手上的血污?
但她没有力量抗拒,连争执的力量都没有。市长的飘行车在草地上方飞行了十分钟。
“这是我的家。”市长说,“我没有跟你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不过我想你会觉得舒适的。别担心,不会有人来烦你。但我觉得你不该一个人待着。”
“我想一个人。”娜温妮阿希望自己的话坚定有力,但声音却十分微弱,几不可闻。
“别这样。”波斯基娜说,“现在不比平常。”
真想回到平常那样啊。
波斯基娜的丈夫为她们准备了饭菜,可她没有胃口。已经很晚了,再过几个小时天就要亮了,她由着他们把她弄上床。然后,等屋子里没了动静,她爬起来,穿好衣服,下楼来到市长的家庭终端前。她命令电脑取消仍然浮在外星人类学家工作站里她的终端上方的全息图像。虽然她无法猜出皮波从那幅图像中发现了什么,但别的人也许猜得出来。她的良心再也承受不了另一桩死亡事件了。
做完这件事,她离开市长家,穿过殖民地中央,沿着河边回到自己的屋子——外星生物学家工作站。
屋里很冷,居住区没有加热。她已经很长时间没在这里住过了,床单上积了厚厚一层灰。但实验室很暖和,收拾得很干净。这个地方她常常使用,她从来没有因为和皮波父子的密切接触耽搁自己的工作。真要那样就好了。
她做得很彻底。凡是与导致皮波之死的发现相关的东西,每个样本,每张切片,每份培养液,全部扔掉,清洗干净,不留一丝痕迹。她不仅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毁掉,而且连毁掉的痕迹都不愿留下。
然后,她打开自己的终端。她要抹掉自己在这方面的所有工作记录,连同父母的记录——正是他们的工作导致了她现在的发现。全部抹掉,即使它们曾经是她生活的核心,多年来,这些工作早已同她的生命连成一体。她将毁掉它们,仿佛要借此来惩罚自己、毁灭自己。
电脑阻止了她。“外星生物研究笔记不得删除。”也许即使没有这个防护措施她也下不了手。父母不止一次告诫她:不应该删除任何东西,不应该遗忘任何东西,知识是神圣的。这种观念深深植根于她的灵魂,比任何教条更加根深蒂固。她进退两难:知识杀害了皮波;可要毁掉知识,等于让父母再死一次,等于毁灭他们遗留给她的一切。她不能保存这些知识,又不能毁掉它们。两边都是无法逾越的高墙,缓慢地挤过来,压紧了她。
娜温妮阿做了唯一一件能做的事:用一层层加密手段深深埋葬她的发现。只要她活着,除她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这个发现。只有当她死后,接替她工作的外星生物学家才能见到她埋藏在电脑里的秘密。
还有一种情况例外。如果她结婚,她的丈夫可以接触她加密的任何文件,只要他有这个愿望。这好办,不结婚就是。这个容易。
她看到了自己的未来,黯淡、无望、难以忍受又无可避免。她不敢寻死,但也很难算活着。她不能结婚,那个秘密她连想都不敢想,唯恐那个致命的真相,又在不经意间透露给别人。永远孤独,肩头上是永远无法卸下的重负,永远怀着负罪感,渴望死去却又被宗教观念束缚,不敢主动寻死。她得到的唯一慰藉是:以后不会再有人因为她的缘故而丧生。她已经罪孽深重,再也担不起更多罪责了。
正是在这种绝望的决心中,她想起了那本《虫族女王和霸主》,想起了死者的代言人。虽然作者——最早的代言人一定在坟墓中长眠了数千年,但其他人类世界上还有别的代言人,像牧师一样,为那些不相信上帝但相信人类生命价值的人服务。代言人将发掘人的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原因,在这人死后将这些事实公之于众。在这块巴西后裔组成的殖民地上,没有代言人,只有牧师,但牧师们无法安慰她。她要请一位死者代言人到这儿来。
这之前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从读了《虫族女王和霸主》,被这本书深深打动之后,她其实一直希望这么做。这里是天主教社会,但根据星际法律,任何公民都有权请求任何宗教的牧师帮助自己,而死者代言人相当于牧师。她可以提出请求,如果哪位代言人愿意来的话,殖民地是无权阻挠他的。
也许不会有代言人愿意来。也许代言人离她太远,等他们到这里时她早已死去。但总存在一线希望,附近星球上有一位代言人,一段时间之后——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他会步出太空港,开始发掘皮波的生活和死亡的真相。也许他会找出真相,用《虫族女王和霸主》里那种她最喜爱不过的明晰的语言向大众宣示,也许这样一来,烧灼她心灵的负罪感便会离她而去。
她的请求输入了电脑,它会通过安赛波通知邻近世界的代言人。来吧,她对那个不知其名的接听者发出静静的呼唤。哪怕你不得不在众人面前揭露我的罪孽,哪怕这样。来吧。
她醒了。后背隐隐作痛,面部发麻。她的脸靠在终端上,电脑已经自动关机,以避免辐射。唤醒她的不是疼痛,而是肩头的轻触。一时间,她还以为碰自己的是一个响应她的呼唤来到她身旁的死者代言人。
“娜温妮阿。”话音轻柔,不是代言人,是另一个人,一个她以为消失在昨夜风雨中的故人。
“利波。”她心中一激灵,猛地站起来,动作太突兀,后背一阵剧痛,眼前顿时天旋地转。她不由得叫出声来。利波的手马上扶住了她的双肩。
“你还好吗?”
他的呼吸闻上去像拂过芬芳花园的微风。她觉得自己安全了、回到家了。“你专门来找我?”
“娜温妮阿,刚能抽出身我就来了。妈妈总算睡着了,我哥哥皮宁欧陪着她。其他事司仪料理得挺好,我就——”
“你知道我能照顾好自己。”她说。
片刻沉静,他又开口了,语气激愤。激愤、绝望,还有疲惫。像迟暮的老人,像耗尽能量的将死的星辰。“老天在上,娜温妮阿,我来不是为了照看你。”
她心里有什么东西封闭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才一直在期待着,直到期待落空才发现。
“你告诉过我,父亲在你的一个电脑模型中发现了什么,说他希望我能自己琢磨出来。我还以为你把模型留在工作站你的终端里,可我回去时模型已经取消了。”
“真的?”
“你心里最清楚,娜温妮阿。除了你之外,没人有权中止你机器里的程序运行。我一定得看看那个模型。”
“为什么?”
他难以置信地瞪着她:“我知道你刚醒来,脑子还不清醒,娜温妮阿。但你肯定知道,父亲在你那个模型里发现了什么。正是因为他的发现,猪仔们才会杀害他。”
她镇定地望着他,一言不发。她打定主意的样子,利波从前见过。
“为什么不给我看?现在我是外星人类学家了,我有权知道。”
“你有权知道所有你父亲的资料和记录,有权知道我公开发表的所有资料。”
“那就发表啊。”
她再次不发一言。
“如果不知道父亲发现的秘密,我们怎么了解猪仔?”她不回答。“你要对上百个人类世界负责,要为了解我们知道的唯一一种现存外星人负责。你怎么能坐在一旁无动于衷?哦,你想自己研究出来,想当第一是吗?行,你就当第一吧,发表的时候署你的名字好了,把娜温妮阿的大名——”
“我不在乎名气。”
“你跟我来这一手,行啊。我奉陪。没有我的资料,你也别想搞出什么名堂——不让我看,我也不让你看我的资料!”
“我不想看你的资料。”
利波再也按捺不住。“那你到底想干什么?想对我怎么样?”他一把抓住她的双肩,将她从椅子里拽了起来,摇晃着她,冲着她大吼大叫。“死在外头的是我父亲,他们为什么杀他,这个答案在你手里,只有你知道那个模型是怎么回事!告诉我!让我看看!”
“决不!”她轻声道。
痛苦、愤怒扭曲了利波的脸。“为什么?”他大喊起来。
“因为我不想让你送命。”
她看得出,他的眼神变了,他懂了。是的,就是这样,利波,因为我爱你。因为假如你知道了那个秘密,猪仔们也会杀死你。我不在乎什么科学,不在乎那些人类世界,不在乎人和外星人的关系。只要你活着,我什么都不在乎。
泪水从他的眼中滚滚而下,淌过他的面颊。“我宁愿死。”他说。
“你安慰别人,”她悄声道,“可谁来安慰你啊。”
“告诉我,让我去死。”
突然间,他的双手不再拎着她,而是抓住她,靠她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你太累了。”她轻声说,“快歇歇吧。”
“我不想歇着。”他含混不清地嘟囔道,但她扶着他,半拖半抱拉着他离开终端。
她扶他走进自己的卧室,不理会床上的积尘,掀开被单。“来,你累了,来,躺下休息。你就是为这个来的,利波,在这儿你可以休息,有人安慰你。”他双手捂着脸,头前后摇晃着。这是一个为自己父亲痛哭的小男孩,一个丧失了一切的小男孩在失声痛哭,就像她从前那样。她拉下他的靴子,替他脱下裤子,双手伸到他腋下,卷起衬衣,将它从他头上拉下来。利波一口口深深吸气,尽量止住抽泣,抬起双手,让她替自己脱下衬衣。
她把他的衣服放在一把椅子上,弯下腰来,将被单在他身上盖好。利波突然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含着眼泪,恳求地望着她。“别走,别扔下我一个人在这儿。”他轻声说,语气中充满绝望,“陪着我。”
她由着他把自己拉到床上。利波紧紧搂着娜温妮阿,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松开了双臂。她却睡不着,她的手轻轻地、温柔地抚过他的肩头、他的胸膛。“利波呀利波,他们把你带走时我还以为从此失去你了,你也像皮波一样永远离开了我。”他听不见她的低语,“可你总会回到我身边的,就像现在一样。”因为她的无心之失,她也许会像夏娃一样被赶出伊甸园,但和夏娃一样,她可以忍受这种痛苦,因为她身旁还有利波,她的亚当。
她有吗?她有吗?她放在利波赤裸肌肤上的手忽然哆嗦起来。她永远不能拥有他。要长相厮守,唯一的途径就是婚姻。卢西塔尼亚是个天主教社会,这方面的规定十分严格。他愿意娶她,现在她相信了。可恰恰是利波,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嫁。
如果嫁给利波,他便会自动获得接触她的资料的密码,无论资料的密级如何。这是星际议会制定的法律。在法律看来,结为夫妻的两个人完全是同一个人。只要电脑相信他有这个需要,就会自动授予他这个权利。电脑当然会认为他需要接触她的工作记录。
而她永远不能让他研究那些资料,否则他便会发现他父亲所发现的秘密,那么,今后在小山上发现的就会是他的尸体。只要她活着,每一个夜晚她都会想象猪仔们是如何折磨他的。难道皮波的死给她带来的罪孽还不够吗?嫁给他等于杀害他,可不嫁给他等于杀害自己。如果不是利波,她还能嫁给谁?
瞧我多聪明啊,居然能找出这样一条通向万劫不复的地狱的道路。
她把自己的脸庞紧紧贴在利波的胸前,泪水洒在他的胸口。
第四章 安 德
想到不得不离开华伦蒂,安德前往卢西塔尼亚的决心不禁有些动摇。孩提时他与姐姐分开过,到现在还对那几年的损失抱恨不已。
我们已知的猪仔语言有四种。我们最常听到的是“男性语言”,有时还可以听到一点“女性语言”的片断。后者显然是在与雌性坡奇尼奥交流时使用的。(好一个性别区分!)还有一种“树语”,这种语言是他们专门用来和祖宗的图腾树说话的。猪仔们还提到了第四种语言,名为“父语”,其中包括用许多大小不同的棍子敲击发声。他们坚持说这是一种真正的语言,和其他语言有所不同,类似葡萄牙语与英语的区别。之所以称为父语,可能是因为敲击用的木棍取自树木,坡奇尼奥们相信他们祖先的灵魂就依附在树上。
坡奇尼奥们学习人类语言的本领极其出色,比我们学习他们的语言高明得多。最近一两年来,只要我们在场,他们彼此交谈也用斯塔克语或葡萄牙语。也许他们已经将人类语言融入了自己的语言,不过也可能是觉得新语言好玩。坡奇尼奥的语言在与我们的接触过程中遭到异化,是非常遗憾的,但只要我们有意与他们保持交流,这种后果就无法避免。
斯温格勒博士问我,坡奇尼奥的名字和对于事物的称谓是否显露了他们文化习俗的某个侧面。答案绝对是肯定的,问题是我不能肯定显露的究竟是哪个侧面。他们在学习斯塔克语和葡萄牙语时经常问我们单词的意思,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词称呼自己。有些名字,比如“鲁特”,可能是从雄性语言翻译过来的,还有些名字在他们的语言中完全没有意思,纯粹是他们凭个人喜好选择人类词汇为自己起的古怪绰号,方便我们称呼他们。
他们称呼彼此为“兄弟”,女性则通称为“妻子”,从来不称她们“姐妹”或“母亲”。他们有时也提到“父亲”,但指的总是代表祖宗灵魂的图腾树。至于他们对我们的称呼,当然,称我们为“人”,但他们也采用德摩斯梯尼的人群分类方法,称人类为“异乡人”,把其他部落的坡奇尼奥称为“生人”。不好理解的是,他们将自己称为“异族”。这说明他们或者会错了意,或者是站在人类立场上来称呼自己!还有,他们有几次居然将女性称为“异种”!这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