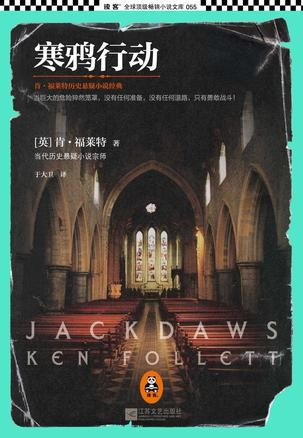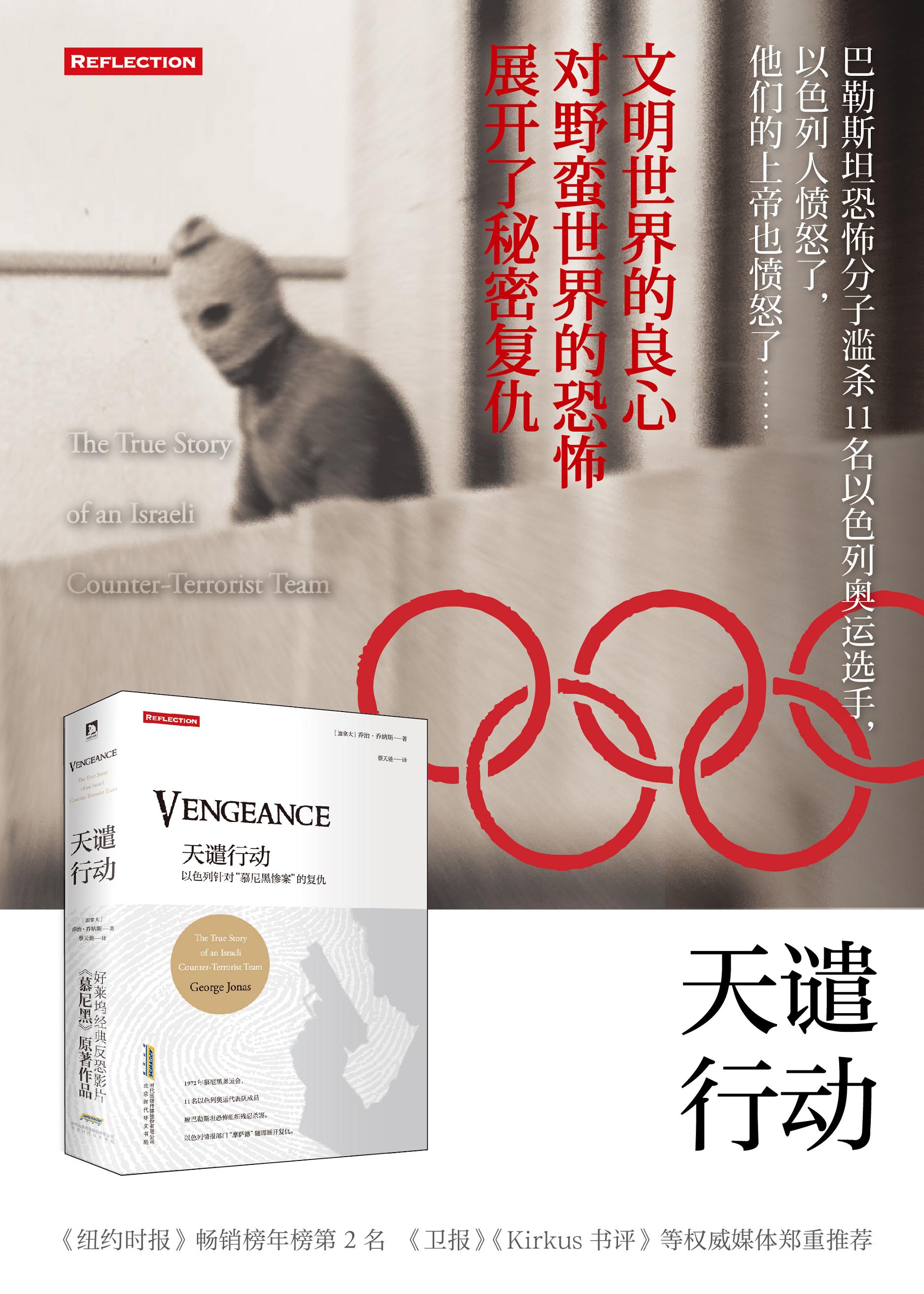寒鸦行动-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迪特尔估计得不错,韦伯果真反着来了。“我可不这么认为,”他说,“贝克尔可以随时通知我。”迪特尔假作气愤,韦伯走了出去。
迪特尔跟静静坐在角落里的黑塞对视了一下。黑塞明白迪特尔用计支走了韦伯,钦佩地看着迪特尔。迪特尔耸耸肩。“有时候倒是全不费力。”他说。
贝克尔带着加斯东进来。老头脸色惨白,看到吉娜维芙的样子,无疑让他吓坏了。迪特尔用德语说:“请坐。你想抽支烟吗?”
加斯东面无表情。
这说明他听不懂德语,这个情况要先掌握。
迪特尔示意他坐下,然后递给他香烟和火柴。加斯东拿了一支香烟,双手颤抖着点燃它。
有的囚犯在这个阶段就垮了,一想到即将发生什么就撑不住了,用不着上刑,迪特尔希望今天就是这种情况。他已经给加斯东展示了两种选择:一种是吉娜维芙的惨相,另一种是香烟和好意善待。
现在,他用法语说话,语调十分友善:“我要问你一些问题。”
“我什么都不知道。”加斯东说。
“不,我觉得你知道,”迪特尔说,“你已经六十岁,大概一辈子都是在兰斯周围度过的。”加斯东并不否认。迪特尔接着说:“我知道,抵抗组织成员都用代码,互相透露的个人信息十分有限,那是为了安全起见。”加斯东本能地略微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大部分人你认识了几十年。抵抗组织成员见面时,一个人可能自称大象、牧师或者茄子,但你知道他长什么样,你知道他叫让…皮埃尔,是个邮递员,家住在公园街,每星期二偷偷跟寡妇马蒂诺幽会,让他妻子以为他是去打保龄球了。”
加斯东把头扭向一边,不愿意看迪特尔的眼睛,这就证实了迪特尔说得对。
迪特尔继续说:“我希望你明白,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痛苦,还是免于受苦,死刑还是缓刑。一切都看你怎么选择。”看到加斯东显得更加惊恐,他很是满意。“你会回答我的问题,”他接着说,“每个人最后都会回答。唯一不确定的是到底拖多长时间。”
这一刻有些人会撑不住,但加斯东没有。“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他说,声音近乎耳语。他很害怕,但仍留有一些勇气,他不会不战而降。
迪特尔一耸肩膀。看来还不太容易。他跟贝克尔用德语说:“回牢房去,把那男孩的衣服脱光,带回来绑到隔壁屋里的柱子上。”
“好的,少校。”贝克尔讨好地说。
迪特尔又转向加斯东,说:“你要告诉我昨天跟你在一起的所有男人和女人的名字和代码,还有抵抗组织任何其他人的。”加斯东摇了摇头,但迪特尔不予理会。“我想知道的每个成员的地址,抵抗成员使用的每一间房子的地址。”
加斯东猛吸着香烟,盯着燃烧着的烟头。
其实,这些并不是什么重要问题。迪特尔的主要目的,是要得到能让他找到其他抵抗组织的信息,但他不能让加斯东知道他的目的。
片刻之后,贝克尔带着贝特朗回来。加斯东吃惊地盯着浑身赤裸的男孩通过审讯室,被带进里面的房间。
迪特尔站起来,他对黑塞说:“看住这个老头。”然后跟随贝克尔进了行刑室。
他小心地让门半掩着,保证加斯东能听到里面的一切。
贝克尔把贝特朗绑在柱子上。不等迪特尔说话,贝克尔就一拳打在贝特朗的肚子上。这家伙力气大,一般人都受不了,那拳头发出的声音令人恐惧。年轻人惨叫一声,在柱子上扭动不已。
“不,不,不。”迪特尔说。如他所料,贝克尔的做法完全不讲科学,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承受这样长时间的殴打是非常容易的。“首先,你要把他的眼睛蒙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块棉布手帕,绑住贝特朗的眼睛,“这样,每一次打击都是最强烈的震撼,打击之间的每分每秒都是痛苦的期待。”
贝克尔拿起他的木棍。迪特尔点点头,贝克尔挥起棍子,一下打在受刑者的头部一侧,硬邦邦的木头与皮肉和骨骼碰撞发出清脆的巨响。贝特朗又惊又痛,哭了出来。
“不,不,”迪特尔又指示道,“不要打脑袋。那会让下巴脱臼,让犯人无法说话。更糟糕的是,你可能会把大脑打坏,那样一来他的任何招供都没有价值。”他把木棍从贝克尔手里拿过来,放回伞架,从武器里选了一根钢撬棍,递给贝克尔。
“从现在起要记住,要给对象造成无法忍受的痛苦,但不要危及他的生命或他对我们招供的能力,避开重要器官,集中在骨头部分,脚腕、小腿、膝盖、手指、肘、肩、肋骨。”
贝克尔脸上露出狡猾的样子。他绕着柱子转着圈,仔细选了选位置,然后用撬棍朝贝特朗的胳膊肘狠狠地抡下去。男孩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这声音正是迪特尔需要的。
贝克尔很高兴。上帝啊,迪特尔暗想,原谅我这场为有效造成痛苦的野蛮教学吧。
按照迪特尔的命令,贝克尔打了贝特朗瘦骨嶙峋的肩膀,然后是他的手、他的脚踝。迪特尔让贝克尔停一下再打,让疼痛有足够的时间稍稍缓解,以忍受下一次打击的痛苦。
贝特朗开始求饶:“别再打了,求求你们。”他恳求着,痛苦和恐惧让他近乎歇斯底里。贝克尔又扬起撬棍,但迪特尔拦住他。他想让这种乞求继续下去。“请别打我了,”贝特朗哭喊着,“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
迪特尔对贝克尔说:“在提审前期就打断一条腿,这办法通常很管用。断腿的疼痛很难忍受,要是破碎的骨头再挨打,疼得就更厉害。”他从伞架上挑出一把大锤。“往膝盖下面打,”他说,把锤子递给贝克尔,“能使多大劲就使多大劲。”
贝克尔瞧准位置,抡起了大锤,胫骨喀嚓一下断裂,那声音清晰可闻。贝特朗尖叫一声晕了过去。贝克尔把角落里放着的一桶水提过来,往贝特朗的脸上泼。年轻人恢复了知觉,又尖叫起来。
最终,尖叫声变成令人心碎的呻吟。“你们想要什么?”贝特朗恳求着,“求求你们,告诉我你们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迪特尔没有问他任何问题。相反,他把钢撬棍递给贝克尔,指着从小腿肌肉刺出的锯齿状断骨,贝克尔朝那里狠狠打去。贝特朗尖叫着,再次晕了过去。
迪特尔觉得或许已经够了。
他进了隔壁。加斯东还坐在原来的地方,但他好像已经变了一个人,他身子向下弯着,用手捂着自己的脸,号啕大哭,连连祈祷着上帝。迪特尔蹲下身子,从湿漉漉的脸上扳开他的手。加斯东用一双泪眼看着他。迪特尔轻声说:“只有你能让它停下来。”
“请停了吧,求你了。”加斯东呻吟着。
“你回答我的问题吗?”
停顿了一下,贝特朗又尖叫了一声。
“可以!”加斯东大喊着,“可以,可以,我什么都告诉你,只要停下来就行!”
迪特尔提高了嗓门喊道:“贝克尔中士!”
“是,少校?”
“现在不要打了。”
“是,少校。”贝克尔听上去有些失望。
迪特尔又换成法语说:“现在,加斯东,让我们从抵抗组织领导人开始。告诉我名称和代码。他是谁?”
加斯东犹豫了一下,迪特尔朝行刑室开着的门望去,加斯东连忙说:“米歇尔?克拉莱特。代号叫‘莫奈’。”
这是个突破,第一个名字是最难到手的,后面的就会自然跟着来了,不用费什么力气。迪特尔把得意隐藏起来,又把香烟和火柴递给加斯东说:“他住在什么地方?”
“在兰斯。”加斯东吐出一口烟,浑身不再打哆嗦了,他说出大教堂附近的一个地址。迪特尔朝黑塞中尉点点头,后者拿出一个笔记本开始记录加斯东的话。迪特尔耐心地从加斯东口中弄到了所有突击队员的名字,有几个人加斯东只知道代码,还说其中两个人他在星期日以前从未见过。迪特尔相信了他的话。离教堂不远还有两个负责接应的司机,加斯东说一个是叫吉尔贝塔的年轻女人,另一个是代号为“元帅”的男人。小组里还有其他人,整个称作波林格尔抵抗组织。
迪特尔问了问抵抗队员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恋爱事件,是不是有人搞同性恋,有没有谁跟别人的老婆睡觉。
虽然拷打已经停了,贝特朗仍在呻吟,时而因伤痛大叫几声。加斯东这时问:“有人会照料他吗?”
迪特尔一耸肩膀。
“求你了,给他找个大夫。”
“好吧……等我们谈完再说。”
加斯东告诉迪特尔,米歇尔和吉尔贝塔是一对情人,但米歇尔已经跟弗立克结婚,就是广场上那个金发姑娘。
到现在为止,加斯东谈的都是一个绝大部分成员已经被消灭的组织,因此他的信息只能用作参考。现在迪特尔转移到更重要的问题上:“当盟军特工来到这里时,他们是如何进行联系的?”
“没人知道这事儿是怎么做的。”加斯东说。他们有“切断防护”。不过,他知道一部分情况。特工跟一个代号叫“中产者”的女人接头。加斯东不知道她在哪儿跟他们会面,但她会先把他们带到自己家里,然后送到米歇尔那儿。
从来没有人见过“中产者”,甚至米歇尔也没见过。加斯东不了解多少这女人的情况,这让迪特尔有点儿失望,不过这就是切断防护的意义所在。
“你知道她住在哪儿吗?”
加斯东点点头说:“有个特工走漏出去的。她在杜波依斯大街11号有幢房子。”
迪特尔尽量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这个情况太关键了。敌人估计会派出更多特工重建波林格尔组织。迪特尔有可能在他们的藏身之处抓个正着。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
加斯东透露说,他们被一架飞机接走,地点是代号为“石头场”的飞机场,实际是查特勒村附近的一块牧草场。此外还有另外一个降落地点,代号叫“金色田野”,但他不知道它在哪儿。
迪特尔向加斯东询问同伦敦联络的情况。是谁下命令袭击电话交换站的?加斯东说弗立克?克拉莱特少校是组织的指挥官,是她从伦敦那里接到的命令。听到这儿,迪特尔来了兴致。一个女人当指挥。不过他亲眼见到她身处战火的勇敢表现,知道她应该是一个出色的领导人。
隔壁,贝特朗在大声求告快点儿死。“求你了,”加斯东说,“找大夫来。”
“说说克拉莱特少校的事,”迪特尔说,“然后我找个人给贝特朗打一针。”
“她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加斯东说道,急于把能让他满意的信息都给他,“大家都说她比任何人潜伏得更久,法国北部她都走遍了。”
迪特尔像着了魔一样问:“她跟不同的抵抗组织接触?”
“我想是的。”
这可真难得——这意味着她可能掌握大量有关法国抵抗组织的信息。迪特尔说:“她在昨天交火后逃走了。你认为她会去哪儿?”
“回伦敦,我敢肯定,”加斯东说,“回去汇报这次奇袭。”
迪特尔暗暗咒骂了一句。他真希望她是在法国,那样他就能抓住她,审问她了。如果他能逮住她,他就能摧毁大半法国抵抗组织——这是他跟隆美尔许诺过的。可现在她已遥不可及。
他站起身。“现在就到这儿吧,”他说,“汉斯,给囚犯找个大夫来。今天我不想让他们任何人死掉——他们还有不少东西要告诉我们。回去把你的记录打出来,一早交给我。”
“好的,少校。”
“给韦伯少校抄一份,但我说给的时候再给。”
“明白。”
“我自己开车回酒店。”迪特尔走了出去。
一走到外面,他的头就开始疼。他用手揉着前额,好不容易才走到车边。他发动汽车离开村子,直奔兰斯。午后的阳光在道路表面反射的光线直刺他的眼睛。这种偏头疼总是在审讯之后来找他的麻烦。一小时后他就会变成瞎子,什么也做不了。他必须赶在发作最厉害之前回到酒店。他不喜欢踩刹车,只是一直在按喇叭。慢慢往家里溜达的葡萄园工人给他闪出一条通道。受惊的马立起后腿,马车翻进了阴沟。他的两眼疼得直流泪,头痛让他感到阵阵恶心。
他开进城里,并没有撞坏汽车。他努力把车开到市中心,到了法兰克福酒店外边,来不及停好车,就把它丢在那儿。他踉跄进到里面,跌跌撞撞朝套房走去。
斯蒂芬妮一看到他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他剥掉制服和衬衣的当儿,她就已经把野外急救箱从他的提箱里拿了出来,在注射器里注入了吗啡混合剂。迪特尔倒在床上,她把针头扎进他的手臂。疼痛一下子就消失了。斯蒂芬妮在他身边躺下,用指尖轻轻抚摸他的脸。
几分钟后,迪特尔就失去了意识。
10
弗立克的家是贝斯沃特街一幢巨大的老房子里的一个单人间,她的房间在阁楼上,如果炸弹穿过屋顶,就会直接落在她的床上。她很少待在这里,不是因为害怕炸弹,而是因为她实际的生活都在别处——在法国,在特别行动处总部,或者在行动处遍及全国的某个培训中心。屋子里属于她的东西不多,一张米歇尔弹吉他的照片,摆着福楼拜和莫里哀法语原文作品的书架,还有一张她在十五岁时在尼斯画的水彩画。矮柜的三个抽屉里是衣服,一个抽屉里是枪支弹药。
她浑身疲惫,情绪低落,脱了衣服后躺在床上,翻弄着一份《检阅》杂志。她在杂志上读到,上周三柏林刚被一千五百架飞机轰炸过,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她想象着那种场面对生活在那里的普通德国人意味着什么,满脑子里都是中世纪绘画中的地狱场景,赤裸的人们被天降的大火活活烧死。她翻了一页,上面是一则二流V牌烟草冒充忍冬牌香烟的无聊报道。
思绪又将她带回昨天的失败,她在脑子里把整个战斗又重演了一遍,想象着假如她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策,是否最后能够取胜,免遭失败。她输掉了这场战斗,也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丈夫,不知道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她不合适做一个领导者,也不合适做一个妻子,也许在她的性格深处有某种缺陷。
现在,她的替代方案也被拒绝了,再做补救的希望渺茫。那些勇敢的人全都白死了。


![(综系统同人)[综系统]筛子补完行动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3/2322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