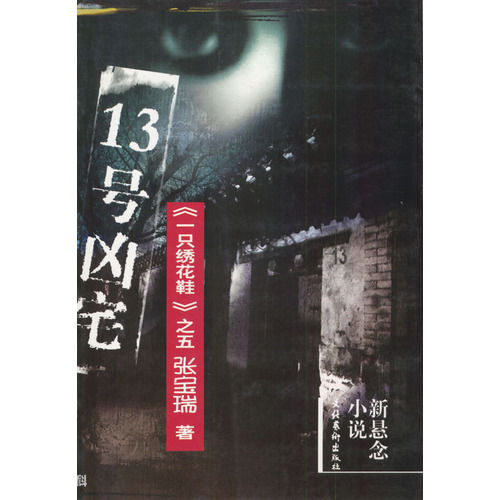凶宅诡事:守宅人-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请问,去南兵马司怎么走?”说着,吴炳湘已挑开门帘,走进了屋。一进屋,吴炳湘顿时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他的手僵在半空中,还没有松开门帘,外面微弱的光线刚好照进来,照在那张吴炳湘熟悉的黑白照片上,照片上的人不正是棺材铺的老板吗?
第六章 日记
赵德山吓得魂飞魄散,再醒来时已经是太阳当空,暖暖的光使他感到好受了不少。他发现自己躺在院子里,还有几只蚂蚁从容地从他的手上爬过,看着痒痒的,实际上并没什么感觉。
赵德山站起身来,轻轻掸下那些蚂蚁,又来到昨晚的那间恐怖的房间前。饭盒还在里面,那块红丝绸在白天的光亮下,颜色鲜艳得很,却没有了晚上看时的恐怖味道。怎么会感到恐怖呢?赵德山又看了看,想不起昨天晚上为什么会那么害怕了,干脆也就不想了。
他推开实际上并没关好的门,走了进去。屋子里还算是亮堂,两张普通的床占了半间房,还有一张圆木的缺了一条腿的凳子。赵德山感到奇怪,两张床怎么就只有一张凳子呢?再往里走,发现门后还有一张,方才释然。灰尘像别的屋子里的一样多,它谁也没有偏袒,和岁月一样是个公平的家伙。屋子里还有个柜子,柜子也很普通。说到普通,赵德山突然想起什么,把目光移回来,发现屋子当中的那张凳子倒是不错的,比起门后的凳子显然要贵重得多。那么,屋子里原来的主人又是什么人呢?一个高贵,一个平凡?又不太可能,赵德山觉得很有意思,这件事就够他想半天的了。他决定慢慢想,先看看还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四处都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激发他那恐怖的回忆,他只好作罢。赵德山来到桌子边,打开自己的饭盒,里面的菜好好的,没有被动过的迹象。是谁把饭盒拿到了这里?
赵德山挠了挠头,或许是鬼想借饭盒把他引到这个屋子里来的。但他来了鬼又没害他,什么也没发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既然没事做,赵德山就在屋子里翻找起来,终于在柜子里发现了一个本子。本子的封面给人挺厚重的感觉,上面落了层不厚不薄的灰,可能因为一直放在柜子里,灰尘没有那么多。赵德山用袖口在那封面上擦了擦,才看清本子是黑色的,上面还有英文,看来本子的主人是个有学识的人的。赵德山不太懂英文,至少本子上的英文他认不太全。这里面会是什么内容呢?
赵德山信手翻开本子,前面的都是用英文写的,按格式来看,是日记,有日期,有年月,记的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多是一八几几年的事,赵德山看不懂,加上笔者字迹潦草,他就不停地往后翻,这才发现,在本子后面的几页里有中文出现,是一水的楷体,整齐而清秀。不过有不少删改的地方,这倒不妨碍别的内容的阅读。
他翻到的这一页,时间记录是1900年3月19日。是八国联军进京的那一年。由于笔者的记录不是连贯的,都是有事才记,赵德山感到这天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于是搬来了那张上等的圆木凳子,坐下来认真地看了起来。
今天是我回北京第二个年头了,给这家主子做管家倒是件不错的差事,我原本以为我会这么一直做下去,一直到老,对此我感到很是失望,觉得自己在英国读的这几年书是白读了。学无用武之地,对一个学者来说真是莫大的悲哀。
赵德山看到这里,深有感触,似乎跟这个日记的主人的距离顿时拉近了。文字就是有这种功能,关键的是在阅读的同时如果能达到心领神会的程度就会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可惜这文字在现在的处境读来……赵德山独自哀伤了一会儿,又继续看了下去。
但今天发生的事却让我知道了,我连做一个好的管家都做不到。这让我产生了深深的自责,也对自己很是失望。
前些天,好友约翰来信说他娶了第二个女人,这才发现自己很爱以前的妻子,他问我这算不算顶失败的人生。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们总是面对选择,在选择之前,我们可以左思右想,一旦给出了答案,我们就没有再选择一次的机会了。我们能面对的只有选择后所带来的结果和由此产生的新的选择。时间是无情的,它抛出的选择题附属于它,亦是同样的无情。但我没有把我的想法告诉他,道理永远是道理,只适合辩论与思考,对安慰一个人来说那只是空话而已。而语言所能表达的,永远只是思想的一个片段。
现在我可以告诉他,他的人生算不上是失败的人生。失败?人生?他想哪里去了?我可以告诉他,我才是一个失败者,当我对自己彻底失望的时候,我是失败者。当你对自己的作为后悔的时候,你是有能力去改变、去补救的,你可以再离婚,再去与前妻复合。这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念头了。但不像我,我是对自己彻底失望了。当一个人没有力气再去争取希望的时候,当一个人对自己彻底失望的时候,他才是彻底失败了。
还是说说今天的事吧。
今天老爷去参加宫中的一个活动,好像是光绪皇帝要为老佛爷祝寿的事。我不想知道得太清楚,我觉得这个国家正在迈向一个在全世界看来都是畸形的时代。夫人去隔壁打牌了,今天会馆的人都忙得很。我反而一下闲了下来,有时间看看书了。但改变我这一生的事情,我想就是在这么一个普通的日子里发生了。
上午九点左右,小姐来找我,她想去郊外玩玩。其实小姐已经十八岁了,她可以自己做主,约上她的朋友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我们这里的人都很宠着她的。但她还是来向我请示。是的,我觉得她是对我有意思的。哪个年轻人在这个年龄不敏感呢?何况我也挺喜欢她,就更加注意她了。她喜欢穿白色的衣服,无论春夏秋冬,活脱脱一个白雪公主。夫人总是责怪她,自己不洗衣服还穿这种不耐脏的颜色,当然,这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又不用她来洗。今天小姐穿的是亮丽的红色旗袍。
至于我,是的,我是喜欢这位小姐的。她很内秀,不像我在外国见到的那些女人,她们倒是开放得很,但我不喜欢。中国人总是安静点的好,或许我还是太传统了。在这里我还不敢直呼她的名字,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叫过她的芳名!天啊,谁知今后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们打算去公园玩,她说不想去什刹海,那里的贵人太多了,人人都矫揉造作,别扭地学着洋人的那一套,她不喜欢。现在的女贵人都学洋人,外国的东西刚刚进入我国,她们什么也不避讳,统统学了起来,什么都是外国的好,自己的东西都不要了。如果能把自己的国籍改了,恐怕她们也是愿意的。她们整天把自己弄得不洋不中的,还自以为是。
倒不像我这个从外国回来的,看惯了外国的事物,反而觉得还是自己国家的好。我想,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有阶段的。比如一开始接触外面事物的时候,你不了解全部,觉得新奇,觉得稀罕,于是想把自己也弄成那样。一旦你了解了,看透了,对这不再“新”的事物就会产生一种距离感,这有助于你客观地认识事物,不至于盲目,我们对外国文化就是这样。而这也是相对的,也有一个强势的问题。比如中国古代的时候,很多国家向我们进贡,来过我国的使节都以为我们国家的东西好,带回去后颇为得意。那是因为中国在那时很强大。现在洋鬼子的国家成了强势的国家,一个个凶巴巴地进来了,觉得他们自己了不得了,也不觉得我们好了,什么都要按他们自己的做,西装、汽车、挂表,样样都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好。中国人看了,就觉得是他们的好了。当然,对于因科技进步而出现的汽车和怀表我们还是要学习的。可这学习是要平等地学,而不是卑微地拿别人的成果来用,否则我们永远都在“学习”,永远赶不上人家。话说回来,这西装我们就不必学了吧?但这传统布衣却成了卑贱的代表,即使料子再好也不如人家的高贵。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洋鬼子的东西也不过如此啊,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心态问题了。
小姐没有盲目追求,而是依旧穿着我们的旗袍,我看在眼里,在心里更是喜欢。她穿着旗袍的样子真的很美,是一种典雅的美,相信那些迷失在西洋服装里的人会有一天重新发现旗袍的美的。那一天,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够强大的时候。与国家现在腐败的程度相比,我更恨国民的献媚和盲目的崇洋心理。
我们走上了去公园的路,但没去公园。到底去了哪儿呢?我也不知道,那是一条林荫小路,人很少,幽幽地向前延伸,她喜欢自然。但那条路我以前没有走过,踏上那条路的时候,我是那么欣喜而又感到莫名的害怕,怕这一走就回不去了,这是一种冥冥中的感觉。
她似乎没有觉察到什么,在路上跳啊、笑啊的,完全没有大小姐的样子,像是一个邻村的姑娘。她的单纯和快乐引来那些贫穷人们的注目。我原本以为那种自由是属于这些普通的百姓的。因为他们不用像做官的人一样时时为自己的官位而忧愁、伤脑筋。也不用像商人一样,每天都承受着一定的心理负担。但我错了,我那时才发现,这些穷人更加没有自由。因为他们每天都要为自己的生计而忙碌,下一顿吃什么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他们不是没有忧愁,而是被生活压得没空去想什么是忧愁。
这时我也才明白,自由的人是指那些心灵自由的人。心灵自由的人不会是穷人,也不会是被金钱与权力困住的人。其实,自由要受到财产的限制,同时也要受到客观环境的约束。
我就这么看着小姐,想着哪天要娶她回家,但是哪天呢?一个小姐嫁给一个管家?我不敢想象,不是没有勇气娶她,而是不确定,她嫁给我之后是否会幸福。我不怕世人议论说我其实是想霸占主人家的财产——老爷家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而是怕在这种议论下,她的家人,也就是老爷、夫人,甚至是她自己也不由得会这么想,即使他们开始的时候不是这么认为的,恐怕到时候我都要怀疑自己的动机了。感情是经不起猜忌的。幸好我看到了这一点,那么我该怎么办?我真的爱她呀。
这么想着,我的思绪在她的欢乐中痛苦着。突然,从树后冒出几个人来,他们蒙着面,一个人手里拿着刀,我们这是到了哪里?我想叫人,却发现周围没有一个人。我们走到了没有人烟的地方?
我举起拳头跑了上去,原本想着他们会用刀来绑架小姐而威胁我。没想到,他们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呼呼地冲上一个人来,躲过我的拳,一脚把我踢翻在地。只此一摔,我就再也起不来了。那时我真后悔没有跟约翰学两招,只顾读书了。小姐哭喊着向我跑来,被一个匪徒一把抱住,他好像是要非礼她!我刚才就感觉到他们是一群野蛮的畜生!其中有一个人竟然还戴着金丝眼镜!我挣扎着要起来,却被另一个人一脚踩在了地上。小姐比我勇敢得多,她奋力地挣扎着。突然,我听到噗的一声响,随后就是小姐简短而痛苦的“啊”的一声。我背上的脚移开了,他们慌张地跑开。我看到一个满身是血的女人,她在向我伸手,嘴里却发不出声音来。小姐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我迷茫地看着她,她痛苦地看着我。
直到有人来了,我才想起去扶她。我一定是吓呆了,我给自己解释道。但对一个死人,我的解释没有任何用处……
我不知道该怎么救她,我之前学的东西在这种场景下一点用都没有,在这种关乎生命的情况下,我只能直愣愣地看着发生的一切,却束手无策。我感到自己的懦弱。
那些英雄体诗歌,那些古希腊神话,那些中国古代的武侠小说,它们都帮不上我,反而在我的脑海里转了一圈后嘲笑我的迂腐。那些可怜的文人呵,你们只能躲在自己的幻想里、文化里,用一支笔塑造一个又一个英雄,但你们却不是英雄!你们永远不能站在现实的最前方抵挡生活中真正的麻烦。
我刚才就被一个莽夫踩在脚下,他很可能与刚才那群穷人无异,不过是学了两招,或者仅仅是空有一身力气,但他踩在了我的身上。我可是一个出国深造过,见识颇丰的学者!为此,我感到羞耻。
我爱的人儿就这么死了,她的眼里充满了恐惧与失望。她恐惧什么?我们活着的人无法知道了。恐惧死亡吗?她是对我失望吗?肯定是这样了。
我抱着她走走停停,有人说:“喂,小伙子!医院在那边!”我冲那人善意地笑了一下,却没有转向医院,他们说我一定是吓傻了。不,那时我清醒得很。一袭红色的旗袍,更红的是血。她一定已经死了。但是,她突然伸出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衣领,那手是温的,手上的血蹭到了我的脖子上。她艰难而哽咽地说:“去医院,救救我!”
去医院?那容易。可我怎么跟老爷解释?几个匪徒冲上来,只有小姐在拼命,而我却没事似地躺在地上?不行。我有我的尊严,我要在这个家里立足,我不能出卖自己。对不起。这三个字我是否说过,我已经忘了,但我知道我没去医院。
当一个穷人带着两名官兵找到我时,我已经是孑然一身了。我自己一个人在马路上潇洒地走着。穷人吃惊地看着我。那两个官兵知道我是南兵马司的人后,并没有与我有什么纠缠,很快就离开了。虽然逃过了一劫,可在心里,我极度地厌恶着自己,厌恶那两个当兵的小人,厌恶这个只讲地位和权力的野蛮社会!我原本还想在官兵面前为自己辩解一下的,竟然没有这个机会。
小姐的尸体具体埋在了哪里我也记不得了。回来后,夫人与老爷问我见没见过小姐,我答的是——“没见过。”他们便心急火燎地去找了,我还帮着他们找,一直到深夜,老爷着急而感谢地说:“刘管家,你也别太累了,早早休息吧。”那时我竟然有种做了好人的感觉。一切文明的烙印被我抛弃,我却感到如此邪恶的轻松。
半夜,我回到



![(瓶邪同人)[瓶邪]老宅诡事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
![(凶宅笔记同人)[凶宅朋我]描骨笔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3/2340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