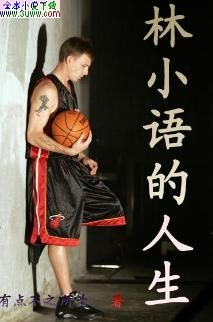温暖的人皮-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妇说:“好心人哪,有谁会在深更半夜陪我这个孤老婆子。”
花荣说:“人死不能复生,老人家不要过于悲伤。”
老妇说:“道理我懂,可是,可是我儿死得冤哪,他还那么年轻,老婆都还没有讨。”
花荣说:“他——”
老妇说:“那年,他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他觉得有愧,对不起来我们老俩口,留下了一封信,就到外面闯荡去了。我们都不晓得他去了哪里,根本就没有他的消息。几个月后,收到了他寄来的两百块钱,还有一封信。信中装了张照片,就是镜框里的这张。他让我们安心,说找到工作了,以后每个月都会寄钱给我们,让我们不要太担心他。他说的话做到了,从那以后,每个月都寄钱给我们,钱有时多有时少,最少也有两百元。我对老头子说,孩子有出息了,你该放心了。老头子和我想法不一样,他总是忧心忡忡。两年前,老头子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我没有料到会那么严重,儿子竟然死了。你知道吗,我儿是被人打死的。我们去收尸时,才知道可怜的儿子这些年,一直靠摆小摊为生,自己省吃俭用把钱寄回来给我们。打死他的人是城管,我不晓得城管是干什么的,只晓得他们好凶恶,活活的把我儿打死了。人都被他们打死了,赔钱有什么用。我们回来后,就在安葬他骨灰的那天晚上,老头子吐血死了,他们都走了,留下了我这个孤老婆子。你说,我能不伤心吗。我也想死,可是,我死了,谁在清明时给他们扫墓呀。”
花荣的眼睛湿了。
他不知道怎么安慰老妇。
他伸出手,握住老妇粗糙的手,老妇的手十分温暖,像母亲的手。
他一直记得母亲温暖的手。
天蒙蒙亮时,风子他们走出了房门,叫唤花荣,说该出发了。
花荣从老妇的房间里走出来,他们十分诧异。
花荣没有理会他们,只是对老妇说:“老人家保重。”
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千块钱,放在了她手上。她连忙说:“不要,不要,我用不着钱的,真用不着的。”
她把钱塞回花荣的口袋,说:“你不要再给我钱了,我会生气的,我生气了就不给你们开门了。”
花荣见她十分决绝,就没有再把钱掏出来。
风子和江菲冷漠地看着他们,也没有拿点钱给老妇的意思,而且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只是想马上逃离老妇的家。
花荣突然特别鄙视这对男女。
老妇开了门,他们出了门。
江菲要抱着皮箱上车。
花荣冷冷地说:“放早后备箱里去吧,那里更安全,你这样抱着,不是故意引起别人的注意吗,我可不想看到我的客人被抢。”
风子说:“花兄弟说得有道理,还是放后面吧。”
花荣说:“我不是你兄弟,以后不要这样叫我,腻歪。我只不过是个开黑车的。”
风子尴尬地笑笑。
风子帮江菲把皮箱放进了后备箱,他看到后备箱的角落里放着一把剔骨尖刀,心里咯噔了一下,然后重重地合上了后备箱的盖子。
风子没有坐在副驾驶位置,而是和江菲坐在了后面。
花荣和老妇告别后,才上车。
风子把嘴巴凑在江菲耳朵上低声说着什么,他们的脸色十分难看。花荣上车后,他们赶紧分开。
离开老妇家,开了十几分钟,来到了一个乡镇。
这是个山区乡镇,冷冷清清。
花荣肚子饿了,找了个路边的包子铺,停下了车。
风子说:“你要干什么?”
花荣说:“难道你们不吃早饭?”
戴着口罩的江菲说:“不吃,走吧。”
花荣心里不快,说:“不吃不行,没有力气开车。你们不吃,就在车里等我吧,我吃完了再走。”
风子瞪着他,什么也没说。
花荣下车,走进了包子铺,坐下来,说:“给我来十个包子,一碗豆浆。”
包子铺的老板娘是个中年妇女,脸很黑,却满面笑容。
她把包子放在一个大盘子里,放在了花荣面前,说:“吃吧,豆浆马上给你端过来。”
花荣拿起一个包子,咬了一口,慢慢地嚼起来。
他故意慢吞吞地吃。
他无所谓,反正不赶时间,开到哪里算哪里,其实,他是想气气那两个莫名其妙的人。
车里,江菲生气地说:“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司机。”
风子说:“这个人平常很好的呀。”
江菲说:“我看不是个好东西。”
风子说:“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江菲说:“我担心他会坏了我们的事情。”
风子说:“没有那么严重,他什么也不知道,你不要多想了,忍耐忍耐,到了我老家就好了。”
江菲说:“你和他说,让他吃快点,赶紧走。”
风子降下车窗玻璃,对包子铺里慢条斯理地吃着包子的花荣说:“花师傅,你能不能快点。”
花荣没有搭理他。
江菲生气地说:“早知道这样,就不和你走了,这样提心吊胆的,不是人过的日子。”
风子说:“好了,别抱怨了,又不是我让你干那些事情的。”
江菲说:“不是为了你,我会这样,你这个混蛋。”
风子咬了咬牙,沉默。
花荣把最后一个包子吃完,对老板娘说:“给你钱。”
老板娘收了钱后,微笑着说:“谢谢,一路走好。”
走出包子铺的花荣,突然想到了什么,又折了回去。
老板娘说:“还有什么事情?”
花荣说:“你知道离这里不远处那个儿子在外地被城管打死的人家吗?”
老板娘说:“知道呀,怎么了?”
花荣从口袋里掏出那一千元,说:“昨天晚上,我们在那人家借了宿,老太太人很好,早上走时,不愿意收我的钱。我心里过意不去,想托你把这些钱给她。”
老板娘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你说什么?”
花荣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老板娘惊骇地说:“活见鬼了。”
花荣说:“怎么?”
老板娘说:“你们住的那家人都死光了呀,哪里有什么老太太。老太太在半年前就喝农药自杀了。你说你们住在她家,还要给老太太钱,这不活见鬼了吗。老太太死后,那房子就一直没有人住,你们——”
花荣心地升起了一股寒气,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冒出了鸡皮疙瘩。
可以说,这是一次莫名其妙而又让人心慌的旅程。风子选择的道路难走不说,他和江菲总是因为困难而相互埋怨,有时不顾花荣在场,大吵大闹。花荣渐渐地有了判断,江菲是个有夫之妇,和风子私奔是因为犯了案,而她犯案是因为风子……其实,风子是带着犯案的江菲逃亡,他以为只要逃到地处贵州山区的老家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尽管知道了这些,花荣还是不清楚江菲的身份,以及她犯了什么案,而且对那皮箱里装的什么也一无所知。好几次,花荣想打开皮箱看个究竟,因为江菲看得紧,没有得逞。他们尽管相互埋怨,不停地吵嘴,可对花荣还是身份警惕。他们不敢住旅馆,渐渐地,也不敢到人家里借宿了,怕留下什么蛛丝马迹。风子和花荣商量,以后累了就在车里睡睡好了,或者在野外搭帐篷休息,他带了两顶小帐篷,还有睡袋什么的。花荣才知道他们的旅行包里装了些什么,还有饼干面包之类的干粮。花荣不答应,说自己没有床根本就睡不了觉。风子说:“这样吧,再给你加两万,你看怎么样。”花荣想了想,答应了他。
十多天后,他们来到了湘西和贵州交界的大山里。
那是个下午,天阴沉沉的,冽风呼啸,天寒地冻。
不知不觉,他们从秋天进入了冬天。
银灰色的现代轿车驰进了大山里的一个山谷。
路是泥沙路,坑坑洼洼。路两边是高过人头的草丛,更远一点是茂密的森林。这个地方人迹罕至的样子,开了半天的车,也没有见到别的车辆在这条路上行走。
花荣说:“妈的,走的什么鸟路。”
风子说:“过了这段就好了。”
花荣说:“好个屁,你以为我是傻瓜呀,进入贵州后,山更多,路更不好走了。”
风子说:“走都走到这里了,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只有继续走下去了。”
花荣说:“等把你们送到地方,估计我的车也报废了。”
他们说话的时候,车突然剧烈抖动,要翻掉的样子。花荣赶紧刹住了车。风子说:“怎么了,赶快走呀,天黑时,我们必须走出大山。”
花荣知道发生了什么,恼怒地说:“必须你妈逼!”
风子说:“你怎么骂人呀。”
花荣说:“老子骂的就是你,王八蛋,你不是故意折腾我吧!车胎爆了,你知不知道!”
风子说:“啊——”
江菲说:“还不下去看看,你们吵什么呀。”
花荣和风子下了车。
右边前轮胎已经瘪下去了,花荣一把拉过风子,恼怒地说:“你睁大眼睛看看,车还能开吗,这荒山野岭的,你就等着喂野狼吧!”
风子说:“花师傅息怒,息怒。想想办法吧。”
江菲也下了车,看到干瘪的轮胎,眼神慌乱。
花荣说:“想什么办法?你匆匆忙忙叫我走,连备胎都没带,这个鬼地方,到哪里去找补胎的人?你他妈再多钱有屁用,你能给我弄个轮胎出来,我就真服你了。”
风子四处张望。
这片山野,除了他们三个人,鬼影都没有。
山风呼啸,天上乌云翻滚。
花荣趴下身体,检查着轮胎,发现轮胎是被铁钉刺穿的。那一片有好几颗铁钉,仿佛是有人故意在这里布下的铁钉,这是一个陷阱?如果说真的有人故意这样做,那么,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花荣说:“情况不妙。”
风子脸色煞白,喃喃地说:“这可怎么办?”
江菲扯下口罩,瞪着眼睛说:“怎么办,我们死在这里算了。我真倒霉,怎么就鬼迷心窍,看上了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什么狗屁诗人,你就是一个骗子,一个流氓,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流浪汉。”
风子眼中冒火。
他颤抖着说:“你可以侮辱我,但是不能侮辱诗人。”
江菲说:“狗屁诗人,狗屁诗人!什么狗屁浪漫,没有钱你连狗都不如,要不是我,你这些年能如此潇洒过日子,能花天酒地。你住的房子是我租的,你的手提电脑是我买的,你吃的穿的都是我提供的,你甚至拿着我给你的钱去泡妞,还美其名说体验生活,你说你是不是狗屁诗人,是不是!现在我出事了,你还要带我去什么鬼地方,还骗我说到了那地方,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还说过什么两个人的幸福生活。能幸福吗,能吗?这些天,我除了恐惧,还是恐惧,我还不如回去自首,就是坐牢也比逃奔的生活强。”
风子大声吼:“别说了,你以为我的心好受!你以为你那几个臭钱就可以收买我,要不是爱你,我早就离开了,也不会走到今天。一切都是你自己愿意的,我从来没有逼过你,是你说爱我离不开我的!你明白吗!”
江菲流下了泪水,表情痛苦,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花荣的牙又开始疼痛。
他倒抽着凉气说:“你们慢慢吵,老子不奉陪你们了。”
花荣往前走去。
风子见他离开,急了:“你他妈的真的走了?”
花荣回转身,说:“你刚才说什么?”
风子说:“我说,你他妈的真的走呀。”
花荣朝他扑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恶狠狠地说:“我告诉你,你骂老子可以,你再敢骂我妈,老子就弄死你。”
风子感觉到了他的力量和愤怒。
他胆怯地说:“花师傅,放开手,有话好说。”
花荣说:“我看江菲说对了,你就是个狗屁诗人。”
风子突然怒了:“别侮辱诗人。”
说完,他伸出手,抓住了花荣头上的帽子。
花荣说:“放开我的帽子,否则我真不客气了。”
风子松开了手,没料到,松手时把花荣的帽子带落到地上。花荣哀嚎了一声,松开了抓住风子衣领的手,赶紧捡起帽子,戴回了头上。
花荣说:“狗东西,有你好瞧的。”
他转过身,往前走去。
江菲说:“花师傅,别走。”
花荣没有回头,说:“你以为我真的会走,我的车还在这里,难道不要了,还有,你们的钱还没有付清,我能走?我只是往前走走,看看有什么办法。”
江菲松了口气。
他们又继续斗起嘴来。
花荣心里像吃了死苍蝇一样难受,他头上的秘密,暴露在了他们眼中,又是羞愧又是怨恨。边走,心里边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走着走着,花荣发现前路边草丛中里有间小木屋,小木屋上有两个大字:“火补。”敢情这是个修轮胎的地方?走近前一看,果然是。问题是,小木屋铁将军把门,根本就没有人。他从门逢里望进去,发现屋里有许多修车补胎的工具,边上还有张行军床。在这荒山野岭开店,会有什么生意,此店的主人是不是脑袋坏掉了。他想到了刺穿轮胎的钉子,会不会和此店的主人有关系?此店的主人也许不仅仅是为了补胎那么简单,会不会是埋藏此地的江洋大盗或者杀人犯?花荣不寒而栗,觉得有人躲在不远的隐蔽处,朝他冷笑。
那隐蔽之人是猎手,而他们就是猎物。
花荣身上一阵阵发冷,牙好像也不痛了。
他回到了原地。
风子和江菲已经不吵了,还抱在一起接吻。
花荣感觉到了恶心,他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父亲和那个寡妇偷情的情景,眼里顿时充满了杀气。
风子和江菲在他眼中变成了两只兔子。
他想剥了这两只兔子的皮。
可是,他现在还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担心另外一双眼睛,猎手的眼睛。
花荣站在他们面前,说:“你们还有心情接吻,都死到临头了。”
他们赶紧分开。
江菲说:“花师傅,有什么办法了吗?”
花荣说:“没有,我不是说都死到临头了吗。”
风子说:“你说什么,死到临头?”
花荣点了点头。
风子说:“到底怎么回事?”
花荣说:“是有人故意的在路上布下了铁钉,让过路的汽车中招,然后……”
江菲听了他的话,吓得四下张望,仿佛随时都有一个蒙面强盗出现在面前。天渐渐的暗下来,风子突然举起双拳,吼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