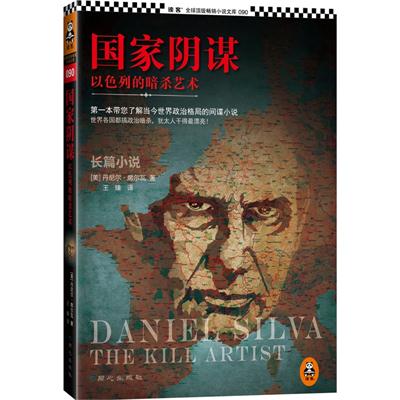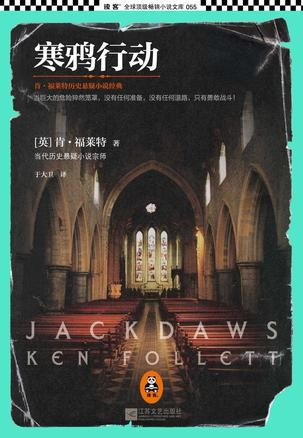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被炸到天花板上去。复仇者们惶恐了,不安了。当搜查毒品的德国警察将他们团团围住时,他们几乎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当一个黑人小孩不慎把球扔进他们的窗户里时,他们“立即趴在地上,双臂抱头,等着那颗手榴弹爆炸”。当邮递员来检查丢失的邮件时,他们赶紧在卧室门后做好埋伏,以防不测。阿弗纳在床上再也睡不着觉,只有搬到壁橱里才能睡着,因为他时刻担心有人在床底下放炸弹。
他跟妻子的团聚也不全是欢乐。考虑到任务结束后,自己再也不可能回以色列生活,他动员妻子到美国生活。妻子从来没有在以色列以外生活过。她孑然一身地住在美国,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不知道阿弗纳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他第一次回美国时,看到妻子孤独脆弱的身影,心里痛苦极了。他不知道这种频频更换姓名与身份、跟哪怕是自己的亲人都无法诉说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而在他妻子的眼里呢,他在过去的七个月中好像老了十岁。虽然实际只有二十六岁,而看起来却像三十四五岁的人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看来你愚弄得了你的脑子。可你愚弄不了你的身体。”
仿佛阴魂一般不散的惶恐与不安让阿弗纳开始对这次任务的正义性感到困惑,对这样的报复行动能否消灭恐怖活动提出了质疑。事实证明,他们的困惑和质疑并不是毫无根据的。阿弗纳在伦敦大街上被恐怖分子跟踪了。紧接着,三个特工一个接一个地被恐怖分子杀害了。第一个特工死在恐怖分子雇来的女人设下的温柔陷阱里。第二个特工在研制新式弹药时被神秘地炸死。第三个特工在冰天雪地的深夜里散步时遭人暗算。阿弗纳虽然感到震惊、愤怒,但在强大的、无形的恐怖势力面前,却又无可奈何。连是谁杀害了自己的同伴都不得而知,更别提报复了。阿弗纳更加困惑了,既对同伴们神秘的死亡感到困惑,也对这种循环往复、无休无止的复仇怪圈感到困惑。正是这种困惑,坚定了他后来离开特工组织和选择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的决心,从而完成了人性的自我救赎。
表面上,三个特工是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但实际上,杀害他们的恰恰是这种困惑。随着暗杀行动的连连得手,特工们变得神情恍惚,举止古怪,神秘莫测。看着一个个生命倒下去,他们变得越来越沉默、惶恐与不安。他们心灰意冷,疑心越来越重。他们随身带着枪,充满了杀气。这种困惑无法与外人言说,不能向家人倾诉,害怕与同伴沟通。孤独像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网把他们紧紧笼罩。他们变得孤僻、厌世、迷惘,甚至绝望,于是企图从女人身上、从工作当中、从全神贯注的思索之中得到一丝慰藉,结果却为恐怖分子所害。小说自始至终都没有交代三个特工到底是谁杀死的,不仅没有交代,还大肆渲染,故布疑阵。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特工们正是死于这种困惑呢?困惑久悬不决必成困境。特工们走不出困境,只有走向毁灭。
拜伦说:复仇是一盘菜,最好等冷却之后再来吃。复仇也许是一盘菜,但得有失去人性和灵魂的冷血杀手才行。否则,即使冷下来的菜也吃不下去。《复仇》中的特工们都是有血有肉的热血男儿,他们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家人。于是,死亡似乎是他们的惟一选择。
没有走向毁灭但已心如死灰的阿弗纳最终离开以色列去了纽约。他不能找工作,因为他不是美国的正式移民。他跟那些从墨西哥来的非法移民一样,成了美国庞大的地下经济中成千上万的从事低级工作的外国人中的一员。但他不认为这是剥削。相反,他心存感激。他不介意开出租车或刷房子得到的钱比正式移民少,也不介意工作时间比他们长。正是在开出租车或刷房子的时候,他慢慢意识到,这些是他可以干一辈子的活。
每次看见父亲坐在折叠躺椅上,半睡半醒地梦想着红宝石,等待电话铃响的时候,阿弗纳就庆幸自己终于走出了复仇的怪圈。这种觉醒来自于他对复仇行动的作用和意义有了比较透彻的了悟,来自于他对人生不可摆脱的荒谬的认识。他认识到,复仇根本不能最终消灭恐怖分子,也无法消灭世界上的恐怖活动。一个恐怖分子倒下去了,另一个恐怖分子又会像指甲那样很快长出来。当笼罩在神圣的国家使命上的面纱被撕下来以后,现实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用暴力来遏止暴力是完全不现实的,它除了能引发新一轮的更加猖狂的恐怖活动之外,还把复仇者摆到了与恐怖分子同样残忍的位置上,跟恐怖分子变成一丘之貉。随着现实本来面目的逐渐显露,复仇者内心的动力渐渐消弭了。
《天谴行动》无疑是一场悲剧。正如其他悲剧一样,它解决不了现实的生存困境,只能暴露残酷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它是悲剧创作者情感的表达,同时也以“同情”的方式引发接受者情感的表达。这种表达是情绪的宣泄与净化,也是对处于悲剧困境中所显示出来的生命力量的哲学思考。在这场“有价值的东西被撕毁”的悲剧中,毁灭的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应唤起我们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和尊严的重新审视,对生命以及生存之本质的理性思考。
序幕
慕尼黑
与大多数以线条流畅、设计巧妙为特点的现代自动步枪比起来,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看起来敦实坚固。这种被正式命名为AK47的攻击步枪,据说是由一位西伯利亚农民发明的。至少围绕着这种世界上最流行的武器的传说是这样。它简单粗糙,长三十四点二英寸,枪托和握把是木制的,深黄色,中部和前部是金属的,暗灰色,中间也是金属的,是后膛和扳机。弹夹向下,呈弧形,可装三十发七点六二毫米的子弹。短导程子弹可穿透钢板。若设置于自动开火状态,卡拉什尼可夫可在一分钟内射出一百发子弹,初始速度为每秒两千三百三十英尺,或者每小时一千六百英里。许多国家都生产过这种枪。近距离使用时,它可以将一个人一分为二。
1972年9月5日,几支卡拉什尼可夫步枪被从油脂纸中拿出来,递给八位代号为“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他们要去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慕尼黑奥运村以色列运动员的住所。
虽然没有人认出他们是敢死队员(恐怖分子经常用这个词来称呼他们自己),但有人看见他们在凌晨四点攀上库索兹因斯基达穆六英尺高的电网。他们就从这个距离以色列运动员住处大约五十码的地方进入奥运村。五十码的距离,一群人再慢再小心也能在一两分钟之内走完。然而,直到四点二十五分,恐怖分子才把密匙插进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第一号公寓前厅门上的锁孔里。在这期间,他们是否得到过奥运村的帮助不得而知。
第一个听到动静的人是个体重二百七十五磅的巨人、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洛德。虽然他不能马上断定这个声音是不是他的室友、摔跤教练莫什·温伯格的,因为后者要很晚才回来,身上也有钥匙——但门后阿拉伯人的声音使他很快断定:情况危险。实际上,正是他用希伯来语喊了一声“危险!”——才把他的室友惊醒。他一边喊一边用巨大的身躯顶住缓缓打开的房门。
在接下来的几秒钟里,八个阿拉伯人企图把古特弗洛德顶住的门推开。双方的力量足以把门框两侧的直木和金属铰链彻底扭曲变形。这为古特弗洛德的队友、举重教练土娃·索科罗夫斯基赢得了足够的时间,让他得以破窗而逃。
一号公寓的其他四个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田径教练阿米卒·沙皮拉,剑术教练安德雷·斯皮泽,步枪教练科哈·朔尔和举重裁判雅科夫·斯普林格已被置于枪口之下。阿拉伯人对他们非常粗暴,恐吓他们,让他们说出其他以色列运动员的住处,还说谁敲开了以色列运动员的门让敢死队进去了,谁就自由了。但他们没有给古特弗洛德这个机会。他们像《圣经》中自己的先人腓力士捆绑被俘的参孙一样把他捆了起来。
恐怖分子没有得到以色列人的任何帮助,于是决定搜查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乌拉圭和中国香港的奥运队员也住在这里。他们没有抓到住在二号、四号和五号公寓的八个以色列队员,但却抓到了住在三号公寓的六个运动员。他们是摔跤运动员埃里泽·哈尔凡、马克·斯拉凡和戛德·佐巴雷,举重运动员大卫·马克·伯格、泽福·福德曼和约瑟夫·罗曼诺。不过,恐怖分子在进入三号公寓之前,必须先对付摔跤教练莫什·温伯格。那天他在外面待得很晚,这时正好从康诺利大街漫步而来。
温伯格的块头大概跟古特弗洛德差不多,对付起来也不容易。他把一个恐怖分子撂倒在地,另一个恐怖分子朝他脸上开了一枪,暂时把他征服了。他虽然受了重伤,但仍然没有放弃。三号公寓的人被俘之后,恐怖分子像赶牲口一样把他们从康诺利大街赶向一号公寓。轻量级摔跤队员戛德·佐巴雷决定向前猛冲。虽然敢死队在他后面开了几枪,但这个小摔跤队员蜿蜒前行,越过围墙内高低不平的地面,及时脱离了险境。温伯格利用这个机会,又抓住一个恐怖分子的下巴并捏碎,又把他打昏了过去。另一个恐怖分子立即朝他的胸部开了几枪,温伯格倒下了。
现在轮到约瑟夫·罗曼诺了。在恐怖分子把他绑起来之前,他试图和他的队友大卫·马克·伯格一起从一号公寓的窗户里逃走,但没成功。罗曼诺从案台上拿起一把刀,刺进了一个恐怖分子的前额。那个阿拉伯人伤得很重,撤了下去。另外一个人从他的后面用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向他近距离射击。这位举重运动员倒下了。第二天救援人员试图搬动他的身体时,据说他从腰部断成了两截。
温伯格仍然没有停止战斗。这位摔跤运动员苏醒后没有爬离一号公寓,而是在公寓里摸索着前行,寻找恐怖分子。敢死队被一个血肉模糊的跌跌撞撞的庞然大物吓了一跳,但他们没有立即开枪。温伯格抓住时机,向一个人撞去,又抓起一把菜刀,砍伤了一个人的手臂。最后他被射中头部身亡。
这时大约是凌晨五点,行动持续了大约二十五分钟。“黑色九月”杀死了两名以色列运动员,绑架九人,两名运动员逃生。恐怖分子没有找到公寓里的另外八个以色列人。
在二十五分钟的激战中,奥运村的安全部门只收到了一些诸如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出了点小麻烦”之类的模糊不清的报告。这也不奇怪,这个时候大多数运动员和官员都在熟睡之中。战斗零零星星的,喊声和枪声之后是一段时间的沉寂。被吵醒的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他们听了一会什么也没听见,就又睡着了。少数几个人从床上爬起来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却什么也没看见。在奥运村,经常有焰火和欢笑声,没有任何庆祝活动的晚上很少。对许多睡在以色列队员附近困倦的人来说,恐怖活动的声音听起来跟庆祝活动差不多。
四点五十五分或者稍晚一点,一位赤手空拳的保安只身来调查了。他用手指拨弄着对讲机,用德语对站在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几个戴着头巾的恐怖分子咕哝道:“这是怎么回事?”被问者没有回答,在门后消失了。
与此同时,两位逃走的以色列人拉响了警报器——一个在南韩队员的公寓里,另一个在意大利人住的地方。半小时以后,当局收到了几份恐怖分子用英语打印的条件。
敢死队还把温伯格的尸体扔到了大街上。
这些条件是:释放“以色列军方”扣押的二百三十四名犯人。他们的名字都打印在纸上,还有几个被西德联邦政府拘捕的人,其中有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的头目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安德雷斯·巴德尔。他们是在同年六月被德国警方逮捕的。敢死队还提出,他们的这些条件满足以后,还要三架飞机把他们送到“安全的目的地”。到那里之后,他们才会释放以色列运动员。公报要求当局上午九点满足这些要求,九点以后他们就会“一次性地或者一个一个地”处决人质。
接下来照例是谈判。西德高层官员提出用他们自己交换人质——作为个人来讲,这是一种勇敢的行为。这些人是: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长和巴伐利亚州的一个部长、奥林匹克村所在市的市长、一个前市长和慕尼黑市警察局局长。但是,敢死队不接受交换人质。最后期限延长到中午。据说,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和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尔通了十分钟的电话,直接进行了磋商。结果是预料之中的。以色列在恐怖主义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没有交易,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交易。
德国人并不想给以色列人施压,但很显然,他们认为以色列政府不够灵活,认为没必要那样做,那样做很危险。为什么他们不愿意释放,比如说,十几个被捕的敢死队员?为什么不给恐怖分子一些面子,让他们释放人质,从而撤出慕尼黑?德国方面愿意把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安德雷斯·巴德尔交给他们,从谈判一开始他们就强调这一点。
谈判在继续。到九点的时候,期限一步一步地延迟。恐怖分子把他们的条件降低到只要一架飞机,把他们和人质送到开罗。他们说,如果以色列政府不把关押的巴勒斯坦人还给他们,他们就处决这些运动员。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让步。因为这些恐怖分子原来威胁说,如果他们从慕尼黑起飞前,他们的同伴还没有被释放的话,他们就杀死这些以色列运动员。
早上八点,给恐怖分子和人质送去了一些食物。勃兰特总理在电视上对这起事件表示悲痛,表达了圆满解决这起事件的愿望——他同时建议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要取消。取消本次运动会是以色列政府的要求,以纪念两位被杀的运动员。在勃兰特总理看来,这样做就等于恐怖分子胜利了。这当然是一种看法——象征着手足情谊与和平的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继续进行,仿佛那些运动员





![(综系统同人)[综系统]筛子补完行动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3/2322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