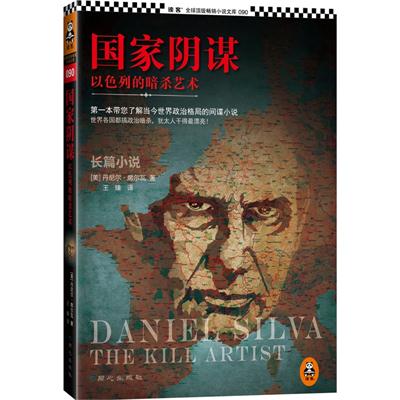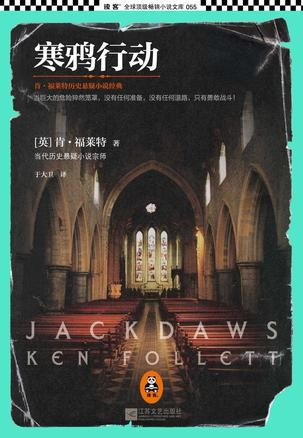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阿弗纳看见电梯门上的指示灯不停地变化。他泄气地靠在墙上,手向臀部摸去。
电梯门打开了。汉斯出来了,脸色苍白。那个希腊人跟在后面,精神错乱一般,向汉斯挥舞着拳头,嘴里说着含糊不清的希腊语,手里提着那个旅行包。
“他妈的罗伯特,他妈的遥控器,”汉斯一看见阿弗纳就说。“我只好自己动手了。”
“快点,”阿弗纳指着员工通道门回答道。“走这里。”
他抓住希腊人的肩膀,把他推到汉斯后面。
他们穿过一间半地下室,再下半段楼梯,走过一段昏暗的楼道就到了大街上。汉斯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希腊人跟在后面,手舞足蹈,唠叨不停。阿弗纳走在最后。还有几个台阶就到出口了。汉斯打开门,阿弗纳位置较低,但也能看见外面的人行道。他还看见了别的东西。
那辆黑色的“梅赛德斯”正好停在他们前面。他们恰好从俄国人等的地方出来了。阿弗纳不可能想到这一点。他们完全可以跟进来的时候一样,从大门出去,但是他们没有。他必须聪明行事,绝对不要原路返回,要把敌人弄糊涂。这样才是聪明人的做法。
这一次却弄巧成拙了。
汉斯看见俄国人的车,停了下来。后座上的那个克格勃已经把车门打开一半,正准备从车里出来。他一定听到了爆炸声,也一定看见了那道火光。他很可能是要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而就在这时,爆炸声刚过,几个人就从他面前的侧门里冲出来。俄国人肯定以为是他们干的。
确实是这样的。虽然他仍然站在半开的车门后面,但他的右手开始向左腋下伸去。克格勃准备拔枪了。
阿弗纳后来想,他也许误解了他的意思。也许那个俄国人——毕竟也是个特工,要考虑掩护自己——并不是去拔枪。他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为什么要干涉?无论那个俄国人如何精明,他都不可能肯定酒店里发生的一切会跟自己有关。他没有理由阻止这三个陌生人从他面前经过。拔枪完全是一种条件反射,未经任何思索。那个俄国人跟汉斯和阿弗纳一样,训练有素,能够作出一触即发的反应。跟没有任何疑虑的目击者和无辜的路人不一样,他在车里等的时候精神是紧张的。这也许是职业训练的一个缺陷,让人警惕得过头了,使人条件反射似的迅速作出反应。他的反应时间太短了,一触即发。一个正常的人会感到吃惊、冷漠、犹豫不决或不知所措,而这些能力他们都失去了。也许正是那片刻的延误和稍稍的迟缓——说来非常奇怪——给每天的生活增添了一丝安全感。
如果说阿弗纳误以为俄国人拔枪的话,那么汉斯也是这么想的。他看见克格勃的手移动时也是这么想的。
汉斯首先开枪了,就像以前训练时那样,连开了两枪。
那个俄国人左手抓着车门框,右手还在摸索手枪皮套时,阿弗纳也开了两枪。阿弗纳是站在台阶的最底端开的枪,有一个角度,他想通过打开的车窗击中目标,他知道低速子弹打不穿“梅赛德斯”钢制的车门。实际上,他看见汉斯的子弹打中了,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子弹打中没有。他希望自己没有打中。不管打没打中,那个俄国人已经朝后倒在座位上。坐在驾驶座上的同伴伸出手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朝里面拖了拖。那个司机一定非常有力,他用一只手就把那个受伤的人拖进了车里,然后砰地把门关上。克格勃的“梅赛德斯”摇摆着车尾疾驰而去时,车轮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
阿弗纳一边把枪收起来,一边用空着的那只手抓着那个希腊人的衣领。此举是多余的,酒店里那个希腊服务员已经吓昏过去了。远处的大街上,罗伯特的汽车咆哮着发动起来。车子转过一个“U”形弯道,眨眼之间来到他们面前。阿弗纳把希腊人紧紧抓在手上的旅行包夺过来,推着他在汉斯后面上了罗伯特的车。然后他向停在马路对面的那辆绿色“因帕拉”跑去。车里的那个希腊人把车门打开。“开车,”他边上车边对他说。“不要太快,明白吗?”
那个希腊人点点头。他跟他那位同胞不一样,非常镇定。阿弗纳这时想,即使他看见了刚才的枪战,一定没看见就在他眼前爆炸的燃烧弹。
他们回到安全屋,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大家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首先,他们得安慰酒店里那个只会说希腊语的服务员。他彻底吓傻了,不是坐在那里发呆,嘴里“嘣嘣嘣”地咕哝着,就是站起来,对汉斯晃动着手指头,用希腊语大骂他。阿弗纳把他带到一边,让他和那个年长的希腊人待在一起,而且给他手里塞了一张一百元的钞票。就像水能浇灭火一样,这张钞票发挥了作用。给了他五六张钞票之后,火终于熄灭了。后来,阿弗纳也给了那个年纪较大的希腊人五六张钞票。希腊人走后,罗伯特说:“喂,我知道你们这些人的感受。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我检查过发射器,是好的。我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们卖给我们的这个破玩意一点都不好。”
罗伯特应该保持沉默的。这个话题使他们激烈地争吵起来。这是他们一起执行任务以来第一次争吵。汉斯坚持认为,如果罗伯特真的怀疑炸药有问题的话,就应该建议推迟行动。如果他们不听他的,那就不能怪罪于他。而实际上,该怪罪的就是他。他只是自言自语似的咕哝“我觉得这个玩意不好”——汉斯说,罗伯特每次都是这样——不明确建议取消。
尽管汉斯有汉斯的想法,但阿弗纳还是跟他大吵了一架。毕竟有一套指挥系统——按常识,汉斯应该在采取一套新方案之前与其他人商量的。他抓起装有四颗炸弹的旅行包,连炸弹的保险都没有拆掉,就向穆扎斯的房间冲去。很显然,是汉斯让那个毫无防备的希腊人跟他进的电梯,并让他叫穆扎斯开的门。然后——那个阿拉伯人摸索着开门时,他示意那个希腊人站到一边——他从旅行包里拿出一颗炸弹。穆扎斯打开门时,汉斯朝门上踢了一脚,像扔手榴弹一样,把燃烧弹扔了进去。但他没有把他的想法告诉罗伯特,也没有告诉阿弗纳。
“如果我告诉你们的话,”汉斯阴沉地说。“你们会不同意。但我相信你们会同意,这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但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浪费更多宝贵的时间。所以我走了捷径。”
“为什么是惟一的解决办法?”罗伯特说。“你让那个希腊人把他叫出来,用枪打死他。”
“用枪打死他?”汉斯愤怒地说,然后转向阿弗纳。“你看,他简直不动脑子!”
阿弗纳只得同意汉斯的说法。用枪打死穆扎斯不能解决房间里的炸弹问题。一旦罗伯特的遥控器失灵了怎么办,惟一的办法就是汉斯那个办法——但他不能擅自行动,他至少应该告知他们。
“如果你在爆炸中受了伤怎么办?”阿弗纳问他。“如果我们扔下你,或者因为留在那里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而被抓住怎么办?你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还有,你为什么要向那个俄国人开枪?”
“因为他准备拔枪。”汉斯义愤填膺地说。“难道我要等他先向我开枪吗?你为什么向他开枪?你向他开枪的理由跟我是一样的。”
“我向他开枪是因为我看见你向他开枪了。”阿弗纳回答道。但没有说服力。这场争吵变得有些孩子气了。“不管怎么说,”阿弗纳补充道,“也许我误解他的意思了。”他当然希望自己是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最不喜欢因为杀了一个特工而跟克格勃纠缠——或者与伊弗里姆以及其他的加里西亚人纠缠。然而,如果那个俄国人真的拔枪的话,他们还能干什么呢?
他对汉斯的行为感到吃惊。这个戴着老花镜的汉斯,这个看起来像一支铅笔的汉斯,这个镇定、有办法、与世无争的汉斯。如果斯蒂夫,或者罗伯特,甚至阿弗纳,突然扛起一包炸药冲出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是汉斯?冲动之下冲了出去,踢开房门,而且后来向俄国人开枪?你真的永远也搞不懂人是怎么回事。
对于汉斯看似疯狂的行为,爱抚仍然让他感到不安。这也许是由当时的环境决定的。汉斯有勇气去面对。如果那些炸弹没有爆炸,或者没有拆除,除了等那个恐怖分子在房间里时向他扔去一颗炸弹之外,还能做什么?汉斯没有错,如果他们停下来讨论的话,那可能就太迟了。
“好吧,”阿弗纳最后说。“我们别说这个了。这个活是我们大家共同承担的,我们回到法兰克福以后,让卡尔来评判吧。”
其他人都同意这样做。虽然阿弗纳是领导,但卡尔从一开始就是——部分是因为他的年龄和经历,但主要是因为他的个性——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犹太学者和突击队中裁定是非的人。尽管卡尔没有参与,他也会非常公正和客观。如果还有别的办法他们可以采用,卡尔也会告诉他们的。
他们又在雅典待了一个星期以后,一个接一个地飞走了。根据报纸上的报道,酒店的爆炸一定像7月4日那天一样。它确实引发了一场大火,但只烧死了穆扎斯。有些报道提到一个德国游客受了点轻伤。媒体上只字未提枪击俄国人的事情。
在法兰克福,他们把这件事跟卡尔讲了。他只是抽着烟斗,抬起眉毛,对着天花板翻白眼。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斯蒂夫的反应恰恰相反。他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似乎非常不安。“怎么样,”斯蒂夫对阿弗纳说。“我们把他干掉了。他妈的俄国佬,我们也把他干掉了。怎么了,伙计们,你们害怕了?”
“喂,安静,斯蒂夫,”卡尔终于说话了。“我不在那里,没法评判。关键是,你们都回到了这里,好好的。我们还是向前看吧。”
很显然,只能这样。但阿弗纳仍然忧心忡忡,说不清什么原因。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顺利。为了给十一个以色列运动员报仇,他们已经干掉了兹威特、汉姆沙里、阿尔一契尔、阿尔一库拜斯以及贝鲁特的纳杰尔、纳塞尔和阿德宛。还干掉了穆扎斯和那个克格勃。关键是,没有费什么力气。
也许正是因为没有费什么力气,阿弗纳胸口才有一种痛苦的压迫感。
第十一章 穆罕默德·布迪亚
自从9月末他们离开日内瓦的米迪酒店以来,阿弗纳第一次,也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害怕了。他记得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在部队里没有、在“六日战争”期间没有、训练的时候没有、做一名普通特工的时候也没有,甚至在执行这次任务之初也没有。到4月中旬他才有这种感觉。当然,他知道紧张、吃惊,甚至害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4月份的感觉与这些截然不同。它不是一闪即逝的肾上腺素的奔突,不是稍纵即逝的心跳到嗓子眼的感觉,也不是转瞬即逝的剧痛,而是一种悄然存在、让人萎靡、几天都挥之不去的焦虑。无论干什么,这种感觉都始终笼罩着他。无论是在餐馆里吃羊排,还是看自己喜爱的演员路易斯·德·凡那斯主演的电影——阿弗纳一定把这位法国喜剧演员的所有电影都看完了——这种感觉始终存在。有时候像钝痛,有时候像有个肿块。他感到恐惧了。
起初,阿弗纳以为是吃了什么东西的缘故。
他很快发现,这种感觉是恐惧。他感到愤懑和羞愧。一想到其他人,卡尔、斯蒂夫、汉斯或者罗伯特会知道他害怕时,他就羞愧难当。对阿弗纳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此了。为了克服这种情绪,他故意经常这样说:“伙计们,我害怕。”“伙计们,我很担心。”交替这样说。当然,这是部队里一种自夸的风格,是惟一许可的形式,通过强烈反对其反面来表明自己的勇气。但他一定做得太过分了。有一天,只剩下他和卡尔时,卡尔非常平静地对他说:
“我知道,我也非常担心。”
他说话的语气使阿弗纳再也不敢说自己害怕了。
“妈的,”他说,“你也害怕?我想知道为什么?”
但卡尔摇了摇头。他们再也没有谈过这个话题。
没过多久,阿弗纳就知道了答案。当时他在纽约跟肖莎娜待了一个星期之后回来。也许跟他发现的时候有关,不是直接的关系,而是间接的关系。
他们的团聚并不全是欢乐。肖莎娜在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搬进了阿弗纳在布鲁克林给她找的公寓里。她和女儿葛拉、小狗查理搬进去时,阿弗纳正在贝鲁特。她感到很孤独。她以前从来没有在以色列以外生活过,她也不知道阿弗纳在哪里,还要多久才能来美国。三个星期以后他来了。肖莎娜紧紧箍住他的脖子,箍得他有点疼了。如果阿弗纳觉得他们被迫过的这种日子肖莎娜以前觉得无所谓的话,那她这次拥抱就让他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
他们在床上度过了头两天。第三天早晨,他从梦中醒来。在梦里,有人正看着他。他睁开眼睛,看见肖莎娜正坐在床边看着他的脸。
“怎么了?”阿弗纳睡眼惺忪地问道。
“我不知道。”她回答道,语气非常严肃。“我的意思是,你的头发没有白,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看起来老了十岁。”
他闻听此言,两天来几乎消失的恐惧又像拳头一样击打在他的胸口上。他什么也没说。后来刮胡子的时候,他不停地端详镜中的自己。肖莎娜是对的。他在过去七个月中老了好几岁,看起来像个三十四五岁的人了,而实际上只有二十六岁。
“喂,”他对镜子中的自己大声说。他从来不这样的。“看来你愚弄得了你的脑子,可你愚弄不了你的身体。”
“你说什么?”肖莎娜在卫生间外面问道。
“没什么。”
在那个星期剩下来的时间里,他开着租来的车,带着肖莎娜在纽约逛了一下,让她看看这座城市,别让她太陌生。他来纽约之前,她最远只走到了拐角处的杂货店。肖莎娜谁都不认识,交朋友不容易。他把她介绍给了自己的一两个熟人。她跟往常一样,从无怨言。一天下午,她在这套光线不好、只有一间卧室的





![(综系统同人)[综系统]筛子补完行动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3/2322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