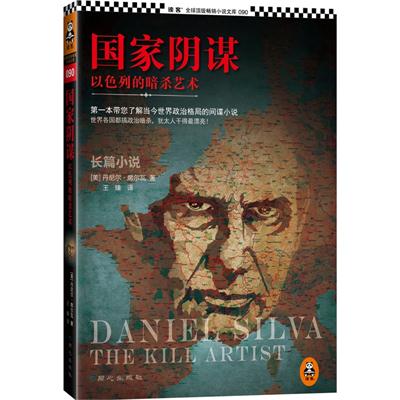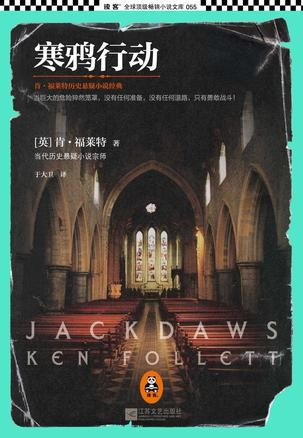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恐怖分子胜利了。这当然是一种看法——象征着手足情谊与和平的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继续进行,仿佛那些运动员被杀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也同样容易被看作是恐怖主义的胜利。不管怎么样,所有参赛国的旗帜必须下半旗,一直到下午为止。后来,十个阿拉伯国家派代表抗议,德国人才被迫把他们的国旗升到旗杆顶上。
大约晚上十点二十分,两架直升机在奥林匹克村附近一块草地上起飞,飞往慕尼黑的菲尔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九名人质和八名敢死队员乘坐“大众”牌公共汽车到达直升机场。虽然西德当局全力配合以色列政府,已经决定不让恐怖分子和人质一起飞往开罗,但在敢死队向直升机转移的时候没遭遇任何埋伏。事后回忆起来——虽然事后总是容易看得明白一些——这也许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好的机会。
菲尔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距离慕尼黑市中心十五英里,行动很快展开。十五分钟以后,也就是大约晚上十点三十五分,两架直升机落地了。一架上面有四名以色列人质,另一架上面有五名。直升机降落在距离那架727喷气式飞机大约一百码远的地方。这架727飞机很显然是准备把这些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质送往开罗。四个敢死队员从直升机上下来,去检查那架飞机。五分钟以后——在光线不好距离又远的情况下——五个神枪手向他们开火了。
有几个恐怖分子被打倒,还有几个立即开枪还击。两架直升机上的四个德国机组人员准备逃走。两个成功逃脱,另外两个在交火中被捕,伤势严重。以色列人什么也干不了。他们坐在跑道上的直升机里,被绑得紧紧的,眼睛也被蒙了起来。
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敢死队没有立即把他们杀掉。也许他们觉得这是最后一张牌,也许他们正忙着还击神枪手,也许他们正忙着躲避神枪手的子弹,也许他们不想杀死九个手无寸铁的人:最疯狂的亡命之徒在无助的人面前也有一种基本的怜悯之心。敢死队拒绝了德国人让他们投降的提议,即使他们知道这时候投降仍然能保住性命。
双方交火持续了大约七十五分钟。大约午夜时分,由于无法赶走躲在直升机下面的恐怖分子——有人质在场,他们使用的火力有限——德国人决定在六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发起攻击。几乎就在发起攻击的同时,一个恐怖分子把一颗手榴弹扔进了那架上面有五个以色列人的直升机上。直升机成了一团火球。几秒钟以后,另外两个恐怖分子开枪杀死了第二架飞机上的其余四名人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装甲车的攻击晚几分钟的话,泽福·福德曼、雅科夫·斯普林格、埃里泽·哈尔凡和巨人约瑟夫·古特弗洛德也许还能活下来。四个以色列队员正设法把绳子弄松——因为人们后来发现把他们绑在椅子上的粗绳结上有齿印——他们也许很快就解开了。这让直升机外的两个恐怖分子大吃一惊。毫无疑问,以色列人试图夺过敢死队的武器来解放自己。至于第一架飞机上的阿米卒·沙皮拉、大卫·马克·伯格、安德雷’斯皮泽、马克·斯拉凡和科哈·朔尔,就不可能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了。他们的尸体烧得无法辨认。
两个活着的恐怖分子还在负隅顽抗。警察和边防部队在十五分钟后杀死了其中一个人——这个人名叫埃萨法第或者“埃萨”,朝第一架直升机上扔手榴弹的就是他。大约就在同时,德国人俘虏了一个伤势严重的恐怖分子,名叫巴德朗。另外两个,埃尔一德纳维和“萨米尔”塔拉菲克也被俘了。他们没有受伤却假装死了。
最后一个恐怖分子是一个瘦长结实的老烟枪,名叫托尼。他喜欢把自己当作阿根廷的拉丁美洲革命家“格瓦拉”。他也许缺乏很多做人的品质,但不乏勇猛。托尼与德国人打一会,躲一会,耗了一个小时,一个边防士兵的脖子上还挨了他一枪。最后他被逼至一隅,在凌晨一点三十分被击毙。战斗终于结束了。
第二天,奥林匹克运动会继续进行。那届奥运会,苏联获得五十枚金牌。美国位居第二,获三十三枚金牌。
第一部 特工的诞生
第一章 阿弗纳
阿弗纳在打开那个棕色的信封之前,就知道了那封信的大致内容。至少,他知道是谁写的,为什么写这封信。在这样的事情上,他的第六感觉总是很准。
这也有道理,因为他的前五种感觉都一般。他的判断力应付日常生活没问题,但要从事他梦寐以求的真正光辉的职业:战斗机飞行员和双向飞碟射击冠军就有些勉强了。他的听力不出众,触觉也无法使他成为一名机械大师。但是他的第六感觉则完全不同。
那些棕色的信封——现在他手里就拿着一个,绝对与以色列政府有关。但是政府的信,甚至军队的信,信封上都会有某种标志——比如说某某部——而这封信上面什么也没有。
信的内容只有五行,是用一台老式希伯来语打字机打出来的,这台打字机似乎在回避“M”这个字母,总是把它打成了“E”。信中问阿弗纳对一个活有没有兴趣。“你也许想跟我见一面,那就在特拉维夫的弗雷希曼街和笛宗高夫街的拐角处吧。”信中写了见面的时间和咖啡馆的名字,还留了一个电话号码。万一他对这个活不感兴趣,或者这个时间不方便,他可以给他打电话。落款是“您诚挚的莫舍·约哈南”,一个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的名字。
这是1969年5月初。这年阿弗纳二十二岁,身体健康。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刚刚从精锐部队服役归来。他跟其他人一样,参加过“六日战争”,在预备队中任上尉——在特种部队里服役过的人都是上尉。
“好极了。”他一边上楼洗澡,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这两样东西——在大中午洗澡,用英语说“好极了99——代表了阿弗纳的本质。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两样更接近他的本质了。部队里有几个人会用一只橘黄色板条箱、几根绳子和一只破水桶做一个移动的澡堂?又有几个人会在其他人的狂笑声中把它用带子捆在坦克上,在沙漠里演习时随时带在身旁?除了澡堂之外,还有一只板条箱,中间切开一个方方正正的洞,这就是内盖夫沙漠上的一个自制的临时厕所。对阿弗纳来说,他不愿意像个猴子一样,蜷缩在沙漠里,让屎壳郎在背上爬来爬去。
并不是这种整洁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他碰巧是个爱整洁的人,他并不以此为耻。如果在整个以色列军队中,他是惟一一位在复员时把餐具像四年前发给他的时候那样一尘不染地交回去的,那又怎么样?
毫无疑问,这有点夸张。但即使是夸张,也代表了阿弗纳的本质。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截止到现在为止,阿弗纳还没去过美国。但他的母亲总是说他小时候开口说的第一个字——那是1947年,以色列建国的前一年——不是“妈妈”或者“爸爸”,而是“美国”。这或许有些杜撰的性质,但听起来合情合理,当然听起来也像“阿弗纳”的发音,“阿弗纳”的发音跟“美国”这个词的发音相似。他长大以后,沿着雷霍沃特空旷干裂的大街,赶着看下午场的电影时,美国就成了他全部的精神生活,成为他的梦想。什么拉娜.特纳,什么约翰·韦恩,什么丽塔·黑沃斯,都是他梦想中的人物。
正是从这些电影中,阿弗纳学会了第一批英语单词——或者更确切地说,美语——像许多以色列人一样,这是一种他自己的语言,他怀着极大的热情一直使用的语言,尽管并不十分精确。电影中的美语跟学校里学的英语不一样,是你可以品尝和触摸的东西。你可以将它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好了,先生,这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
阿弗纳现在再也不可能过多地考虑这些事情了,一个年轻人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时,谁会浪费时间去操心孩提时代的梦想呢?现在他离开了部队。当时他们请他留下来,求他留下来,哄他留下来。但是他不留。四年已经够了。但是,现在呢?是要这个活还是要玛丽·肖莎娜还是去上大学?
阿弗纳洗完澡出来,身上凉爽干净,皮肤黝黑,他朝镜子里瞥了一眼,然后用毛巾把自己裹起来。他长得像他父亲——虽然并不是一模一样。父亲的块头比他的大,头发颜色也比他的深,尽管父亲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而且使他变得难以置信的衰老。现在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肌肉也变成了脂肪,他的精神——唉,也时好时坏。父亲一定与浴室凳子上的那个棕色信封有关,虽然不是直接关系。阿弗纳相信这一点,父亲绝不会跟他们谈这个的。相反,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会阻止他们。“我的儿子,”他会对他们说,“不能重蹈我的覆辙。”
然而,阿弗纳甚至不会把那封信的事告诉他。他自己会对他们说不的,正如一两个月前他不得不对阿曼的那些人说不一样。“如果你不愿意在部队里做一名现役军人,那好吧。”他们对他说,“那军情局怎么样?”“不去。不去,谢谢。”
他会对莫舍或者棕色信封里的任何人说不。不过,他会去见那个人。星期一总是要去特拉维夫的,因为要接肖莎娜。为什么不去见见他们,听听他们怎么说?听一听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两个月来,阿弗纳一直在向以色列航空公司求职。所有的人都说进不去。但是他通过他的一个姑妈把资料给了一个人。这个人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在航空公司总部工作。当然,做飞行员是没指望的。他的各项科学测验都没有通过。而且,飞行员都是空军。但是,为以色列航空公司干活也是在为一家航空公司干活。即使做一名乘务员或者在办公室工作也行。也许还有机会旅行,或者短时间离开以色列,去看一眼远方奇妙的世界呢。或者,谁知道呢?也许能遇到一两个训练时认识的、后来当了空军的老朋友呢!他们也许已经当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了,也许有一天还会让阿弗纳试一下着陆,或者至少试一下起飞呢。
阿弗纳坐在马桶盖上,做了一个波音707顺利着陆的姿势。这是加油器。喷气机的巨轮像两片羽毛飘浮在跑道上。这也难怪,自从十岁开始,他就一直在浴室里练习飞机着陆。阿弗纳把波音飞机滑进棚里之后,开始刷牙、穿衣。母亲出去看什么人了。肖莎娜在特拉维夫。父亲——嗯,阿弗纳想,他可以乘公共汽车从雷霍沃特到他父亲家里,到父亲家里之后也许还能借一下他那辆破旧的“雪铁龙”呢。他身上有足够的钱坐公共汽车。在星期六的以色列,钱没有多大用处。就娱乐而言,这个国家封锁得比鼓还要紧,除非你想去餐馆里吃冰冷的三明治。
但在星期一,有“雪铁龙”还是不错的,尽管它在中东是一种最老式的车子。用车去接肖莎娜可以让他们不用搭乘别人的便车,虽然她并不是特别在意。肖莎娜身材苗条,面庞白皙,头发呈蜜黄色,拥有一副埃及人石刻般瘦削的贵族式的容貌,看起来像王族。而骨子里,她却是个地地道道的以色列人。她意志坚强,也没什么因溺爱养成的坏习惯。阿弗纳第一次去她父母家时,用错了一个词,那是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前一天晚上他们刚刚在他们都认识的一个朋友家认识,他没有记住她的名字。她的小表弟给他开了门。
“你是?”
“呃,呃……公主在家吗?”
除了她的外貌之外,用这个词来描述肖莎娜并不合适。公主?那个小孩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差点把门砰地关上了。幸运的是,肖莎娜这时正好从楼上下来,阿弗纳才没有碰一鼻子灰。
她盼着他会带她去看一场电影呢,但他却不得不在当天晚上回到部队里。他刚刚入伍,不想一开始就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管她公主不公主呢。
“你今晚必须回去吗?”她问他。“其他的人星期天才回去。”
“在我的部队里,今晚就得回去。”
“那好吧,我们散散步吧。”
就这样,他们去散步。那时她还不满十八岁,但是她已经非常清楚,别再问他什么问题了。在以色列,谈到部队里的事情时,人们不再往下问。肖莎娜当然也不问。以后也一次没问。
从他们第一次约会开始,只要他有一两天假期,他们就这样,平均每个月散一次步,看一场电影。假定一年十次,四年就是四十次。二十次散步,二十场电影。星期五搭便车回到雷霍沃特的母亲家中时,一般是在晚上十一点或者午夜。“喂,妈,我回来了。”把乌兹冲锋枪朝墙边一靠,把衣服一挂,倒头就睡。
但是,现在差不多三年过去了,要考虑未来了。有一条路比较简单,而且在他的大多数朋友看来,这条路似乎比较自然。这条路正好在阿弗纳现在站立的这个酷热难当、尘土飞扬的拐角处。他在这个拐角处等那趟破旧的、摇摇晃晃的公共汽车。肖莎娜的叔叔准备给他们借些钱,在这里的一块空地上建一栋房子。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阿弗纳和肖莎娜的友谊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或者说,二十次散步和二十场电影的考验。她很快就可以拿到教师资格证书。至于他嘛,他至少有在部队服役的背景。许多幸福的婚姻都是建立在不那么光明的前途之上的。
但是,他们还没有背上“法兰克福”这个负担。法兰克福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城市。
法兰克福是阿弗纳一个人的负担。肖莎娜是个地地道道的以色列人,四代都是以色列人。虽然她也有欧洲的背景,但是这对她来说毫无意义。二十一年来,她从来没有闻到过神秘、幽暗、仙境般的森林在两天雨水的浇灌之后散发出来的浓烈的香味。对她来说,雪只是个单词而已。也许只有少数几个幸运的孩子才能在特别寒冷的冬天在耶路撒冷的山上见到那么几个小时。但是她从来没有见到过,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一座超过二十年历史的城镇。当然,这座城镇实际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她跟阿弗纳不一样。
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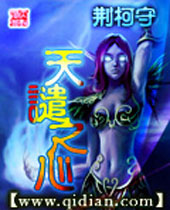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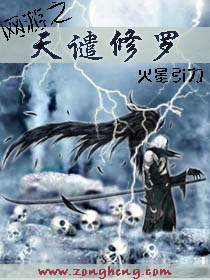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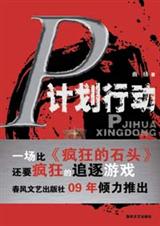
![(综系统同人)[综系统]筛子补完行动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3/2322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