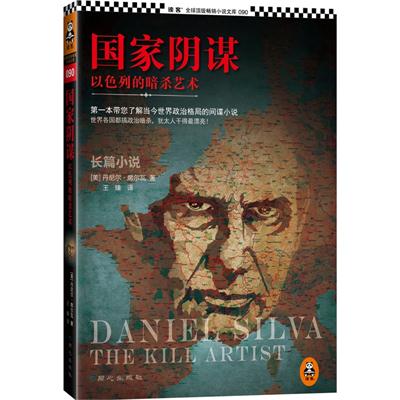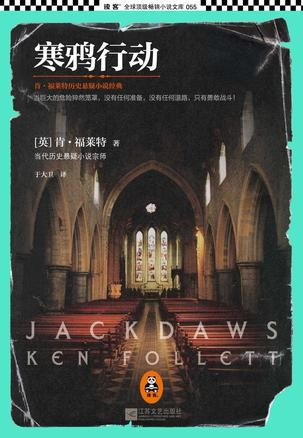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4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在哪里给我打电话的?”他问道。
“我在纽约,”伊弗里姆说。“我想跟你见个面。”
“当然可以。”阿弗纳回答道。“你为什么不来我这里?”
“不,不,”伊弗里姆说。“我不想去你府上打扰你。你为什么不来酒店?”
他们说好第二天早上在酒店大堂见面,这样阿弗纳就不用问伊弗里姆他这次用的是什么名字了。虽然肖莎娜的电话不可能被录音,伊弗里姆毫无疑问是从公用电话亭里打的,时刻警惕已成为他的习惯。
“很高兴见到你,”第二天,他们坐在酒店里那间狭小褪色的房间里,伊弗里姆这样说。“你看起来休息好了。哦——还有一个活我们想让你去干。”
他并不感到吃惊。阿弗纳头一天想了一个晚上,最后得出结论,伊弗里姆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才想跟他在纽约谈一谈的。
怎么回答,他也预先打好了主意。他还没有做好立即就干的准备。事实上,他在找借口。
“这是个什么活?”他问道。“跟以前那个一样吗?”
“不一样,”伊弗里姆说。“跟那个完全不同。”他那个让人发疯的习惯仍然没有改变。阿弗纳从第一次见他起就记住了这个习惯。他把一张餐巾纸举到脸上,阿弗纳以为他要擤鼻子,结果却什么也没干。“完全不同。首先,在不同的大陆。南美。”
阿弗纳一言不发。
“惟一相同的是,”伊弗里姆继续说,“你不能带家属。就这个。但我们会安排你,呃,两三个星期回一次家,或者每七个月回一次家,或者一年回一次家。”
“不行。”阿弗纳说。他说“不行”的口气非常平淡。
伊弗里姆抬起头来,显然很吃惊。他甚至半心半意地笑了起来。“那好,”他说。“也许你想考虑一下。”
“没什么好考虑的。我不想干。”
伊弗里姆沉默了几秒钟。他把手放在阿弗纳的肩膀上。“瞧瞧,我们是朋友,”他说。“你怎么了?”
阿弗纳没想到自己的口气那么严厉,也许因为他有些为自己感到耻辱。他在干什么?怪不得伊弗里姆那么吃惊:一个以色列突击队员拒绝执行任务,这是不寻常的。“好吧,因为我们是朋友,”他回答道。“所以我才告诉你。我们的家庭关系无法再忍受那样一次旅行,而且……呃,我对它再也没有兴趣了。”
伊弗里姆把手臂放下来,走到窗前。他站在那里,看着窗外。几秒钟之后,他转过身来,面对阿弗纳。“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他说,“我真的很遗憾听到答案是否定的……”他停下来,换了一副口气。“喂,也许是我的错。我太快给你打电话了。你还需要一些时间考虑。”
“我不需要时间。”阿弗纳回答道。“我很高兴你给我打电话,这样我才能告诉你我不想干了。好吗?对不起。”
伊弗里姆又坐下来。“我明白,”他轻轻地说。“也许你以为我不明白,但我明白。相信我。”他用真正同情的口吻说。这就更糟了。阿弗纳以为这种口吻的意思是:我明白你经历了这场战斗之后感到很累。我明白你很紧张。我明白你缺乏长期进行下去的能力。这不是讽刺,也不是质疑,但这种说话的方式就像医生跟病人说话一样,一个晚期病人。虽然这不是他的错,但是医生也无能为力。这一刻是阿弗纳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候。就如同卡尔所说,在十秒钟之内就从英雄变成了狗熊。
伊弗里姆接下来说的一件事更为糟糕,尤其是以虚情假意的口吻说出来的时候。
“听着,别担心,”他说。“别这么郁闷。没事的。我们要让你和你的家人回到以色列。在以色列,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这些工作同样重要。”
“我不想回以色列。”阿弗纳说。
伊弗里姆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我想在纽约待一段时间。”阿弗纳慢悠悠地重复道。
“你是什么意思?”伊弗里姆问道,“你不能这样。”
“我不能这样是什么意思?”阿弗纳说,抬起目光,看着他的顶头上司。“我想待在纽约。”
“但你没法待在纽约,”伊弗里姆说,一副对小孩子说话的口吻。“你没有证件,没有工作,什么也没有。你在这里能干什么?”他展开双手,在空中挥舞着餐巾纸。“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在说留在这里。”阿弗纳通情达理地说。“虽然我还不知道在这里能干什么,但我并不担心。我想跟家人待在一起,就这么回事。别的我什么也不想知道。”
伊弗里姆耸耸肩,表情痛苦。“那好吧,”他说。“也许我来的不是时候。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至少,我希望不明白你说了些什么。你是在告诉我你打算做个移民?你要我回去给你的母亲和父亲说一声?你在以色列出生,打算离开祖国?”
阿弗纳想说“是的”,然而却没有。他深吸了一口气,那个字还是没有说出来。他胆子非常小,就是不能当着伊弗里姆的面把它说出来。那时说不出来。
尽管他已经想好了,尽管他跟肖莎娜讨论过了,但他还没有真正作出决定。也许他永远作不出这个决定。也许他永远没有勇气看着伊弗里姆这样的人的眼睛,把他的决定说出来。
或者把决定告诉他母亲这样的人。
“我不是离开祖国。”他移开视线,说。“我会,啊,我也许会回来的。但是现在……我只想待在外面。仅此而已。”
“那好,”伊弗里姆立即说,“如果你告诉我你想在这里待几个月,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但现在就不谈了。我要去华盛顿几天。回以色列之前,再跟你谈谈。同时,也跟你的妻子谈谈。我相信你的妻子是不想待在美国的。”伊弗里姆又笑了起来,好像这个想法诉诸文字就滑稽可笑了,然后补充道:“我没想跟你说得那么尖刻。请原谅,我误解了你,我以为你说你要永远待在这里。”
他把手向阿弗纳伸过去。
阿弗纳握了握他的手,但仍然不敢正视伊弗里姆的目光。“虽然我没有说‘永远’,但我的意思是几年。在这里,或澳大利亚,或者别的地方,我还没想好。我的意思是这样。”
“再谈吧,再谈吧。”伊弗里姆快速地说。“以后再谈。”他开始收拾证件,放进自己的手提箱里,再也没有看阿弗纳一眼。阿弗纳简直无法离开酒店的房间。他非常生气,也非常愧疚。
“你……你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吗?”他问伊弗里姆,对自己越来越生气。伊弗里姆停止在手提箱里摸索,看着他。“不来,”他冷漠地说。“谢谢。我还有人要见。”
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阿弗纳没有直接回家。他去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一直从东边走到哈得逊河,对曼哈顿拥挤的人群和车流视而不见,一连走过了一百个红灯口,连看都没有朝周围看一眼。他在冥思苦想。他不那样说,应该怎么跟伊弗里姆说呢?他连给自己都解释不清楚,又怎么能给他解释清楚呢?为什么他不愿意回以色列?
他一直希望在美国生活,难道是因为他虽然爱国却从来没有把中东当作自己的家园?还是因为那里沉重、压抑,有时候很冷但永远都不新鲜洁净的空气?这里的空气,无论是潮湿还是干燥,是恶臭还是芳香,都不祥地笼罩着他,烧烤着他,让他麻木,把沙子吹进他的眼睛里。而不像欧洲的空气,从容、柔和、平凡、雅致,让他留恋。
不,不仅仅是空气。难道是因为他失败了?至少在他的眼里失败了?因为这个一心想当英雄的荷兰小男孩终于被骗成了一个英雄?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嘲讽?因为每次有人拍他的背或者跟他握手的时候他都不得不想为什么?他们把卡尔、罗伯特和汉斯忘了吗?负责这项任务的头回来了,而部下却没有回来——他还是英雄吗?甚至连部下的尸首都没有。按以色列的传统,伤者或者牺牲的同志的尸体是从来不会丢下不管的,即使冒着十几个人的生命危险也要把他弄回家。大部分部下都牺牲了而主要目标都没有干掉,还是英雄?恐怖组织头子们还在欧洲到处跑,还是英雄?
也许他应该向伊弗里姆这样解释。也许这也不是真正的原因,而是别的原因。但即使他明白了,他仍然不能说出来。他试着跟肖莎娜说了一下,然而却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他不能自圆其说。然而到这个时候他终于知道了,他知道他永远无法让别人明白了。
只要他在以色列,他就必须成为一个荷兰小男孩。他只想做个跟别人平等的人。也许对其他以色列人来说不是这样的,但对他来说是这样。谁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他不是加里西亚人。也许因为他跟他的母亲不一样。也许因为他觉得在法兰克福才更觉得像在家里一样。也许因为他不像集体农场的那些农民那样吃苦耐劳。但是,如果他不是一个荷兰小男孩,那他就谁也不是。根本谁也不是。
但是,没有这么多要求的国家难道没有吗?在这些国家里,一个人就是他自己,为自己而活,没有二等公民或者心虚的感觉?这些国家不希望一个公民成为英雄?成为一个集体农场的农民英雄,一个开拓的英雄,一个士兵英雄?在这些国家里,一个人不愿意去执行一项任务时,不必感到自卑?
当然,这不是以色列的错。阿弗纳也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这是他的错。以色列的标准很高,原因就在这里。有些人能够很自然地达到这些标准——比如母亲——许多人可能不在意。还有许多人也许没有意识到还有什么标准——伟大高尚、英勇无畏、勇于牺牲——要他们去达到。他们记不住什么标准。他们工作,选举,互相大吼大叫,每年去部队里服役,在以色列过着非常快乐的生活。他们不必成为英雄。
阿弗纳必须成为英雄,只要他是以色列人。这是他的错,而不是别人的错。他不能成为英雄也不是别人的错。因为事实是,他不是一个英雄,只是个普通人而已。他讨厌胡说八道,讨厌把自己装扮成别人。而在以色列,必须这样。成为英雄,或者假装是另外一个人。不一定要成为突击队员,去炸碉堡,挖地雷,搜恐怖分子,但要成为母亲那样的人。靠一点退休金度日,为家庭做出牺牲,沦落为一个集体农场的农民,不要回报,说什么:犹太人有了一个家,这就是回报,等着别人找上门来。
还眼巴巴地看着加里西亚人分布丁。
不。
他再也不愿意这样。他不愿意成为来自那海瑞亚的那个小“野客”。如果再有人把犹太人推下海的话,他就会回去投入战斗:这一点毋庸置疑。哪怕七十岁了,他也要回去。但与此同时,他要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在美国。
几天后,伊弗里姆在华盛顿给他打来电话。“你在考虑打算怎么办的时候,”他说,“还有一件事我希望你考虑一下。”
“什么事?”阿弗纳问道。
“你仍然在合同期内。”
起初阿弗纳以为他听错了。他在公用电话亭里,拨了华盛顿伊弗里姆那个电话亭的号码,女王大街上的交通很繁忙。“你说合同吗?”他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有你签字的那份文件,”伊弗里姆说。“在我办公室,记得吗?你10月份回来的时候,读完之后签的。”
阿弗纳记得很清楚。他记得“赎罪日之战”以后在伊弗里姆的办公室里签过一份文件。但他没有那么麻烦地还要去读。
“你的意思是,”他问伊弗里姆,“你让我签过一份我永远为你们这些家伙干活的文件?”
伊弗里姆大笑起来。“还没有那么糟,”他回答道。“只是一份三年的合同,每年要续签的。你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已经重签了。”
“等一等,”阿弗纳有些头昏脑涨地说。
“不管我签的是什么,但我不在的时候,没有我的同意,你们怎么能续签呢?”
“你什么意思,你的同意?”伊弗里姆说。“我们不需要你的同意。我们想这样做就行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通知你。”
“但你们没有,我在国外。”
“我们放在你的档案里了,”伊弗里姆回答道。“这是完全合法的,相信我,按我说的去做。你在考虑今后的打算时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你放了我的什么?”阿弗纳慢条斯理地说。即使伊弗里姆花一辈子的时间来想,他都不可能想出一个更好的激怒阿弗纳的办法来。他妈的加里西亚人,放在我的档案里了,他以为他现在逮住我了?他这辈子都别想!“告诉你,”阿弗纳对伊弗里姆说。“既然你已经放在我的档案里了,那你就把我的文件随便寄到哪里吧,寄到南美吧,我在纽约。”
“不要那么大的火气嘛,”伊弗里姆说。“我只想打个电话告诉你,没有别的意思。我以为你想知道呢。”
“好吧,你已经告诉我了,”阿弗纳回答道。“现在让我告诉你,我哪里也不去,我也不会回家。”
“那你就违反了合同。”伊弗里姆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阿弗纳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飞到了日内瓦。
由于他使用的是另外一本护照,所以没有住在米迪酒店。但他联系了回到欧洲执行常规任务的斯蒂夫,到达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在以前最喜欢的莫凡彼餐馆跟他见了面。“你状态不佳啊,伙计。”斯蒂夫对阿弗纳说。
“为什么?”阿弗纳问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斯蒂夫摇了摇头,说。“你有麻烦了。”
“你在说什么?”
“我在伊弗里姆回家的路上见到他了,”斯蒂夫说。“他告诉我他在纽约跟你谈过。他说他过去对你期望很高,还说你一点都不讲道理。”
“我不想干了。”
“我知道,”斯蒂夫说。“他告诉我了。你打算去干什么?”
“我还不知道干什么。我想把我的钱拿了就走。很久以前我们就谈过这个的,还记得吗?卡尔也这样说了,我们说,一结束我们就走,我们都这样说过。”
“说过,我记得。”斯蒂夫点点头





![(综系统同人)[综系统]筛子补完行动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3/2322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