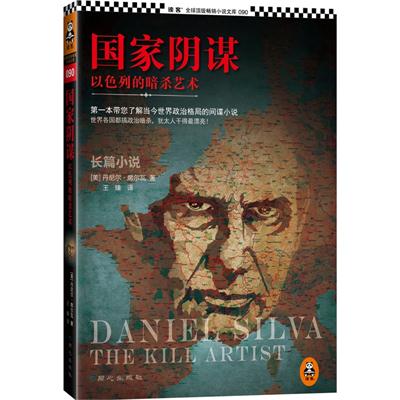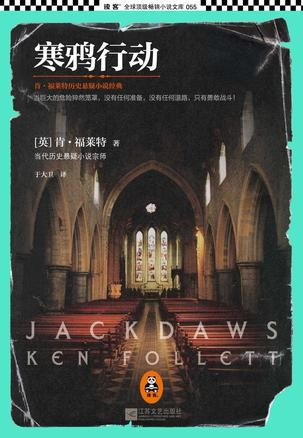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如果你扣动扳机两次,无论发生什么,只要你的目标是对的,都会有两颗子弹同时命中目标。如果没有打中也没关系,两颗子弹没打中跟一颗子弹没打中是一回事。如果你没打中又还来得及,你可以再瞄一次,把两颗子弹打出去。但两颗就够了,只打两颗。你每次扣动扳机时,扣两次。
“记住这一点,”戴夫说。“睡觉的时候也要记住,总是噗—噗。绝对不要他妈的噗—次就完了,这样不好,而是噗—噗,即使在你睡觉的时候也这样。”
阿弗纳完成基础训练多年后的一天,他在特拉维夫市的加伯汀斯基大街碰到了戴夫。“是你啊?”那个美国老人高兴地说。“你怎么样?还记得噗—噗吗?注意别忘了!”
阿弗纳从来没忘记过。
他不是一个天生的射手,但是凭着“野客”良好、谨慎的作风,他一遍一遍地练习,直到最终达到要求。他不是这个组里最好的——成为最好的还需要判断力和节奏感。而阿弗纳不具备这些——但他下决心凭借自己的毅力尽可能地学好。他做到了。在格斗实践中,他尝试拔枪的时候不要离目标太远——“你以为你在发射洲际导弹吗?也许。”戴夫会这样说——但他也努力克服自己觉得距离太远会打偏的担心。“当然,你用枪管顶着他就不会打偏,但是那样的话,敌人就会狠狠地揍你,这样你就失败了。”这就是戴夫关于那个错误要对阿弗纳说的话,除非他没有机会说。至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其他的课程也是一样,摄影课、通信课、爆破课——阿弗纳以前在部队里学过这些课程,不需要其他人那么多训练。突击队员必须了解一些爆破的基本知识,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不过阿弗纳不是装炸弹或拆炸弹的专家——也许装拆一个简单的还可以。在战场上,一个普通人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放置、打开炸弹的保险,启动爆炸装置。在这个层面上,事情就简单了。一切都是事先预备好的——雷管、发射机,以及可塑炸药。这样的炸药只需要一小撮就可以把一个保险箱的门炸开。但你不必那么小心。你可以把它扔在地上,用锤子锤它,甚至用它来捻熄香烟。它的性能十分稳定,你要学习的就是把它做成什么形状——可以做成任何你想要的形状,甚至还可以给它上色——然后把它放在起爆管里,把导线连上。红色线与红色线相连,蓝色线与蓝色线相接,很简单。
证件课程就更有趣了。这是阿弗纳最擅长的课程,也许是因为它与第六感觉有关。不是伪造假证件——因为这是专家的事,别指望一线特工会了解那么多——而是使用和侦查。这是一门微妙的科学,需要一个人具有推理能力。教官是一个名叫奥特加的阿根廷犹太人。正如他所说,与其说它是一门别的学问,还不如说它是心理学。你必须对身份证件有一些了解、对人有深入的了解才行。
奥特加认为,一线特工应该首先学会怎样识别假证件,然后再学习怎样搞到和使用假证件。在以色列,“穆萨德”这个组织的实际工作不是从事反间谍活动——另有一个名叫“辛贝特”的国内安全机构负责这个——但在以色列以外的国家,反间谍也是特工的工作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了解别人在使用假证件时所犯的错误可以避免他们重蹈覆辙。
比如,奥特加给他们每人发一个护照,让他们随便在哪一页做些改变,比如用刀片刮掉一个符号,写上另一个符号。“你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页码上这样做。”他对他们说。“你们把护照还给我的时候,不要告诉我是哪一页。”
他们这样做了,奥特加让他们把护照打开,放在他摊开的手掌里。他能立即说出他们窜改过的地方。护照在这些所谓的伪造者们绞尽脑汁地干了一个小时的那一页打开了。护照的装订之处总是会弯曲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我让护照打开的时候,”奥特加说,“我不看护照,我看你。”
任何一本护照,即使没有窜改过,都会在某一页打开。这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持护照的人的目光没有闪烁不定的话。闪烁不定的目光是你最希望看到的东西,特工是不可能当场崩溃甚至哭起来的。但闪烁的目光也可能没有任何意义,或者跟你关心的事情没有关系。也许那个家伙在走私香烟呢。这时你的第六感觉就要介入了。如果你没有第六感觉,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特工,无论你是查假证还是用假证都是这样。
就阿弗纳来说,这是他作为一个特工的优势所在。他才华横溢,特工所需要的那些本领他都有。确实,在诸如数学和科学这些令人惧怕的课程上的能力,有时候也是需要的。有些设备特别是那些通讯设备,复杂得难以置信,有扰频器,还有反扰频器。发射机发射一次就能发出一个小时的信息。阿弗纳觉得加密和解密的原理非常难学。一次性缓冲器对他来说总像个谜一样,还有计算机。他最缺乏的是记忆技巧,身体的协调能力也只是中等。他的驾驶技术也是技巧不足,勇气有余,就像他说英语和德语一样,敢说,但说得不好。他虽然能很快抓住一个事件的全局,但在细节上却没有耐心。
然而——关键就在这里——在“穆萨德”特工组织里,没有专业才能的人也有施展本领的机会。有许多无线电信号天才或化学奇才只能待在实验室里生产隐形墨水。他们也需要掌握全局的人。像阿弗纳这样的人,也许没有任何专长,却善于推理。
阿弗纳擅长根据事实推理。在他心里好像时常有一个声音在低声对他说:不要在乎那个,注意这个就行了。不管是证件还是人,他总能几乎是下意识地记住那些最小的标记。就拿他们练习时用的比利时护照来说,他虽然不能立即说出毛病出在哪里:签证好像是真的;揉搓的时候,颜色也没有粘在手指上——对着光看纸张也不是那么薄——但他头脑中有一个警钟,他必须在三十秒内作出决定,就像真的在机场一样,要么把乘客扣留下来,要么向他挥手告别。他又看看护照,当然——是看护照上的照片,夹照片的金属回形针完全生锈了。锈迹斑斑的回形针应该在证件上夹了两年了,而且好像一直是装在满是汗渍的口袋里的,但是反面却与之不符,锈迹很少。后来换上去的照片上没有什么锈迹:锈迹是无法放回到跟原来的照片一模一样的位置上的。
阿弗纳也擅长“扫描”艺术,即密切留意周围不寻常的事情。“扫描”艺术不是一门独立的课程,永远保持警惕被看作是对每个特工的要求。“扫描”,简单地说,就是用你的眼球频繁地扫视你周围的环境,就像雷达的信标一样。决不要让全部注意力在一件物体上停留几秒钟以上。为了使“扫描”成为一个绝对的、二十四小时都具备的习惯,教官们常常在出乎受训人员意料的时间和地点为他们设置一些意想不到的陷阱,他们下班后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散步的时候也不例外。教官们教他们如何把一切反射面——橱窗、车门——当作镜子,随时了解周围的一切,同时又让别人对他们的行为没有觉察。
“扫描”确实成了大多数特工一辈子的习惯。但阿弗纳很快注意到了另外一点:“扫描器”的身份也会暴露。比如,特工们很少笑。事实上,大多数特工面无表情,一方面要不停地用眼睛扫描,另一方面又要让面部的表情丰富多变是很难的。这是另一种知识,阿弗纳把它储存在下意识里,以备将来之需。
作为一名侦察员,不仅仅是事情会立刻影响你,还有信息也会影响你,这是特工培训中主要的一点。在阿弗纳待在蘑菇形的圆屋顶下的六个月中,这一点比其他什么都重要,一再强调。他们经常出去侦察。搭汽车去海法,在酒店的大堂里坐到下午四点,然后回来一点不漏地告诉教官他们看到了什么。不要剪辑,不要判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把你记得的东西全部说出来——每件事都要记得。
当然,要做到这点需要记性和耐心——这不是阿弗纳的强项——这项训练让他对人性有了深入的了解。通常,在第一个受训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会有另外一个组的一个受训人员坐在海法一家酒店的大堂里。如果他们的汇报大相径庭,教官就会对他们说:“听着,伙计,为什么不到隔壁给我把这个问题搞搞清楚。”
通常,答案很简单。一个受训人员在观察时感到无聊了,或者饿了,就会去找咖啡或者三明治。特工也是人——烟抽完了,要洗澡了——这个因素常常在另一个特工的分析中被省略掉,有些受训人员想像力非常丰富,喜欢夸大甚至虚构。这些训练不仅仅是训练或测试他们的观察力,而且还可以搞清楚他们的某些品性。他们会不会捏造,或者会不会添油加醋?他们能不能把观察和想象分开?碰上自相矛盾之处,他们是据实承认还是顽抗到底?
这对于另一个领域的培训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领域中,阿弗纳是最好的。这就是策划。设计一个模拟的军事行动,选人,把需要的辅助工具列出来。在一组学员中选谁担任什么任务——根据他们各自的强项、特长和个性——可能是成功的关键。
教官很快注意到,阿弗纳能根据这些同伴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性格,让他们扮演不同的角色。他能大大地超越这些表象。比如:假定一次虚构的任务是秘密进入设在罗马的阿拉伯人的大使馆,摧毁它的通讯室。阿弗纳就会要住在当地的罗马特工向他详细汇报在整整一个星期内大使馆每天二十四小时的日程安排。在行动前的三天时间里,他会指派最不活泼但最可靠的特工画一张周围街道的交通图。假定这个虚拟的大使馆里有一个套间,阿弗纳就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想租住这个套间的西德商人,从而搞到所有楼层的布局。他会用尽可能少的人完成每个阶段的任务。他决不亲自向自己的特工通报情况,而是让各个部门最聪明、最细心的人来做这件事。
最后,他会在这份方案上签上他的大名,笔迹粗大醒目。他为这份计划感到自豪,也知道为自己的计划感到自豪的重要性。有一次,教官来回看着那几份计划,举起那些潦草难读的字迹,讽刺地说:“瞧,这是一个大英雄的签名。”
在阿弗纳看来,教官说得没错,一个人的签名越不清楚,他对自己的计划越是缺乏自信。在实战中,阿弗纳总是要看送给他的方案上的签名。如果他能毫不费力地读出这些名字,这个人很可能就能活着回来。
这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在各个领域的训练当中,那些阿弗纳认为的信息背后的心理活动给他的印象最深。那些信息他也许不会记得太久,但他总是记得当时的心理活动。至于那些技术上的细节嘛,他可以问别人或者查阅资料。重要的是心理活动,它可以帮助他获得新的信息。
比如,阿弗纳永远不会忘记教官谈到证件时说的一番话——虽然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但他却一直记得。
从证件的性质来说,有各种各样的假证件。从特工也许会使用的永久居留证到一小时证件——比如,从机场厕所偷来的游客的护照——在紧急情况下,特工也许可以用它来过境。但是奥特加说,与证件的性质比起来,你对证件的信心更为重要。证件永远不会独自发挥作用,只有跟你联系在一起时才发挥作用。如果你不相信你的证件,或者不相信给你证件的人,你会把一个永久性的身份证件降级为一个一小时护照。反过来,即使你拿着偷来的驾驶证,只要你相信它,你也能走得很远。
在一线特工执行的每项任务中都有某些心理活动的成分。如果在巴黎或阿姆斯特丹设置监控点,一对年轻夫妇引起的注意要比,比如说,一个穿着雨衣、孤零零地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看报的人少。但是在西西里岛或者科西嘉岛,把任务交给一个孤身一人的男人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考虑。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安全屋最理想的主人是年纪稍大的夫妇。而在索尔邦大学,一对男女学生最不显眼。阿弗纳第一次跟踪开车的教官时,他以为教官会玩各种飞车技巧,完全没想到他跟踪的这个人在特拉维夫慢得像一个老太太,每次转弯的时候都要打信号灯。最后在黄灯的时候,教官甚至停了下来,就在信号灯变成红色的一瞬间,他倏地穿过了繁忙的路口。阿弗纳跟不上他了,要是跟下去的话,就要出交通事故了。这次经历虽然简单,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许多受训人员希望学到固定的规则,确切的程序。固定的规则虽然有,但对特工来说,一成不变地照搬书本是最致命的错误。它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活——这也是为什么阿弗纳觉得这个活儿那么适合他的原因。秘密就在于掌握规则但又不受规则的束缚,能够即兴发挥且总能应付突发事件的人将会脱颖而出。不像部队,说到底,它属于官僚机构。而这项工作,却是为那些不驯服的人量身定做的。至少阿弗纳是这么认为的。
六个月之后,训练移师野外。对有些人来说,进入这个阶段之前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考试。但实际上,每天的训练任务都是一次考试。通过这些考试,教官对这些未来特工们的表现进行评估。阿弗纳不知道在他们这组人中哪些人“考过了”或“没考过”。这方面的信息他们从来不告诉其他人。一个受训人员再也见不着了,也许就意味着他有了别的任务或者分流到某个特殊领域去了。但也可能意味着中途辍学了。关于这些,受训人员总是在私下议论,从来没有问过,也没得到过任何正式答复。
在移师野外训练之前,阿弗纳接到指令,让他参加几个特别情况介绍会,是关于工作程序和汇报程序的,还包含一些有趣的技术信息,但无甚令人惊异的东西。有一个通报会比较特别。阿弗纳不知道是应该把它看作一件没有价值的东西呢——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很滑稽——还是应该把它看作一个不祥的征兆。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它像





![(综系统同人)[综系统]筛子补完行动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3/2322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