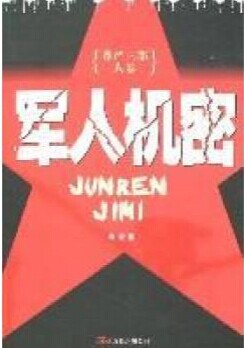军人机密-第4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们倒挺内行。”
“救命啊……”兵们还在使劲地扔丁丁,丁丁不得不大声呼救。周天品大吼:“行了!逮到还不撒手了。一个个,什么作风!”兵们悻悻地停下来。
周天品:“各连注意,今天晚上加餐,小庆贺一下。”
兵们欢呼而散。
精神病医院,到处是各种病态的人。
谢石榴的单人病房。盼盼坐在椅子上,直直地看着。谢石榴坐在床沿,弯着腰,闷头抽烟。
两个人像是相持了很久。谢石榴磕掉烟灰,重挖了一锅,又点上。他的手有些发抖。
盼盼开口:“舅舅,您的手为什么发抖?”
谢石榴:“……不知道他们,给我打了些什么鬼药……”
“他们顶多打些镇静剂。”
谢石榴低着头,翻了盼盼一眼,显得极其畏惧,马上又垂下眼皮。
盼盼:“您的背也驼了吗?”
谢石榴直起腰来。
“勇舅,您别害怕,我不想再问你们什么了。真话、假话,我都不想听了。这两天,再找不到金达莱,我就回去了。”
谢石榴的腰一下又弯了下去。他畏缩地点点头。
盼盼走到门口,回过身,怜悯地看着谢石榴,说道:“妈妈很担心您的脾气,在这里,您别跟人家硬碰硬……听说,他们有电棍……”谢石榴虚弱不堪,深弯着腰点了点头。门关上的声音响过片刻,谢石榴脚前的地上,砸出来两块“水印”!
山上。竹棚内,灰尘一片,零乱不堪。盼盼站在门口,看了看,转身下山。
一辆旧汽车的驾驶室里,金达莱蜷在座椅上睡着。她的头前,有一个装着些剩饭的小铁桶。
大碾子等终于穿上了参战人员穿的那种邻国军服。他们很正规地出操,十分出色的射击,时时弄得兵们目瞪口呆。没几天,大碾子等成了“教官”,指点着兵们:“天天读”时,司马童拿着“红宝书”口若悬河;晚会上,乔乔在跳“造反有理”的舞蹈,兵们学得如痴如醉:水泥案前,吴文宽虚心向丁丁求教乒乓技艺……
周天品与通讯员站在操场边上,看着大碾子等人为兵们表演“谢家拳”,满脸欣赏。
通讯员:“这哪是新兵呀,除了钟小鸥,这四个起码是排长以上水平。”
周天品:“天上掉下来四个宝贝蛋儿。”
通讯员:“当炮兵怪可惜的,他们纯粹是当步兵的料。”
周天品若有所思:“这种拳我好像在哪见过……”
“周天品,你好大胆子!”背后传来一声断喝,周天品回头一看,是与他年龄相仿的团政委。
“政委……”
团政委看着操场,故作严重地说:“你是招来一支专业武斗队啊!”
周天品与团政委走进掩蔽所,通讯员倒完水退出去,随手关好门。团政委看着门一关,马上放下架子,将卷好的烟笑眯眯地递给周天品:“老周,国内带来的,地道的河南黄金叶。”周天品大咧咧地接过来。团政委立即为其点上火。
周天品:“你是专门为他们来的?”
团政委:“红卫兵,你想留也留不住,国务院有专门批示。但这次我主要不是为这事。”
周天品:“什么事?”
团政委沉默地为自己也卷好一支烟后,冲着桌上的那个记者照片看了一眼:“为她的事。”
周天品“呼”地从床沿上站起来,喝道:“你们有完没完了!她又怎么着谁了?!”
团政委:“你小声点儿,我的老连长。五七年你老婆打成右派,不就是组织叫你离,你不离,还大叫大嚷地喊屈,才从副团长降下来的吗?当年我这个你手下的副指导员,如今团政委都干了三年了。吃一堑要长一智。”
周天品泄气地坐下来。
团政委:“其实也没什么新的问题,只是文化大革命嘛,历史问题被重新审查……有个情况你是知道的,出国参战部队的政审很严,过去是看你有个‘战斗英雄’的老本,可现在,老将、老帅都照样……上级也是为你好……有样东西你看一下,千万别发火。”
周天品接过团政委递过来的一封信和一张表——离婚申请书。而且那上面已有签字:夏晔星。周天品甩了烟,“霍”地立起:“你们找她啦?!”
团政委:“我求求你,千万别喊,千万别喊,不给我留面子,还要考虑这事的影响吧?”
周天品忍了又忍,咬牙道:“再降我一级吧。”
团政委:“这回不是降不降级的问题,如果你再不签字,就可能……安排你立即回国,做转业处理了。”
周天品一屁股坐下来。沉默良久,他把表郑重地还给团政委:“随便吧。”
夜,周天品靠在一门炮上,双目紧闭。他的眼前出现的是夏晔星签字时泪如雨下的情景……周天品紧闭的眼角冒出两粒硕大的泪珠,在月下闪着亮光。
第二日,防空炮战。
这次战斗异常惨烈,阵地频频遭到敌机导弹的袭击,火海一片。
“什么?百鸟舌导弹,专门对付我们雷达自控高炮的?妈的,我说的呢!”掩蔽所,周天品接着电话,“……是,是……保住那几个红卫兵……”
阵地上,战士们纷纷阵亡。大碾子等人均已负伤,但他们接替牺牲者,跃上炮位,英勇奋战。一声爆炸,钟小鸥倒在了血泊中。
“小鸥……小鸥……”丁丁摇着钟小鸥大声哭喊。周天品奔出来,抱住钟小鸥:“钟小鸥……”
大碾子在炮位上看了一眼,边流泪,边发狠地开炮:“我操你奶奶——”
中篇
20
战后,阵地一片肃杀。阵亡战士的遗体被摆成一排,钟小鸥也躺在其中,他微笑着,还是个乖男孩的样子。周天品、战士、大碾子等坐在一边,默默地守着。团政委领着一个穿中山服的干部走过来,看见眼前的情景,脱帽默哀了片刻。
团政委介绍:“这位是中国大使馆的同志。”
大碾子等看了那个干部一眼,毫无表情地坐着没动。周天品张了张嘴,也没动。干部对舒乔说:“请你们几个跟我来一下,听我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大碾子等人惊异地相互看了一眼,不得不站起身,跟着干部走向掩蔽所。
团政委对周天品道:“老周,你简单交待一下,先跟我去团里。恐怕你跟他们是一趟回国的车。”周天品不语,只是沉沉地点了点头。
不一会儿,大碾子等从掩蔽所垂着脑袋走出来。大碾子与司马童把钟小鸥放上担架,四人默默地在战士们组成的夹道中离开战场,跟着大使馆的人向山下走……
吴丁突然奔回来,抓住周天品的胳膊哭喊着:“营长,给小鸥报仇啊!”周天品痛苦难言。丁丁使劲晃着他:“你为什么不答应?为什么不答应?!”周痛苦万状。
战上们突然在通讯员的带领下高吼:“为钟小鸥报仇——”“为钟小鸥报仇——”
丁丁向战士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下山。
周天品突然向团政委伸出手,恶狠狠地:“给我!”团政委一时没明白过来:“什么?”
周天品:“你说是什么!”团政委反应过来,马上掏出那张表,递过去。周天品拔出笔,签好自己的名,扔还团政委:“你滚吧!”
路口,界碑。
一辆军用吉普驰近。大碾子等下车。吴丁捧着一只黑色的骨灰盒。大碾子等回头望了望界碑,然后向附近的山上走去。在一棵盛开红花的木棉树下挖了一个坑,他们将钟小鸥的骨灰掩埋了。
——一九六七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亲自指示:擅自出境参战的红卫兵必须全部遣送回国,包括牺牲的红卫兵遗体、遗骨均移回国内妥为安葬。
山顶,大碾子等人或坐或立地眺望着远方——尽管经历炮火、生死的他(她)们,已明显成熟了,但眼中却仍然是无限迷茫。
“我们还有路吗?”大碾子开口。
司马童:“不是我们。从此,你无权再代表我们,我司马童要走自己的路。”
乔乔看看大碾子与司马童,似哭似笑地说了一句:“一切都过去了……去它的吧!”丁丁自言自语:“长大了,长大了,我终于长大了。”
他们陆续下山,走的路线不同,间隔很大。
天高地阔。深秋,田园凋蔽。
乡间,曲曲弯弯的土路上走着一辆马车。车上除了一个戴着红袖章,抱着鞭竿的邋遢老汉,便是楚风屏和所有的孩子们:司马童、乔乔、丁丁、金达莱及大碾子。心事重重的一行人中,只有金达莱满目新奇地东张西望。马车走进一座空荡荡的小村,最后停在田大年家。
楚风屏叫着“田嫂”、“大年兄弟”,推开虚掩的院门。院里、屋里,均空无一人。
赶车老汉说道:“这阵子都在队里‘天天读’呢。”
楚风屏:“大年兄弟不是有病吗?”
“你们先歇着吧。”老汉不愿多搭话。他赶车走了几步,看见前面有辆吉普车,脸色一变,掉过车头,紧张地对楚风屏说:“这位楚,楚……不管谁,你们千万别说是我把你们从县里捎来的……”说完便赶着车匆匆走了。
楚风屏看了一眼,同大碾子等将被褥、脸盆等行李提进院子。他们打量着小院。乔乔看着那几间破败的房子,紧皱着眉头。
圈里的一头猪拱开门,走出来,挡在前面,看着这些陌生人。猪摇着尾巴,友好地向前走了几步。紧盯着它的金达莱,恐怖地叫了一声,躲到楚风屏身后。猪走到舒乔身边,在乔乔的裤腿上蹭痒。乔乔厌恶地一脚踢过去:“真恶心。”猪尖叫着跑开了。
楚风屏看在眼里,平静地说道:“孩子们,你们从此要适应这里的生活。要学会一天只吃两顿饭,没有鱼,没有肉,只有红薯和苞谷稀粥。要学会挨虱子咬,臭虫叮,没有蚊帐,没有水洗脚,也能睡觉。要学会在粪缸上上厕所,并且每月一次把粪便淘出来,送到地里去。你们要……”
丁丁打断楚:“妈妈,我们打过仗,什么苦都吃过了。”
楚风屏缓缓说:“那是不一样的。你们能当兵,却不一定能当农民……”她轻叹一声,说道,“先把这头猪赶回圈里去吧。”
大碾子等一拥而上,撵得猪满院子乱窜。好一阵大呼小叫、滚滚爬爬地追逐,才把猪按在地上。他们一人拽着猪的一条腿外加一条尾巴,活活把猪扔进圈去。楚风屏看着浑身是土的大碾子等,有些苦涩地笑笑。
村路上,走着一群散会的村民。田妻和小碾子一左一右搀着有病的大年。在踏上院门台阶时,为了腾出手,双手去架大年,小碾子把《毛主席语录》用嘴叼着。田妻责怪地从小碾子嘴里拽出语录本,嗔道:“碾子!”突然,院里传来一声:“哎!”
田妻等一愣,忙推开门——最先看见的是离门最近的大碾子,他正犯愣。
楚风屏奔上来,喊道:“田嫂,大年兄弟。”
田妻惊喜地说:“哟,楚大姐,不是说半个月后再来吗?”
楚风屏:“城里打得太厉害,就没等你们回信,先闯来了。”
田妻好像有什么为难的事,看了丈夫一眼。
大年咳嗽着:“来了好……来了好……”
田妻问道:“孩子们都来了?”
楚风屏:“两家五个,两男三女,全来了。”
田妻按下心事,兴奋地道:“好,好,好啊!”田妻的眼睛一直盯在她的亲生儿子——大碾子身上。大年也不由自主惊喜地盯着大碾子。
“大碾子长得这么壮!”楚风屏举高胳膊揉着小碾子的脑袋,“像门炮似的。”
“楚姨,”小碾子叫了一声,憨憨地笑着。大碾子也冲大年、田妻各鞠了一躬:“田叔叔,阿姨。”田妻听着十分别扭。
楚风屏解释:“军队里的孩子都这么叫。”
田妻:“哦,哦。”
楚风屏对其他孩子:“都愣着干什么?”
司马童、丁丁、金达莱、乔乔上前叫人:“叔叔好,阿姨好。”
楚风屏介绍:“这个叫司马童,这个叫吴丁,这个叫金达莱,这个叫舒乔。”田妻欲拉又未拉舒乔的手:“喔哟哟,喔哟哟,这么漂亮一个大姑娘,我这个草屋破院的,可委屈了你……”说着,田妻用袖口去擦乔乔脸上抓猪时留下的一撇泥。乔乔一边应付地笑,一边斜眼瞧着那显得黑糊糊的袖子和手,欲闪不闪,轻轻地蹙眉。
金达莱颇有妒意:“她是我们家的一块招牌,走到哪都讨人喜欢,就是爱睡懒觉。”
田妻笑着捧住金达莱的脸蛋:“田婶也喜欢你。田婶还知道你是个朝鲜姑娘,你是咱这个小村子八百年来接待的第一个外宾!”
人们笑起来。
晚饭,大年和大碾子等围着木桌。楚风屏与田妻端着冒尖的两瓦盆煮红薯,放在桌子中央。田妻不好意思地说:“楚大姐,真是的,这第一餐就……其实猪哇鸡的,都是现成的。”
楚风屏:“就这样,能吃饱就很好了。”
大碾子等面面相觑。
大年:“委屈你们了。”
大碾子等看着盆不动。
楚风屏:“吃啊。”
丁丁试探地问:“筷子呢?”
小碾子这时伸出手去,拿起一个,因为很烫,两手倒着,离开桌子,蹲到门槛上边吹边咬着吃。大碾子等人学着,纷纷伸手,边倒手,边剥皮。
夜,小村静谧,偶尔有一两声狗叫。
大年家。男孩在一间房。楚风屏与女孩在一间房,木床、草铺……各种方式弄成的卧处,横七竖八地睡着。
一团烛光在院内馒慢划过。那烛光移进男孩的屋里,在熟睡的大碾子头前停了下来。良久,煤油灯罩不断颤抖着。远远地传来几声大年的咳嗽,这烛光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大年夫妇的房内,大年:“你也不怕把孩子弄醒。”
田妻关好门,吹熄煤油灯,靠在门上,脸上有泪,她仰面朝天地说道:“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