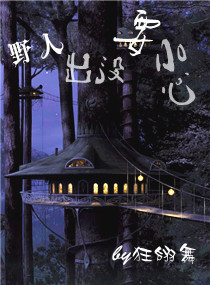野人部落-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又一边频递飞媚,一边做掩面害羞状。种种忸怩,种种做态,真个像真一般。终于“尕妹”就扭头跑开了,“阿哥”也撒腿追开了,一时间满滩里欢声笑语响成一片……
八(2)
这是一种无法言述的、不可理喻的风牛风马,就在这风牛风马中,男人们的那种欲火就真的得到了抒发和抚慰。天长日久,这便成了野驼滩旮旯城的一种习俗。每当夕阳西下,劳作归来,光棍汉们就端上茶碗,抱上酒罐,这里一群,那里一伙,边饮边唱,边唱边跳。直至太阳下山,明月升起,犹不能歇。往往还要点上一堆篝火,围成一圈,彻夜狂欢。那个场景啊,不身临其境是没法儿细说的!
在这无拘无束的、忘天忘地的苦中作乐时,那些真正的“尕妹”或是“阿姐”也被感动了。我前面说,那些女人们经了九死一生的磨难,也变得随遇而安了。其实不然,这只是一部分人的事,另有一部分,她们的心火却永不灭息。在平时的日子里,他们被那班权势者们关在笼子里,得着恩宠,似是享受贵族的清福,只好强颜欢笑。但内心里却是一肚子苦水。现在,听着那没完没了的花儿少年,心头的潮水就日益增强。一到黄昏,欢歌四起,她们就情不自禁地,探出洞口,趴到墙头,悄悄地听,偷偷地看。听着看着,有人就落泪了。终于在某个夜晚,就发生了一桩集体私奔事件。
那是一个明月高挂中天的夜晚,据我舅舅回忆说,那会儿时间已经不早,有许多人已经唱累了,喝醉了,准备收场回营了,只剩下他们骆驼团的一伙兄弟还在醉歌醉闹。忽然,从远远的一道沙陵后面,又传来了一曲歌声。那歌声十分清亮悦耳,分分明明是一个真女子的声音。人们就愣了,以为耳朵出了毛病。过了一阵,那歌声竟渐渐地由远而近,歌词也听得清了:半夜里起来月满天,石旮旯的门儿半掩。
阿哥是灵宝如意丹,尕妹是吃药的病汉……
人们就着慌了,多少个日子里喊:“尕妹”,现在尕妹真的到了眼前,反而使他们紧张得不知所措。一些醉鬼们也霎然酒醒,张目搜寻,只见一道沙陵上,一白衣女子碎步而来,月光照身,宛若狐仙,人们就登时闭住了气。这白衣女子是谁,原来她竟是马黑马的一个宠妾。她原是新疆剧社的一年轻演员,长得最是妩媚动人,当时才刚刚二十出头,被马黑马据为己有。羊副官、卜连长等人都不能染指。因她平日里总爱穿一件白绸衫子,人们都叫她“雪女子”,真实的姓名已无从知晓。她这会儿忽然撞入光棍汉中,竟使人不敢相信是真的。
过了好大一会,那雪女子见无人应答,又唱:青石头上的红嘴鸦,白鸽子一天天喂大。
我对你掏了心里话,你把我冷着为啥?
听了这声催问,有一个石匠出身的车班长终于站了出来——这个车班长的名字很古怪,叫“车怕万一”,人长得很是英俊干练,而且还能写会画,是队伍里仅次于羊副官的一个士兵秀才。平日里玩耍他常扮“尕妹”角色,这会儿就恢复了“阿哥”本相。他笑望着那个雪女子,斗胆回过去一段:白石头上的黄菊花,开了是光照天下。
我心里早已乱如麻,你到底是人呢嘛鬼嘛?
那女子得此应答,显然很高兴,止住步,又丢过来一段:胆大的猎手进山哩,怕什么狼呢虎呢?
只要你是个长球的,问什么人呢鬼呢?
“哗——”人群骚动了,这句质问真是非同凡响,谁也没想到,一个纤纤女儿家,竟会如此大胆!那车班长就来了劲儿,胸膛一拍,又回过去一段:黄河边下来的大轱辘车,拉的是炮弹和火药。
吃粮的人是叮当货,别当是废铜么烂铁。
“好。”人们欢叫起来。
那雪女子听此一段,似中了心怀。但不知怎的,顿了一顿,忽然又软了口气:二郎山戴帽是一道云,山根里拉了雾了。
我背上骂名你要上人,我羞者没走的路了……
这显然又在暗示着,她虽然嘴硬,心里却是怕的,意思是你别太当真。但车班长不肯罢休,又追过去一句:木匠拉锯造大车,大车从冰河上过了。
你把阿哥的心拉邪,难道就再不管了?
“妙!”众人又一声呼,都觉得这一声反问来得好,看她如何对答。
那雪女子却未被将住,只略略犹豫了一下,又回道:大车过河进城哩,进城了拉一车货哩。
我把阿哥的心拉邪,拉邪了你又咋呢?
这边,车班长更不示弱,立刻又顶过去:打一把七寸的刀子哩!
包一个鱼皮鞘哩。
长一个七尺的身子哩,闯一个天大的祸哩!……
“哗——”众弟兄拍起子来。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闯一个天大的祸”指什么意思,不言而明。这一下倒把雪女子给镇住了,一时语塞,半天没了声音。
八(3)
一团乌云飘过,遮住了半个月亮,人们隐约看见,她掩面哭了。
一阵沉默,万籁俱寂。我舅舅说:“来!喝酒!”于是,大家又叮叮当当碰起了酒碗。
喝着喝着,醒着的醉了,醉了的又醒了,七嘴八舌,杂歌乱吼:“望断天涯的路断了,雪山把沙漠隔了……这辈子把爹娘都不想了,还想个鸟的烦恼!”
种种慷慨悲歌,种种劝说诱导,犹如雨打梨花,风动林涛。终于,一轮明月冲破云团,那雪女子又如出水芙蓉般抬起了泪眼,明眸皓齿一闪动,心底的话儿就吐了出来:月亮上来车轱辘大,脑袋掉了是碗大。
刀子斧头奴不怕,单怕是阿哥们丢下……
“吼——”人们大悟了,感动了,她原来并不畏惧那强权的淫威,她怕的仅仅只是这个!于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承诺飞了过去:舍命保宋的杨令公,三国的英雄子龙。
阿哥是尕妹的金鞍子,半道上闪你是驴们!
歌声轰轰回荡四野,一方是剖心露肝的肺腑倾诉,一方是山盟海誓的铮铮誓言。越唱越欢,越唱越火。不知不觉,先前已经睡下的人,也重新爬起来跑到了滩上。那些一直战兢兢观望倾听的其他女人们,也终于受不住强烈的感染,步着雪女子的后尘,一个个溜出洞穴,加入了歌者的行列。汉子们愈加兴奋狂热,大碗的酒,破嗓的吼,阿哥在这边,尕妹在那边,中间隔一道沙陵,一唱一和,一对一笑,竟渐渐形成了一场纵情忘我的男女群体大汇唱……男的歌:民国手里造元宝,推翻了清朝的江山。
翻天覆地闹一番,不枉活了一世少年!
女的应:铜车铁马的英雄业,顺黄河慢慢儿淌下。
尕妹和阿哥是冤屈鬼,死了是一坑里葬下……
歌声动心彻骨,凌云摩天。先前的那种猫儿叫春没有了,恨天咒地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成了一种波澜壮阔的人生宣言……
终于,情的烈焰、性的烈焰、酒的烈焰、欲的烈焰,共同汇聚成了一股不可遏止的歌的海洋,汉子们敲碗顿足齐声作吼:十朵的牡丹九朵开,你这朵为啥不开?
青龙腾空者播雨哩,花骨朵把嘴儿努开!
女子们闻此召唤,涛声应呼:上山的老虎下山来,下山者喝一趟水来。
我这边招手你那边来,来了者××者耍来……
“哗——”如江河决堤,洪水滔天,阿哥们全都疯了、狂了,那车班长率先一跃而起,奔了过去;跟着,又有一伙年轻大胆的阿哥们潮涌而上,一眨眼工夫,数十个男男女女,拥做一团……
九
这一桩事件,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轰动了整个野驼滩旮旯城。马黑马震怒了,羊副官震怒了,卜连长震怒了,他们压根儿也没想到,他们的女人,他们的部下,竟会有如此大胆的越轨之举。马黑马气得几乎发疯,一阵哆嗦,一声令下,卜连长立刻率兵把那参与闹事的几十个男女抓了起来……接下便是军法审判。羊副官担任了法官的角色,他首先把那帮男女狠狠训斥一顿,接着便开始追查谁是闹事的头儿。这自然不难,很快,未等他人检举揭发,车班长自己就站了出来,胸膛一拍:“我是主犯!”那雪女子也毫无惧色,直言道:“这事不怪他人,是我带头寻上门的!”其他的男女也跟着咋呼:“天上把地下的雨下了,驴儿把马儿踏了,怀上个骡驹儿也是喜,管你牛的屁事?”羊副官气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好上报马黑马定夺。
尚未等马黑马做出决判,李老军又奏一本。李说:“这事儿复杂,不可造次。古人说:篱牢犬不入,倘若我们能把自己的女人管好,怎么能戴上这种绿帽子?况且兵是马儿将是鞭,如果我们治军有方,部下怎敢如此妄为?由此看来,咱们也有责任……”马黑马听了这话,居然真的冷静了下来,长思半晌说:“咳!认个羞吧!”随之做出一个判决:男人们因是酒后造罪,情有可原,暂时饶过,下不为例。女人们则是偶然失足,上了贼当,权且容忍,以观后效。至于为首的车班长和雪女子二人,则不能随便放过,将车班长以“强奸民女,带头破坏军纪”为名,狠打了二十军棍。雪女子又因“首倡淫乱,败坏贞节”为名,被贬为“民妇”,赶出了司令部“王宫”……
这个处理应该说是宽宏大量的,无可多言的,男男女女皆大欢喜。
事情到此,似乎已经风平浪静。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事情还出在那雪女子身上。她自被赶出“王宫”之后,表面上是受了惩罚,实际上却是因祸得福,回归了自由。她根本不在乎马黑马的所谓“失宠”,恰恰要的就是这种无拘无束。她在那密密丛丛的沙宫石窟中,独选一个僻静的石旮旯住了下来,由众“阿哥”帮忙,用泥巴土坯修了一道院墙,用沙柴红柳扎了一道篱笆门槛,过起了独门独户的日子。车班长等一帮弟兄,自然成了她的贴心好友,隔三差五,欢聚一起,或高歌山头,或醉舞沙滩,成了旮旯城一大新鲜景观。事情如果就此下去,也不失为苍天悯人的一个美好。但事情的发展变化往往出人意料,时间稍长,毛病就出来了,她由因祸得福而反过来因福得祸了。
我们知道,野驼滩的兵们是由骑一旅、凉州团、骆驼团三支力量汇合的,再加上独眼龙那几个,就是三支半,来源很复杂,积怨也深。虽然在盐巴风波后,马黑马已郑重宣布,三家弟兄一律平等,再不分什么嫡系杂牌,但事实上,派系斗争并没消除。在平常的日子,没什么特别的利害冲突,也就你好我好都过去了。一旦遇着特殊的利害,矛盾就暴露了。在前个阶段的男女事情中,主要是官兵之间的矛盾,士兵们还是同病相怜的;现在突见一个天仙女子从天而降,落到了众人群中,一些人的眼睛就红了。凉州团的人说,雪女子是由大家的粮草换来的,怎么能由你们骆驼团独享?骑一旅的人便说,你们这些俘虏娃子,靠我们的仁慈活下命来,不思报恩,反而还想龙口夺食,岂有此理!于是,冲突就发生了。我舅舅他们——主要是车班长等一些年轻士兵,当然不肯屈服退让,于是就经常发生吵嘴打架的事情。雪女子被夹在中间,自然成了矛盾的焦点,真是出了虎口,又入了狼窝……
她本来也想委曲求全,尽可能牺牲自己,抚慰众人。但毕竟她又不能人尽可夫。她虽然自由放浪,总还是有选择的,群歌共舞可以,同枕共眠就难能。这就必要导致某些人的黄河之心不死。
这情形自然也不会不被马黑马知道。那独眼龙是个天生的好事之徒,每逢发生这种事情,就会幸灾乐祸地跑去,向上层们绘声绘色地加以描述,说那些光棍汉们为了一个贱妇,如何地争风吃醋,如何地打得头破血流……马黑马每当听到这些,就嘿嘿一笑说:“好啊,让那个小婊子作乐去吧,我不嫉妒!”
上面是这样,下面就更加放肆。渐渐地,冲突就升了级,由一般的打架斗殴终于发展成了群体械斗。不但骆驼团跟骑一旅斗,骑一旅也跟凉州团斗,而且斗着斗着,打斗的双方或者三方还会突然间罢兵息怒,围坐一起喝起酒来。喝着喝着又会因一言不合而摔掉酒碗,再次打斗起来。渐渐地野驼滩打斗成风,成了继群体自慰、花儿对歌之后的第三种风俗习惯。所幸的是,他们的打斗仅限于拳脚棍棒,尚未动刀动枪。李老军有一次对羊副官说,要设法制止,不然的话,要出大乱子。羊副官却笑一声说,你不让他们打斗,他们那过剩的精力往哪里发泄?李老军又说,不管咋样,总不能闹出命案。羊副官又说,你别操心,物极必反,马旅长心中有数!果然,李老军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天,车班长和我舅舅他们,奉命到水山里去疏通一道淤塞的坎儿井,中午未能回营吃饭,凉州团的一伙人便趁机又闯进了雪女子的洞中。她说夜里来,那伙人非要白日里来,实在纠缠不过,就冲出人群,朝秦太太的洞中跑去躲避。这秦太太是谁?正是前面说过的那个带有一男一女两个娃儿、女娃儿为了弟弟而饿死了自己的那家母亲。据说她是原骆驼团一个团副的太太,当时在军中妇女中年龄最大,已四十多岁,加之木讷厚道,姿色平平,便和少数几个女人被马黑马等弃之于“民间”,未得“恩幸”。平日里只有李老军等几个老兵和她相与往来,喝喝茶、抽抽烟、拉拉家常,很少有年轻士兵找她的麻烦。偶尔有几个无赖汉子闯到她这里,她也要么是好言相劝,要么是拉她那个娃儿死守身边,使得那些人终无计可施,嘻嘻哈哈一场也就走了。这情况人所皆知,雪女子一遇尴尬之境,就跑来向她寻求庇护。可今天那伙人偏是不依不饶,雪女子跑到秦太太院子后,那伙人也追到了秦太太院子。而且这伙人还未站稳脚跟,又有骑一旅的一伙人也尾追而至。不一会工夫,秦太太的院里院外,便扎满了吵吵嚷嚷的兵们……
平心而论,这些兵们并不真是要对一个女人干什么,他们只是借一个女人为引子,玩一种男人间的恶作剧,如果真的要对一个女人施之以暴,雪女子有十条腿也是跑不了的。这底细也是心照不宣。当时听着有两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