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药-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安德鲁是他父母短暂婚姻中唯一的孩子。另一个安德鲁巴不得西莉亚能见到的亲属,已在两年前去世了。那是他没结过婚的姑姑,安德鲁童年时代大多和她住在一起。这姑姑并不富裕,可是在安德鲁双亲完全不资助的情况下,一点一滴地攒钱供安德鲁上完了大学。她死后,在律师事务所,安德鲁看到了她原有财产的剩余部分——可怜巴巴的,只值几百美元。只是在这时,安德鲁才意识到,他姑姑为他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
事实上,婚礼那天,西莉亚对安德鲁的母亲处理得很轻松自如。不需要任何解释她就胸中有数了。她对安德鲁的母亲真诚相待,甚至很热情,但也不是假惺惺地过分亲热。后来,安德鲁为他母亲不得体的言行表示遗憾时,西莉亚回答说,“亲爱的,是我们两人结婚,又不是我们两家结婚。”接着她又说,“现在我就是你的家,你以前得到的爱太少,你将从我这里得到多得多的爱。”
今天在这海滩上,安德鲁已体会到西莉亚的话兑了现。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准备,”西莉亚继续着他俩刚才的谈话,“在怀头一胎的大部分时间里仍旧工作,然后在家待一年,以全部时间来当母亲。
随后再去工作,直到怀第二个孩子,再照此处理。”
“成,我同意,”他说。“在被你爱和使你怀孕期间,我计划少少地行医。”
“你得多多地行医,你将仍是一个关心病人的好大夫。”
“但愿如此。”安德鲁幸福地叹了一口气,几分钟后就睡着了。
随后几天,他们互相了解对方,在他们婚前可一直就没时间这样做。
他们的早餐每天有人送到他们的小平房来;送的人叫雷蒙娜,是个和颜悦色、贤妻良母型的黑人妇女。西莉亚在一天吃早餐时说,“我喜欢这里。
这小岛,这里的人,这种静谧。你选中了这个地方度蜜月我真高兴,安德鲁,我永远不会忘记这里的一切。”
“我也高兴,”他说。
安德鲁最初建议到夏威夷去度蜜月。可是他觉察出西莉亚不太愿意,马上就提出这原先是第二位的选择。
现在西莉亚才说,“当时我没讲出来,如果去夏威夷的话,会使我难过的。”
他问她为什么。又一幅过去的画面呈现了出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西莉亚和她母亲住在费城;在美国海军中当士官的父亲——威利斯·德·格雷——正在夏威夷,他是珍珠港内停泊的美国战舰“亚利桑那号”上的军士长。日本人突然袭击的那一天,“亚利桑那号”被炸沉。船上一千零二名水手失踪。大多数是困死在舱内的;他们的尸体根本就没有找到,其中之一是威利斯·德·格雷。
在回答安德鲁的问题时,西莉亚说,“是的,我记得他。当然,他那时经常出海。但只要他回来休假,家里就总是很热闹,很开心。知道他即将回家时,我们总是很激动。连我的小妹妹珍妮特都安静不下来。尽管她对他的印象不如我深。”
安德鲁问道,“他是怎样一个人?”
西莉亚在回答前想了一会儿。“他个子很大,说话声音很响亮,他使人笑口常开,而且很喜欢小孩。他还是个强者——不单指身体,尽管他确实身体强壮,主要指精神上他很坚强。我母亲就不行,你可能看到了。她完全依赖他。甚至在他离家时,他也写信告诉她该怎么做。”
“现在她就依赖你罗?”
“看来结果是这样。事实上,从我父亲一死就这样了。”西莉亚微笑道。
“当然,我早熟得惹人厌,很可能现在还这样。”
“有一点儿,”安德鲁说,“但我认定能忍受下去。”
后来他温柔地说,“你不愿去夏威夷度蜜月,我现在理解了。你到过那里吗?你去过珍珠港吗?”
西莉亚摇摇头。“我母亲从来不想去,而我尽管弄不清什么原因,至今还没打算去。”她停了一会儿继续说,“我听说可以到‘亚利桑那号’下沉的地方去,可以看得见海底的那条船,但就是没办法把它打捞上来。你会觉得我这念头奇怪,安德鲁,但总有一天我会乐于到我父亲牺牲的地方去,但不是一个人去。我想带上儿女去。”
两人有一会儿没说话,后来安德鲁说,“我认为这念头一点儿也不奇怪。
我现在就向你保证:当我们有了儿女,当他们懂事的时候,那时我会安排这事的。”
另一天,在一只破旧不堪的渗水小划艇上,安德鲁一边不熟练地用力划桨,一边同西莉亚谈她的工作。
“我从前总认为,”安德鲁评论说,“医药公司的新药推销员都是——嗯,都是男人。”
“不要划得离岸太远,我有预感,这破玩意儿快沉了。”西莉亚说,“你说得对——大多是男人,但也有少数女人;有些过去是军队的护士。不过在费尔丁·罗思公司,我是第一个,迄今为止还是唯一的女新药推销员。”
“这可了不起。你怎么做到的?”
“兜了个圈子。”
西莉亚回忆说,一九五二年她从宾州大学毕业,得化学学士学位。她是靠奖学金以及夜晚和周末在药房打工上完大学的。
“在药房干的时候,一只手根据医生处方给顾客拿药,另一只手给顾客拿卷发器、除臭剂等等,我学会了许多后来证明对我有用的东西。对了,有时我也私下卖一些物品。”
她作了点说明。
男人,多半是些年轻人,有时来到药房心神不宁地走来走去,总想引那男营业员的注意。这些迹象逃不过西莉亚的眼睛。她就问,“你要买什么?”
回答往往是,“他什么时候有空?”
“如果你需要避孕套,”西莉亚和颜悦色地说,“我们有不少货供你挑选。”于是她就从柜台里拿出各种商标的盒子堆在柜台上。那些男人羞红了脸,买后赶紧走了。
偶尔也有轻狂之徒问西莉亚,能不能帮他试一下这产品。对这种问题她备着回答。“好吧。你说什么时候都行。我想现在我的梅毒已经没事了。”
尽管有的人可能意识到这是玩笑话,却显然没有人想冒这个险,因为凡是提过这种轻薄问题的人,她再也没见过他们露面了。
安德鲁大笑,桨也不划了,随小艇去漂流。
西莉亚又说,凭着学士学位,她向费尔丁·罗思制药公司申请做一个助理药剂师。被录用后,她在制药实验室工作了两年。
“我在那里也学到一些东西——主要是,除非你有志于献身科学,实验室的工作单调、重复,令人厌烦。销售和如何做买卖当时使我感兴趣。我现在仍对这两样感兴趣。”她加了一句,“而且做买卖的部门是可以做出重大决策的地方。”
可是想从实验室工作转到销售部门去一事,做起来却很困难。起初她按常规打报告要求,被回绝了。他们说,公司的政策是,销售部门只雇妇女当秘书。”
她不愿接受上级的这一决定,想好了一套办法。
“我认识到,如果公司改变政策,那么提议改变的人该是萨姆·霍索恩。在我们的婚礼上你见到过他。”
“就是你的上级,地区销售部的头儿,”安德鲁说。“那个批准我们生两个孩子的人。”
“对,他点头了,我将来才能干下去。我当时可决定了,要影响霍索恩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他妻子。这要冒风险。这一着差点儿行不通。”
西莉亚发现,莉莲·霍索恩太太在一些妇女团体中很活跃,因此,看来她可能同情一个有事业心的妇女。于是,一个白天,当萨姆在公司上班的时候,西莉亚去他家里找他妻子。
“我从来没见过她,”西莉亚对安德鲁说。“我也没同她预约。我只是去按门铃并闯了进去。”
霍索恩太太的接待很不友好。她三十刚出头,比西莉亚大七岁,是那种不说废话、性格坚强的人。她听西莉亚说明来意时,不耐烦地把乌黑的长发往后面拢去。末了,莉莲·霍索恩说,“真可笑,我从不过问丈夫的工作。
而且,他要是知道你来过这里,他会大发雷霆的。”
“我知道,”西莉亚说。“这甚至可能使我失去工作。”
“你事先就该考虑到这点。”
“我考虑过的,霍索恩太太。可是我想冒冒险,因为你思想很先进,你相信对妇女应该一视同仁,相信妇女不应该由于性别不同就受到不公正的歧视。”
有那么一会儿,莉莲·霍索恩看来要发作了。她厉声对西莉亚说,“你胆子可真大!”
“不错,”西莉亚说。“这就说明,我将来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女推销员。”
对方盯着她看,突然放声大笑。“天哪!”她说。“我确实相信你应该如此。”
隔了一会儿:“我刚才正要去煮咖啡,德·格雷小姐。到厨房来,咱们聊一聊。”
这是她们友谊的开始,这友谊将要延续许多年。
“甚至在那以后,”西莉亚对安德鲁说,“对萨姆还得做些说服工作。
他总算接见我了。我想他对所看到的比较满意,而且,莉莲不断地对他施加影响。这时他必须征得他上级的同意。可到底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她低头看着,小艇里的水这时已淹没了他们的踝关节。“安德鲁,我说对了!这玩意儿在往下沉!”
他们大笑着跳到船外,拖着小艇游到岸边。
当晚他们一起用餐时,西莉亚对安德鲁说,“我在销售部门当上新药推销员以后,我意识到,我不仅需要干得和男推销员一样好,而且要干得比他们更好。”
“我记得一次最近的经历,”她丈夫说,“你不止干得比男推销员更好,比我这当医生的还好。”
她粲然一笑,摘下眼镜,隔着桌子抚摸丈夫的手。“我在那儿交了好运,还不单是罗特洛霉素救活了病人。”
“你老是摘下眼镜,”安德鲁评论说,“为什么?”
“我近视,离不开眼镜;可我又知道摘下眼镜自己漂亮些。就是这道理。”
“你戴不戴眼镜都好看,”他说。“要是你觉得眼镜碍事,不妨考虑用无形眼镜。好多人都开始用了。”
“我们回去后我就去了解无形眼镜的情况,”西莉亚说。“我这老样子还有什么不行的地方?还有什么要改的吗?”
“现在你的一切我都喜欢。”
这儿离他们住的小平房一英里,他们来时手牵着手,走着草草铺就的弯曲小路,几乎一路上看不到行人。晚上天气暖和,只听得见浪打着礁石和小虫唧唧的声音。此刻,在一个陈设简陋、叫做“旅客之家”的小饭馆,他们正在吃当地的标准伙食:煎红、青豌豆和米饭。
尽管“旅客之家”不够资格上《米什林导游手册》,但对于饿着肚子的人来说,店主提供的食物却是美味佳肴,那是把刚捕到的鱼放在一只老古董的长柄平底锅中,用柴火煎熟。店主是个高大而干瘦的巴哈马人,名叫克里欧法斯·莫斯。他把安德鲁和西莉亚安排在一张俯眺大海的桌边,桌上有一根蜡烛插在啤酒瓶口上,照着隔桌相对的夫妻俩。眼前就是四散的朵朵云彩和一轮明月。“在新泽西,”西莉亚提醒安德鲁说,“可能已到凉快和多雨的天气了。”
“我们很快就要去那里。你还是多谈谈你自己和卖药的事吧。”
西莉亚说,她当上推销员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去内布拉斯加州。在她以前,费尔丁·罗思公司没派推销员去过。
“这对我颇有好处。我非常清楚我的处境,因为一切都需从零开始。没有机构,没有资料,也没有人指点我该去找谁,到哪里去找。”
“你的朋友萨姆是否有意这样做,想考验考验你?”
“也可能。我从来没有问过他。”
西莉亚什么也不问,就着手干了起来。在奥马哈,她找了一套小小的公寓作为据点,然后开着汽车在这州里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跑。每到一地,她就将电话簿黄纸部分中的“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栏撕下,用打字机登记好了入档,然后就开始走访。她发现,她的辖区内有一千五百名大夫;后来她决定从中挑出二百名来,她认为这些大夫是开处方最多的人。
“你离家这么远,”安德鲁说,“感到孤单吗?”
“没时间想家,我太忙了。”
她很早就发现,想见到一个医生有多么难。“有时我得在候诊室等上几个钟头,而当我终于进去后,医生也许至多只给我五分钟时间。最后,在北普拉特市,我被一个医生撵了出来。但他也帮了我一个大忙。”
“怎么回事?”
西莉亚尝了一下煎红,声称,“油太厚!我不该吃它,但很好吃,不吃又怪可惜的。”她放下叉子,靠在椅背上回忆说:
“他和你一样是个内科医生,安德鲁。我看有四十岁左右,可能那天过得很不顺心。反正我刚开始谈到想推销药品时,他就打断了我的话。‘年轻的女士,’他说,‘你想和我谈你要卖的药,那么我也要和你讲点事情。我在医科大学读了四年书,当了五年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我行医也已经十年了。尽管我并不懂得所有的东西,比你懂的东西还是多得多,这一点总不奇怪吧!刚才你想凭你那点浅薄的知识讲给我听的东西,在任何一本医药杂志上的广告里,不用二十秒钟我就可以看完。因此,你走开!’”
安德鲁做了个鬼脸。“好狠呀!”
“不过对我有好处,”西莉亚说,“因为他说得对。尽管当我离去时,觉得自己就像是臭狗屎似的。”
“你那费尔丁·罗思医药公司没给你受过什么训练?”
“一点点儿。时间又短又很肤浅,学的大多是一套找销路的生意经。我的化学知识小有帮助,但作用不大。我就是不够资格去和那些医术高超、临床经验丰富的大夫打交道。”
“既然你提到这一点,”安德鲁说,“这就是有些医生不愿见新药推销员的一个原因。除了要听他们老一套自卖自夸的生意经以外,有时还得到危险的错误信息。有些新药推销员为了使你开处方时用他们的产品,会信口开河,不惜让你得到错误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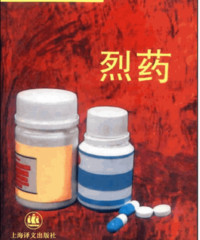
![烈药 作者:[加拿大]阿瑟·黑利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