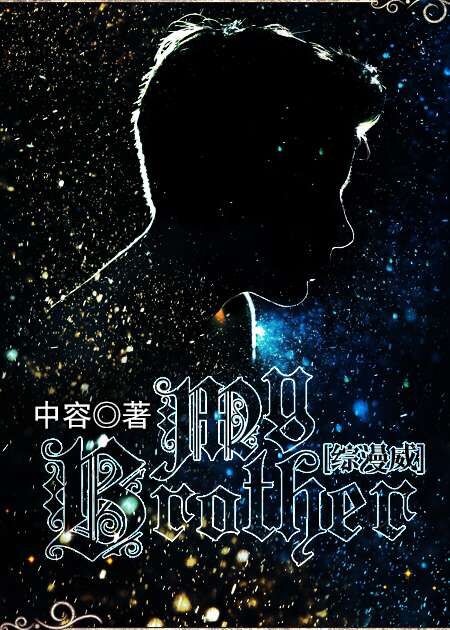the rainbow-虹(中文版)-第4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厄休拉忽然感到一阵透心凉,他打算把自己卖掉吗?
“赫伯恩上校结过婚没有?”
“结过婚了———他有两个女儿。”
但是她的骄傲情绪不允许她去担心赫伯恩上校的女儿会不会想到要嫁给他。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格德伦走了进来。这时斯克里本斯基依然懒懒地在晃动着他的摇椅。
“你那样子瞧着可真懒。”格德伦说。
“我就是很懒。”他回答说。
“你看着真像是软弱无力的。”她说。
“我就是软弱无力。”他回答说。
“你别摇了不行吗?”格德伦问道。
“不行———这是perpetuum mobile。(拉丁文,永动器)”
“瞧你那样子,简直像全身没有一根骨头似的。”
“那正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感觉。”
“我对你这种趣味可一点儿也不欣赏。”
“那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幸了。”
他仍然摇着他的摇椅。
格德伦在他背后坐下来,当他往后摇的时候,她用两个指头捏住他的一绺头发,所以等他再往前摇去的时候,她使劲拽住他。但他完全若无其事。现在屋里只有摇椅压在地板上的声音。格德伦一声不响,像只螃蟹似的,每等他摇过来一次就抓住他的一绺头发。厄休拉红着脸很有些不安地坐在那里。她看到他皱起眉头,越来越有些恼火了。
最后他像一根脱扣的弹簧,突然跳起来,站在壁炉前面。
“真见鬼,我为什么不能摇一摇?”他凶恶地极不耐烦地问道。
他这样像一根弹簧似的从懒散状态中忽然跳起来,使厄休拉觉得他很可爱。他生气地站在壁炉边的地毯上,眼里露出愤怒的光芒。
格德伦仍和她平常一样深刻而柔和地大笑着。
“男人从不坐在摇椅里摇晃的。”她说。
“女孩子从不揪男人的头发的。”他说。
格德伦又大笑了。
厄休拉感到很有趣地坐在那里,可是她在等待着。他知道厄休拉在等待着他。这使得他的血液沸腾起来。他一定得到她身边去,听从她的召唤。
有一次,他驾着轻便马车带她到德比去。他属于那种冒冒失失的工兵,他们在一家小旅店吃了午饭,然后又去逛商场,他们对任何东西都看得非常高兴。他在一个书摊上给她买了一本《呼啸山庄》。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集市,她说:
“从前我父亲常带我去坐那摇船。”
“你喜欢吗?”他问道。
“噢,那太有意思了。”她说。
“你愿意现在再去试试吗?”
“太愿意了,”她说,尽管她还有些害怕。可是,能够去干一件不同寻常的令人激动的事,总是对她有很大诱惑力的。
他马上到售票处去付了钱,然后扶着她上去。他现在除了注意他眼前所干的事情之外,似乎把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全都忘了。对在场的其他人,在他看来全都不必在意。她本来想先不上去,可是她觉得现在离开他反而更难为情,还不如大胆上摇船上去,让大家去看好了。他的眼睛充满了笑意,瘦长的身子站在她面前,开始让摇船摆动起来。她并不害怕,她只感到非常激动。他的脸开始慢慢发红,眼睛里闪动着激动的光芒。她抬头看着他,她的脸好像在阳光下开放的一朵花,是那么地光彩夺目,那么动人。他们就这样在那宁静的空气中飘荡着,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向天空,然后又以可怕的速度降落下来。她感到非常高兴。这种运动似乎在他们的血液中扇起了火焰,他们大笑着,感到仿佛全身都着了火。
玩过摇船之后,他们又去玩旋转木马,以便让自己慢慢冷静下来。他扭着身子对着她骑在跳动着的木马上,看上去老是那么自由自在,玩得十分高兴的样子。对旧的传统表示反感的一股热情更使他显得悠然自得。当他们坐在急速旋转的木马上,耳边听着留声机放出的音乐的时候,她始终也没有忘记过四周的人群。他和她似乎永无休止地骑着马在群众的面前跑过,永远轻快、骄傲、英武地骑着马在群众扬起的面孔前跑过,他们是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活动,把广大的群众踩在自己的脚下。
后来,他们必须离开旋转木马了。她感到很不痛快,感到自己仿佛由一个巨人忽然缩小得和普通人一样,并不得不自己也混在普通群众之中了。
他们离开市集,回到他们自己的轻便马车旁边去。在走过一个大教堂的时候,厄休拉一定要进去看看,可是整个教堂里到处是脚手架,烂砖碎瓦堆得到处都是,从墙上脱落下来的灰皮,踩在脚下扑哧发响,工人们粗俗的叫喊声和锤子的敲击声在满屋里震响。
在她不顾一切,在集市上,在群众的面孔前骑着木马奔驰了一阵以后,过去的许多她无法控制的向往现在又回到了她的心头,一时间,她似乎带着这些向往忽然进入了一种无比阴森的宁静的境界。在一阵骄傲情绪之后,她需要安抚和安慰,因为骄傲和轻蔑似乎比任何东西都更能刺伤她的心。
她发现这无比古老的阴森中充满了从墙上剥落下来的灰皮,那些灰皮扬起阵阵尘土,使这里充满了陈年石灰的气味。到处是脚手架,到处是成堆的垃圾,连圣坛上也堆满了尘土。
“咱们坐下来歇会儿吧。”她说。
他们不让任何人注意到,偷偷坐在最后一排椅子上,坐在一片阴暗之中,她观看着砌砖工和抹灰工干他们的肮脏、忙乱的工作。穿着长靴的工人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用一种粗鄙的声腔叫喊着:
“嗨,伙计,那些抹墙脚的模子拿来了吗?”
从教堂的屋顶上传来哑着嗓子的回答声,那屋子里的回声使人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斯克里本斯基紧挨着她坐着。一切似乎都是无比的美妙,尽管她也许觉得有些可怕,整个世界仿佛已经成了一堆废墟,而她和他却安然无恙、无法无天地在这废墟上胡乱爬行。他紧挨着她坐着,把身体贴在她身上,她也明确感到了他对她所产生的影响。可是她十分高兴,感觉到他挤压在她身上使她十分激动,仿佛他的存在对她就是一种动力,敦促她采取某种行动。
在他们赶着马车回家的时候,他紧挨着她坐着。车子每一晃动,他都有意显得十分放肆地贴在她身上,一直等到车子再次晃动的时候,再坐直身子。一句话没说,在她的披肩的掩盖之下把她的手拿过来,他开始用一只手解开她手套上的扣子,替她把手套脱下,仔细地脱光了她的手,而他却仍然全神贯注地驾着车,仰起脸看着前面的大路。在他替她脱手套的时候,由于他的手和她的手非常轻巧地来回接触,一种充满性感的喜悦几乎让那小姑娘如醉如痴了。他的手是那么美妙,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在那黑暗的地下世界十分熟练地拉开手套,触摸着她的手,脱下手套,先让她的手心,接着让她的手指全裸露出来。然后,他用手紧握着她的手,两只手是那么贴近,仿佛他的手和她的手已合而为一了。这时,他眼望着大路和马的耳朵,全神贯注地赶着车在村子里走过。她一直坐在他身边,狂喜不已,脸上焕发着光彩,一种新的光线使她完全盲目了。他们俩谁都不说话。从外表看去他们俩是完全分开的,可是通过他们紧拉着的手,他和她已经完全血肉相连了。
接着,他假装出好像毫不在意的样子,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对她说:
“刚才坐在教堂里让我想起了英格拉姆。”
“谁是英格拉姆?”她问道。
她也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可是她知道他现在要开始谈一些不该谈的话了。
“他是和我一起到查塔姆去的一个军官———是个副官———只比我大一岁。”
“那教堂怎么会让你想起他呢?”
“噢,他在罗彻斯特认识了一个姑娘,他们常常坐在一家大教堂的角落里谈情说爱。”
“那可太好了!”她不假思索地说。
他们彼此误会了对方的意思。
“但这也有一个缺点。教堂里的执事为这事吵开了。”
“多么混账,他们为什么不能坐在教堂里呢?”
“我想他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对神不敬的举动———除了你和英格拉姆以及那个姑娘。”
“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对神不敬,我认为在教堂里谈恋爱是完全正当的。”
她简直是挑战似的冲口而出,完全不去考虑她的灵魂了。
他没有说话。
“她长得很漂亮吗?”
“你说谁?埃米莉?是的,她长得相当漂亮,她是个做女帽的工人,她不愿意让人看到她和英格拉姆一块儿上街。这真是有点儿太惨了,因为那个教堂执事一直盯着他们,后来打听出他们的姓名,就当回事吵吵开了。后来简直弄得满城风雨。”
“她后来怎么办呢?”
“她到伦敦去进了一家很大的店铺,英格拉姆仍然常到伦敦去看她。”
“他爱她吗?”
“他和她在一起,现在已经有一年半了。”
“她是个什么样的姑娘?”
“埃米莉个子很小,简直像一朵盛开的紫罗兰,长着一对漂亮的眉毛。”
厄休拉思索了一会儿,这是否是外部世界的一段真正的浪漫故事。
“所有的男人都有情人吗?”她问道,对自己的这种鲁莽态度,自己也感到吃惊了。可是她的手和他的手仍然紧握在一起,他的脸也仍然丝毫没有改变,一直安详地望着前面。
“他们常常提到这个或者那个美得不得了的女人,大家喝得醉醺醺的谈论着她。他们大多数人只要一有空就匆匆跑到伦敦去。”
“去干什么?”
“去找那些美得不得了的女人呀。”
“什么样的女人?”
“各种各样的,一般说来,她的名字老是变来变去。有一个家伙简直是完全疯了,他随时都预备好一个手提箱,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提着那箱子跑到火车站去,到了车上再换衣服,不管车厢里坐着什么人,他都可以刷地一下脱下衣服,当着人的面至少把上半身的衣服全部换掉。”
厄休拉抖动了一下,感到有些不解。
“他为什么要那么匆忙呢?”
她说话时已感到喉咙有些发梗,说话不利索了。
“我想是他脑子里一直想着那个女人吧。”
她感到有点吃惊,有点意想不到。可是这个充满情欲的破除常规的世界使她感到十分着迷。她感到这似乎是表现了一种光辉的鲁莽。她现在也开始了对生命的探索。那情景似乎十分辉煌。
那天晚上直到天黑以后,她还一直呆在沼泽农庄。斯克里本斯基后来陪她回家去。因为她简直不愿意离开他,她正在等待着,等待着某种新的经历。
那天晚上天气很暖,在四周新出现的暗影中,她感觉到了另一个更坚实、更美、更超然的世界。现在一切一定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他紧挨着她走着,仍是那样一言不发、全神贯注地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腰,轻轻地非常柔和地把她拉向他的身边,用那只胳膊使劲压在她的身上;她似乎已让他提起来,在空中飘动,她的脚几乎已碰不到地面了。紧贴在他的坚实的身体上前进,她似乎是躺在他的身上,只感到天旋地转。在她正感到几乎要发晕的时候,他把脸向她更贴近了一些,她的头正倚在他的肩上,现在她的脸已经感觉到了他的温暖的呼吸。然后,轻巧地,啊,轻巧地,那么地轻巧,使她感到简直马上要晕过去了,他的嘴唇接触到了她的脸,她感到似乎在一股黑暗的暖流中漂浮起来了。
她仍然等待着,在她那晕眩和漂浮的状态中等待着,完全像神话故事中的睡美人一样。她等待着。他又一次向她伸过脸来,他那温暖的嘴唇又一次贴上了她的脸。他们放缓脚步站住了。他们在树阴下一动不动地停下来,他的嘴唇停留在她的脸上,好像一只蝴蝶停留在一朵花上一样。她把身子更向他贴近一些。他一转身用两只胳膊抱着她,把她使劲搂住。
接着,在那片黑暗中,他轻轻向她低下头去,用他的嘴碰了一下她的嘴。她感到害怕,她呆呆地躺在他的怀里,感觉到他的嘴唇碰到了她的嘴唇。她完全呆住了,不知如何是好。接着他又把嘴伸过来,压在她的嘴上,一股温暖的急速的浪潮在她心中涌了上来,她微微张开自己的嘴唇,在一种痛苦的急切的旋涡中她把他更加拉过来,让他和她贴得更紧。她的嘴唇又贴过来,那浪潮起伏不定,那么温柔,噢,那么温柔,噢,可是又像一股强有力的河水的巨浪,无法抗拒,直到最后她发出一声盲目的喊叫,把他推开了。
她听到他站在她身边沉重地,奇怪地呼吸着,他那种可怕而宏伟的感觉占据了她的心灵。可是她现在在她自己的心灵中止不住微微退缩了一下。他们犹豫不决地又向前走去,像山头的桉树的影子一样不停地抖动着,当年她外祖父拿着一捧水仙花前往求婚的时候就曾走过这个地方,她母亲和年轻的丈夫也曾像厄休拉和斯克里本斯基一样紧搂着从这里走过。
厄休拉完全意识到覆盖在他们头顶上枝叶扶疏的大树的枝干,也意识到桉树的精美的叶子正仿佛是装饰着这夏夜的一串串的流苏。
他们紧挨着,步履协调地向前走着。他握着她的手,他们为要泡得更久一些,故意找较远的弯路走。她老感觉到自己仿佛被搂得离开地面了,仿佛她的脚已变得像一阵清风一样轻巧了。
他很想再吻她一下———可是那天夜晚他不准备再来那种直透心窝的亲吻了。她现在已知道,已知道亲吻是什么滋味了。所以他感到现在更难走近她的身边了。
那天夜晚,她上床的时候感觉全身像通了电一样地温暖,仿佛黎明的清风正在她心中吹动,把她举了起来。她深沉而甜蜜地,噢,是那么甜蜜地睡着。清早,她感觉自己简直像一株健旺的麦穗,那么芳香,又那么充实。
他们就这样在情窦初开的迷离惝恍状况中继续过着情人的生活。厄休拉对谁也没有讲这件事;她已经完全迷失在她自己的世界中了。
可是某种离奇的感情使她极希望找一个人,假装让她分担她的心事。她在学校里有一个很沉静、严肃的朋友叫埃塞尔。她感到必须对埃塞尔讲讲她的事。埃塞尔低着她的保证守口如瓶的头全神贯注地听着,于是厄休拉把她的秘密全部讲了出来。噢,那实在是太美了。他是那么地温柔,那么地多情、体贴!厄休拉简直像个老于此道的妇女那样谈讲着。
“你认为,”厄休拉问道,“让一个男人吻你———真正的接吻,而不是闹着玩,———是不应该的吗?”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