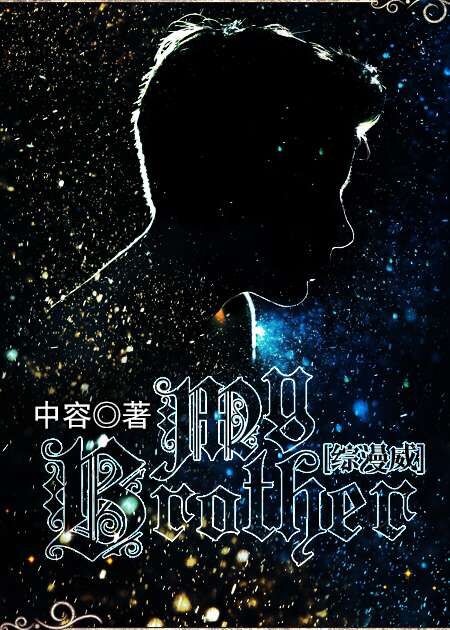the rainbow-虹(中文版)-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爬上那座小山,直朝着牧师的住宅走去。狂风在篱笆上发出呼呼的声音,他尽力用自己的身子挡住那一捧水仙花。他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只感觉到狂风在吹着。
夜已来临,光秃秃的树木在风中呼啸。他知道,牧师这会儿准在他的书房里,那波兰女人一定带着她的孩子在厨房里呆着,在那间屋子里呆着也很舒适的。他走进大门,沿着一条小道走下去,这时天光已经十分暗了。小道的两旁也有一些水仙在风中中摇摆,一些被吹乱的番红花,搅成一团,已经没有任何光彩了。
从厨房的后窗里,一道灯光射在外面的树丛上,他开始有些犹豫了。他怎么能这样办呢?向窗里望去,他看到她抱着孩子,坐在一张摇椅上。孩子已经换上了睡觉的衣服,坐在她的膝头上。她那长着一头乱发的漂亮的脑袋朝着火那边耷拉着,孩子的清秀的脸颊和白皙的皮肤反照出火光的影子;她几乎像一个成年人似的在想着什么心事。妈妈的脸色阴沉而安静。他痛苦地看到,她现在又沉浸在她过去的生活中了。那孩子的头发像玻璃丝一样闪闪发亮,她的脸是那样光彩夺目,简直仿佛是一个从里面照明的蜡人儿。狂风愈吹愈猛。妈妈和孩子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坐着。孩子用一双空虚的黑眼睛望着炉火;妈妈则出神地望着虚空。那小姑娘几乎已经睡着了,现在只是她的意志还勉强使她的眼睛圆圆地睁着。
在狂风摇动着那所房子的时候,孩子忽然不安地转过头来,布兰文看到她的小嘴唇动了一下。妈妈开始摇晃着身子,他可以听到那摇椅的底座发出的嘎吱声。接着他听到妈妈唱着一支外国歌曲的低沉单调的声音。接着又是一阵狂风吹过。那妈妈似乎已随着狂风飘走;孩子的一双黑眼睛睁得更大了。布兰文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彩,团团乌云正惊慌地匆匆在黑暗的天空飘过。
接着那孩子叹了一口气,像是抱怨,又像是命令地说:
“不要再唱那玩艺儿了,妈妈,我不愿意再听这支歌。”
歌声慢慢消失了。
“你应该上床睡觉了。”妈妈说。
他看到孩子紧抓住妈妈的身子表示抗议,看到妈妈仍然没有改变她的出神状态,看到了那孩子倚在妈妈身上使劲抓着她的神情。接着,那孩子忽然仿佛指责似的一字一句地说: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风仍在吹着,妈妈开始讲故事了,那孩子依偎在妈妈胸前。布兰文在外边等待着,惶惑不安地观看着在风中猛烈摇晃的树木和愈来愈浓的黑暗。他得追随他自己的命运,现在他还在门口徘徊。
那孩子偎着她的妈妈,蜷成一团,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在她的散乱的金黄色的头发中,那双黑色的大眼睛一眨也不眨,像一个蜷卧的小动物,除了眼睛之外,已经完全入睡了。妈妈坐在那里,仿佛灵魂已经出窍,那故事不过是自动从她嘴里冒出来罢了。布兰文站在外面,看到夜幕已经降临,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他抓着水仙花的那只手已经冻僵了。
故事终于讲完,妈妈站起身来,那孩子这时正紧紧地搂着她的脖子。她的身体一定很强健,她抱起那么大的一个孩子看来毫不费力。小安娜紧搂着她妈妈的脖子,那张漂亮的奇怪的小脸从妈妈的肩头上向外望着,除了那双眼睛,她已经完全睡着,而这双圆睁着的黑色的眼睛却依然在进行反抗,在和某种看不见的东西进行战斗。
她们走进里屋去以后,布兰文第一次在他站着的地方活动了一下身子,朝四面的黑夜看了一眼。他真希望,一切会真正像刚才这段毫无顾忌的时间他所感到的一样,那样的美丽,那样的随和。随着那个孩子,他也感到一阵奇怪的紧张,甚至是一种痛苦,仿佛是命中注定。
妈妈又回到厨房里来了。她开始叠着孩子的几件衣服。他敲门。她有点犹豫地打开门,朝后退了一步,完全像个外国人,神情显得有些不安。
“晚上好,”他说,“我就在这儿呆一分钟。”
她的脸色顿时完全变了;她毫无思想准备。她低头看着他。他这时手里举着水仙花,站在台阶下面由窗口照出的光线之中,他的身后是一片黑暗。他穿着一身黑衣服,她仿佛仍然不认识他。她简直有些害怕了。
可是,他已经走进门里,转身把门关上了。她向厨房中间走去,对他这深夜的来访感到很吃惊。他摘掉他的帽子,向她走近几步。然后,他就那样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戴着黑色的围巾,站在电灯光下,一只手拿着帽子,另一只手握着黄色的水仙花。她远离他站着,完全听他摆布,自己已经六神无主了。她不认识他,她只知道他是一个前来找她的男人。她只看见站在她身前的那个黑色的男人的身影,和他手里抓着的一束花。她看不见他的脸和他的闪闪发光的眼睛。
他呆呆地看着她,不很了解她,只感到自己是在她的存在的笼罩之下。
“我来到这里想跟你谈一句话,”他朝着桌子边跨进几步,把他的帽子和花放在桌上说。那束花他一撒手就松开变成一大堆了。她看到他前进,退缩了几步。她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存在了。狂风在烟囱里呼呼响着,他站在那里等待着。他已经放下了他手里的东西。现在他攥起拳头。
他意识到她站在那里,惶惑,恐惧,但已和他联系在一起。
“我到这里来,”他以一种出奇的平静和严肃的声音说,“想要求你嫁给我。你现在要结婚并没有任何约束,对吗?”
长时间的沉默,这时他的一双蓝色的眼睛显得十分奇怪,仿佛脱离了个人意志,直向她的眼睛里面看去,希望得到一个真实的回答。他希望找到她内心的真实。这时她仿佛被催眠了,最后终于不得不回答。
“是的,我完全可以随我自己的意愿再一次结婚。”
他的眼神马上改变了,进一步脱离了个人意志,仿佛他看着她就只是为了寻求她内心的真实。他那双眼睛是那样的稳定、集中注意,和永恒,仿佛它们永远也不会改变了。它们似乎直盯在她身上,要使她融化掉。她微微抖了几下,感到自己被重新创造了,完全失去自己的意志,和他融合在一起,和他具有了一个共同的意志。
“你要娶我?”她说。
他的脸色马上变白了。
“是的。”他说。
现在笼罩着他们的仍然只是惶惑和沉默。
“不,”她说,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我不知道。”
他感到他内心的紧张情绪已经被打破,他松开了拳头,他现在又能开始活动了。他站在那里看着她,神情恍惚,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有那么一段时间,她对他来说,似乎失去了真实的存在。然后,他看到她向他走过来,她十分奇怪地一直来到他身边,仿佛她并没有移动,而是在滑行。她把一只手放在她的外衣上。
“好的,我愿意。”她说,仿佛并不代表她自己。她用一双圆圆的、真诚的、此刻体现着最高的真实重新睁开的眼睛看着他。他站在那里,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他一动不动,只是他的眼睛完全被她的眼神慑住,因而感到很痛苦。她似乎用她的重新睁开的、简直像一个孩子似的圆圆的眼睛看着他,然后她离奇地动了一下,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难堪的痛苦。于是她慢慢地把她那微黑的脸和胸脯向他伸过来,那缓缓暗示着的亲吻使他不禁感到头脑里仿佛有件什么东西突然崩裂了,刹那间,他完全陷入昏天黑地之中。
他双手把她搂住,神情恍惚地吻着她。这样使自己完全跟自己脱离,对他简直是一种赤裸裸地难以忍受的痛苦。她被他搂在怀里,像个孩子似的轻盈和顺从,却又是那样渴求他的拥抱,无限的拥抱,这简直使他无法忍受,他几乎要受不住了。
他转身找到一把椅子,仍然把她搂在怀中。和她一起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把她紧搂在胸前。接着,有那么几秒钟,他已经完全进入睡乡,已被封闭在最深沉的睡梦之中,他已经睡着,把一切完全彻底地遗忘了。
慢慢地他又清醒过来,始终把她温暖的身体紧紧抱在怀里。她也和他一样完全沉默,和他一样沉浸在同样的遗忘之中和那丰饶的黑暗里。
他慢慢又回到现实中来,可是已经被重新创造过,已经在黑暗的子宫中重新孕育,又获得了一次新生。一切都是那样轻松和充满了光彩,像黎明一样清新,一切都无比鲜洁,都刚刚开始。像黎明一样,清新和幸福的酒杯越来越满了。她也和他一样沉默地坐着,仿佛她也完全有同样的感受。
接着,她抬头看着他,那双圆睁着的年轻的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彩。他低下头去,在她的嘴唇上吻着。黎明在他们身上撒下了它的光辉,他们的新的生命已经诞生了,一切都是非人所能想象的美好,一切是这样的美好,几乎像是经过一次死亡后的复苏。他忽然更紧地把她搂住。
因为,很快她脸上的光彩开始消失了,她躺在他的怀抱中,偏着头倚在他身上,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脑袋耷拉着,有一点疲倦,由于她感到疲倦,所以失去了神彩。而在她的疲惫心情中,她又有点想到要拒绝他了。
“我还有个孩子。”她打破长时间的沉默说。他不理解她的话。已经有很长时间他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话的声音了。现在他也听到狂风的吼叫,仿佛那风是刚才又吹起来的。
“是的。”他有点莫名其妙地说。他感到心中有一阵轻微的疼痛,因而止不住轻轻蹙起了眉头。他急于想抓住一样什么东西,可又总抓不着。
“你将来会喜欢她吗?”她说。
他心中的那股疼痛现在流遍了他的全身。
“我现在就非常喜欢她。”他说。
她仍然依偎在他的怀里,从他的身上获得温暖而毫不自觉。感觉到她呆在那里,从他身上得到温暖,同时把她自己的重量和她的离奇的信心交托给他,这对他是一种重要保证。可是她现在在哪里呢?她似乎是那样心不在焉。他的头脑中于是又充满了惶惑之感。他并不理解她。
“可是我比你年岁大多了。”她说。
“多大?”他问道。
“我今年三十四岁了,”她说。
“我是二十八岁,”他说。
“大六岁。”
尽管这使她有些高兴,可是他仍然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他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感到疑惑不定。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经历,这样完全为她所忘怀,而她又依偎在他的身上,让他用他起伏的胸膛承受着她的身体,感到她的重量依托在他的生存之上,因而使他既显得完备,更显得具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力量。他丝毫没有对她进行干预。他甚至并不了解她。她现在这样躺在那里,把她的重量完全放在他的身上,这对他真是一种非常离奇的经历。他满心喜悦,一言不发。让她躺在自己的起伏的胸脯之上,他感到了自己的强健的体格。由他们俩组成的这离奇的、不可侵犯的完备,使他感到自己像上帝一样可靠和稳定。在无比高兴之中,他想到如果牧师知道了现在的情况,不知会怎么说。
“你不必再在这儿呆下去,给人当管家了。”他说。
“我还喜欢这儿的这工作。”她说,“我已经跑了许多地方,我现在倒觉得这里很好。”
听到这话,他又一次沉默了。一方面她是那样贴近他躺着,而同时她又仿佛是从非常遥远的地方在给他回答。可是,他并不在乎。
“你自己的家是个什么样子,在你小的时候?”他问道。
“我父亲是个地主。”她回答说,“我们家正好在一条河边。”
从这些话里他并没有理解到很多东西,一切还是像过去一样模模糊糊。可是,只要她近在他的身边,其他的一切他都不在意。
“我也是一个地主———一个小地主。”他说。
“是的。”她说。
他几乎不敢随便动一动,他坐在那里,用两手搂着她。她一动不动地躺在他的起伏的胸脯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完全没有动。接着,轻轻地,胆怯地,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圆圆的胳膊上,放到陌生的地方。她似乎在他身上压得更紧了。自下而上的一股热流,直冲到他的胸中。
但是,这太快了。她站起身来,走到一个抽屉边去,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很小的盘垫。她看上去有一种安静的、对什么都很内行的神态,不论在华沙的时候,还是在叛乱之后,她和她的丈夫在一起时,她一直都当看护。她开始在桌上摆盘子,她似乎完全忘掉了布兰文。他坐直身子,对她的矛盾态度感到不能容忍。她来回走动着,让人无法理解。
接着,在他仍坐在那里沉思默想、惶惑不安的时候,她却向他走过来,用她那灰色的几乎带着微笑的闪光的圆圆的大眼睛看着他。可是她的既丑又美的嘴却仍然脉脉含悲,毫无表示,他不禁感到害怕了。
他的由于较长时间不曾使用而显得紧张激动的眼睛,在她的面前微微有些畏缩,他感到自己也显得有点畏缩了,可他却仍然仿佛是服从于她的意志似的站了起来,弯下腰去吻着她的含悲的厚重、宽大的嘴,而她也任他亲吻着,一动也不动。那恐惧的感情未免太强烈了。这一次他仍然没有得到她。
她转身走开。牧师的厨房里一切井井有条,然而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她和她孩子的无秩序和不整洁却使它显得更美了。在她身上既有一种说不出的离奇的遥远感,同时又仿佛有一种和他紧密相连的感觉。这情况使得他的心在他胸膛里猛烈跳动着。他站在那里,等待着,彷徨不安。
当他穿着他那身黑衣服,蓝色的眼睛发出使她惶惑的亮光,面部的肌肉紧张地抽动着,头发蓬松,站在那里的时候,她又一次向他走了过来。她笔直向他走来,走近他的穿着黑色衣服的紧张的身体,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胳膊上。他半天没有动。她的眼睛,在它们的最深处的一片黑暗中,原始的电光一般的记忆正进行着充满激情的斗争,同时既排斥他,又吸引着他。可是他仍然未为所动。他困难地呼吸着,额头上和他的头发根上,都冒出了汗珠。
“你想要娶我吗?”她慢慢地,永远带着那种不肯定的声调问道。
他简直害怕自己会说不出话来了。他使劲吸了一口气说:
“我要。”
然后又一次,这对他简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她又把一只手轻轻放在他的胳膊上,向他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