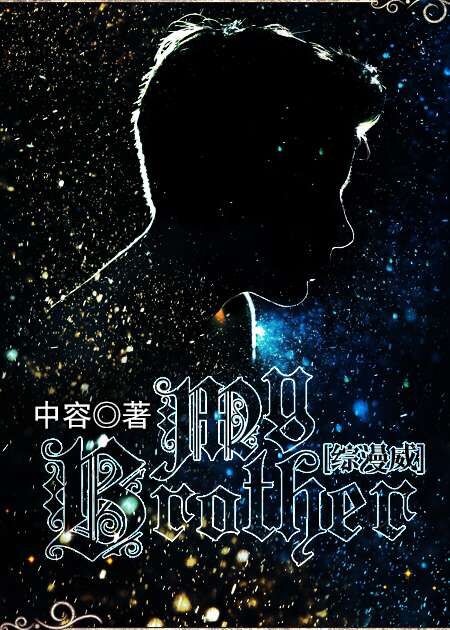the rainbow-虹(中文版)-第7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感到仿佛他的生命已经死亡了。他的灵魂已经消灭了。他的整个存在已经完全失去了活力,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幽灵,和生命完全脱离了。他已经失去了实体,变成一个平面的图形了。疯狂的情绪一天比一天更为严重,一种失去存在的恐惧占据了他的心。
他这里跑跑,那里跑跑,到处乱跑。可是不管他干什么,他知道他永远只是以他的皮囊出现,里面完全空空如也。他到戏院去看戏;他在那里所听见和看到的一切,都只不过停留在他的意识的冷冰冰的表面上,表面以下便什么也不存在了。这也就是他的全部知觉,因而他根本不可能再获得任何经历了。在他心中出现的只是一种机械的反应,此外便什么也没有了。他已经再没有生命,没有内容。在他的思想中也不存在他所接触到的那些人。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已知数的排列组合。在他现在所居住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厚度或深度,一切都不过是靠思想臆造出来的一些死的形象,没有生命,也没有存在。
在大多数时间中,他都和他的伙伴或朋友们在一起。很快,他会把什么全都忘记了。他们的活动构成了他对他自己的否定,他们牵动着他的消极的恐惧。
只有在喝醉酒的时候,他还感到比较快乐,他喝酒喝得很多。只要一喝醉酒,他就完全改变了他原来的神态。他马上变成了在温暖、散漫、空灵的世界中飘浮着的一朵温暖、散漫和闪闪发光的云彩。他在一种散漫和混乱的方式之中,对任何事都感到十分满意。一切都渐渐融化成一团玫瑰色的火光,他就是那个火光,一切东西都是那个火光,所有其他的人也都是那个火光,一切实在是太好了,太好了。这时他就会放开嗓子歌唱,一切都太美了。
厄休拉沉默而坚定地回到了贝德俄弗。她非常爱斯克里本斯基,这一点她是肯定无疑的。此外她便什么也不能承认了。
她读完了他那封一心想着跟她结婚,然后一块儿上印度去的长信,这信在她心中没有引起任何特殊的反应。她仿佛对他讲的关于结婚的问题全然未加理睬。这个念头似乎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她的头脑。对于那封信的绝大部分,她似乎觉得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空话。
她很高兴,也很随便地马上给他回了一封信,她是从来不爱写长信的。
印度听来是个十分可爱的地方。我现在几乎就可以看见我自己骑着一头大象,摇摇晃晃地在两排毕恭毕敬站在路旁观望的土人们中间走过。可是,我不知道我爸爸会不会让我去。咱们只能等着瞧瞧。
我一直还过着咱们俩在一块儿时我所度过的那令人爱恋的时光。可是我觉得,到最后你已经不是那么喜欢我了,是不是?在我们离开巴黎的时候,你就已经不喜欢我了。你为什么会那样呢?
我仍然非常爱你,我爱你的肉体。它是那么干净和漂亮。我真高兴你不会光着身子出门,不然所有的女人都会对你一见钟情的。那将会使我非常嫉妒,我实在太爱你了。
这封信使他多少还有些满意。可是一天一天地过去,他却仍只是那样游荡着,仿佛已经死去,完全不存在了。
直到四月底以前,他一直没有能够再到诺丁汉去。这一回,他拉着她和他一块儿到牛津附近他的一个朋友的家里去度一个周末。这时他们已经订婚了。他给她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这件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他给她买了一个翡翠戒指,她对这个戒指感到非常高兴。
她家里的人现在都跟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仿佛她已经离开他们了。他们现在对她的事都很少过问。
她和他到牛津附近一所郊区的房子里呆了三天。一切都十分舒服,她感到非常快乐。可是,给她留下最深刻记忆的却是在他和她睡过一夜偷偷溜回自己房间去之后,她清晨起来独自享受着自己的最丰富的生命,独自最充分地享受着她独自占有这个房间的时候。这时,她拉开窗帘,看到了下面花园里的李子树有如白雪盖顶,在一派阳光下闪闪发光,看到那开满花朵的树枝亭亭玉立在蓝天之下。它们舒展开自己的花朵,它们在蓝天之下把它们的雪白的花朵向四周抛撒出去!这景象让她多么激动啊!
她必须赶快穿好衣服,以便在任何人跑来和她谈话之前先到花园里那些李子树下去散一会儿步。她轻轻溜了出去,像一位女王在许多精灵中闲步。当她在树下抬头向蓝天望去的时候,那些花看上去仿佛是用银子做成的。这时她还闻到一点淡淡的香味,听到几只蜜蜂微弱的嗡嗡声,这充满生命的幸福的早晨是何等的神妙。
她听到开早饭的铃声,马上就进屋里去了。
“你刚才上哪儿去了?”别的一些人问她。
“我到李子树下去走了走。”她说,她的脸也像一朵花一样发亮了。“那地方实在太可爱了。”
这话使得斯克里本斯基不禁暗暗有点发怒。她没有邀他一块儿去。他感到非常恼火。
晚上月亮上来了,在月光下闪亮的花朵更显得那样的神秘,他们俩一块儿去看花。她在他走在她身边的时候,看到了他脸上的月光。在月光之下,他的五官都仿佛用银子铸成,而那躲在阴暗中的眼睛简直是深不可测。她热情地望着他。他显得非常沉静。
他们假装走累了,跑进屋里去。她很快就上床了。
“一会儿可尽量早点来。”她在假装和他吻别的时候低声说。
他紧张地、念念不忘地等待着,等着一有机会就赶快跑到她那里去。
她尽情享受着他的温柔,为他神魂颠倒。她喜欢把她的手放在他身体两边柔和的皮肤上,或者在他故意用劲绷紧下面的肌肉的时候,用手摸着他的后边,这里的肌肉由于骑马训练已经变得非常坚硬有力了;那原来用手摸着非常柔软光滑的地方,竟会忽然变得硬得捏都捏不动,并且是那样的对她尽心尽力,这使得她简直激动得如痴如狂了。
她占有着他的身体,并以一个占有者的喜悦漫不经心地享受着它。可是,他却慢慢对她的身体感到害怕了。他非常想她,他无尽无休地想着她,可是在他的情欲中出现了一种紧张情绪,或者一种阻挠力量,使他没有办法尽情享受那无限的拥抱慢慢带来的甜蜜的结束。他感到害怕。他的意志总是那样的紧张,那样的不可调和。
她的毕业考试将在盛夏时候进行。她坚持要去参加考试,虽然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她完全没有好好学习。他也愿意她去参加获得学位的考试。他想,那样她就会感到满意了。可是在内心深处,他希望她不会通过,这样她就会更喜欢他了。
“我们结婚之后,你是愿意住在印度,还是住在英国?”他问她。
“哦,当然愿意在印度,”她说,她那随随便便,显然不加考虑的神态使他十分生气。
有一次,她十分激动地说:
“我真愿意离开英国。这里的一切都是这样的下流和平庸,没有任何能鼓舞起人的精神的东西。我非常痛恨民主。”
听到她这样讲话,他感到很生气,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当她对任何事情进行攻击的时候,他多少都有些感到不能忍耐。那仿佛都是在攻击他似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带着敌意问她,“你为什么痛恨民主?”
“在民主制度中,爬到最上面的都是些贪婪的混蛋家伙,”她说,“因为只有他们那样的人才愿意拼命往上爬。只有堕落的民族才实行民主。”
“那么你想要什么样的制度呢———难道是贵族制度?”他问道,心中暗暗有些激动。他常常感到,他有权属于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然而,现在听到她谈到他的阶级,使他更感到一种由奇怪的、痛苦的欢乐而引起的痛苦。他感觉到,他这是默认了某种不合法的东西,他这是想利用某种错误的、可怕的有利条件。
“我就是喜欢贵族制度,”她大声叫着说,“而且我百分之百地更赞成以出身为基础的贵族制度,而不是以金钱为基础的贵族制度。在今天究竟谁是贵族———谁被选出来作为最好的人来统治我们:就是那些有钱的或者有办法弄钱的人。至于他们还有些什么别的全都无关紧要:但是他们必须有金钱头脑———因为他们是在金钱的名义下进行统治的。”
“政府是人民选出来的。”他说。
“我知道是他们选的,可是你说的人民是什么?他们中每一个个体都只知道金钱的利益。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手里的钱和我的钱一样多,那他就和我完全平等,这一点使我非常愤恨。我知道,我比他们全都要好得多。我痛恨他们。他们不能和我平等。我痛恨这种以金钱为基础形成的平等,这是一种肮脏下流的平等。”
她瞪着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望着他。他感觉到她仿佛要把他给毁灭掉了。她已经抓住了他,现在正想把他摔个粉碎。他对她越来越生气了。至少,他得为和她的共同生活而进行斗争。一种无情的、盲目的反抗精神占据了他的心。
“对钱我完全不在乎,”他说,“对那一锅肥肉汤我也无心染指。我是非常爱护我的手指头的。”
“你的手指头跟我有什么关系?”她有些激动地说,“你和你那可爱的手指头,你们所以要到印度去,因为到了那里你也会变成一个人物头了!你要去印度,这不过是一种逃避罢了。”
“那是要逃避什么呢?”他大叫着说,由于愤怒和恐惧脸都变白了。
“你想着,印度人比我们本国人更简单得多,你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好让你对他们作威作福。”她说,“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去统治他们,你们还认为自己做得很对。你们是些什么人,凭什么感到自己做得很对?你们在统治别人方面,究竟在什么问题上做得很对?你们的统治罪该万死。你们统治的目的是什么?不也就是要把那里的一切都变得和这里一样下流和毫无生气吗!”
“我丝毫也没有感觉到我们做得很对。”他说。
“那么你感觉到什么呢?一切全是一派空话,不管你感觉什么或者不感觉什么。”
“你自己怎么感觉呢?”他问道,“在你自己的思想上,你觉得你完全对吗?”
“是的,我是那么觉得,因为我反对你们,反对你们那些古老的没有生气的东西。”她大声说。
她最后通过冷酷的知识发出的这句话,立即打下了他那面正在飞扬着的旗帜。他感到自己忽然让人砍去了两腿,就剩下一个毫无价值的躯干了。他感到一阵可怕的晕眩,仿佛他的两腿真的被人砍掉,现在完全不能活动,自己完全变成一具残废的必须依靠别人生活的毫无价值的躯体了。仿佛自己已经不再活着的一种无比绝望的可怕的感觉使他神志恍惚,简直要发疯了。
现在,甚至就在他还和她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也已经感觉到了他本身的死亡,现在他尽管还在行走着,可是他的身体仿佛已变成一具没有自己的生命的皮囊了。在这种状态下,他既听不见,也看不见,已完全没有感觉,只是他的生命的机械活动还在继续着罢了。
他以他在目前这一状态中所能有的仇恨情绪,仇恨着她。他的机智向他提出种种可以使她尊重他的办法。因为她根本就不尊重他。他在离开她之后,并没有给她写信。他同别的女人,同格德伦调情。
最后,这件事使得她愤怒万分。她对他的身体还仍然抱有强烈的嫉妒心理。她所以如此愤怒地斥责他,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完全满足一个女人,现在却又去打别的女人的主意。
“我不能让你满足吗?”他向她问道,整个脸直到喉咙又一次完全变白了。
“不能,”她说,“从在伦敦的第一个星期起,你就从来没有能够满足过我。你现在也没有能够满足我。你这么跟我———,那对我有什么意义呢?”
她带着一种冷漠的、完全不在意的鄙夷神态一扭肩膀把头转了过去。他感到真恨不得把她给宰了。
当她已经刺激得他快要发疯的时候,当她看到他的眼睛里已经露出无比阴森的发疯一样的痛苦神情的时候,她忽然感到一阵巨大的痛苦,巨大的无法克服的痛苦正啃咬着她自己的心。她爱他,因为哦,她一定要爱他,她极力希望能够爱他,这种感情比生或死的感情还要强烈。
而在这个时候,正当他由于感到她正在彻底毁灭他而无比愤怒,当他的一切自满情绪已被彻底消灭,当他日常生活中的那个自我形象已被粉碎,现在仅剩下一个被剥光的、原始的、萎缩的、受尽折磨的人的时候,她希望爱他的热情现在真正变成了一种爱情,她又仰身搂住了他,他们带着无比强烈的激情搂在一起,这一回他知道他已经使她满意了。
可是在这一切之中,已包含着一颗日益发展的死亡的种子。在每一次接触之后,她对他的难以满足的欲望,或者对她始终没有从他身上得到的某种东西的欲望愈来愈强烈,她的爱情越来越变得无法获得满足了。在每次接触之后,他一次比一次更加疯狂地依靠着她,想自己坚强地站起来,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办事的希望越来越削弱了。他感到自己已经完全变成她的一种属性了。
刚好在考试之前,降临节来到了。她准备先去休息几天。多萝西继承了她父亲的一笔遗产,在苏塞克斯有了自己的一所庄园。她邀请他们到她那里去小住几天。
他们来到小山脚下,在多萝西的那座地势低下的整洁的农庄里,他们可以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厄休拉老想到那些小山顶上去跑一跑。有一条白色的小道盘旋而上,一直通到那个最高的小山的圆顶。她一定要去。
在小山顶上,她可以看到几英里之外的英伦海峡,看到微微照亮天空的起伏的海面,在远处像一个影子一样升起来的怀特岛,穿过平整的平原向海边蜿蜒流去的河流,那阴森一片的阿润德尔城堡,然后便是那平坦的高高升起的大草原,形成天空之下的一片平整的高地。它以它自己的闪烁着阳光的巨大的力量接受上天的恩宠,在他巨大的永远不会削弱的身体和那天空的永远不变的身躯交合的时候,只有很少一些小树丛干扰其间。
往下,她可以看到小山坡上的一些村庄和树林。火车勇敢地奔跑着,一个很精致的小玩艺儿,摆出一副无比重要的姿态越过草原开进了一个小山口,头顶上不停地冒着白色的蒸气。但整个看上去却是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