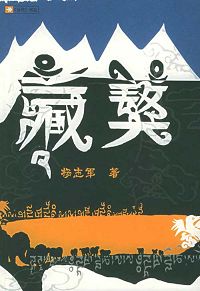獒-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去看了一下,告诉他,这个可能是老年性的风湿病,膝盖的软骨内膜里面可能是有积液,夜晚冷的时候,得多盖层被子。
央金正在缝制羊皮袄,她已经给她阿爸缝好了一件,手里缝的另一件不知道是给谁的,看上去挺宽大,尼玛也穿不起。
我夸赞她的手艺,央金不仅有一副好歌喉,而且人品很好,特别贤惠,不知道哪个男人有福气,找到了她这样的好妻子。
我问:手里的羊皮袄子是给谁的?真好看!
央金神秘地一笑,转开了话题,说:来的时候,我从家里买了些酥油,今年的酥油就不用打了,再说也没人手,这几天阿爸的老毛病又犯了,尼玛也有些感冒。
我说:大叔的腿是风湿骨病,得赶紧治,拖久了不行,多吉大叔家有些草药,回头我拿一些来给尼玛熬药,喝一喝,感冒就好了。
央金忽然问我,她问我好端端的,怎么会想到来大草原,马上入秋了,草原上的风暴令人可怕,这里的冬天会特别的冷,你会受不了。
央金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我也不需要隐瞒什么,我开玩笑地说:刚从部队退役下来,女朋友又分了手,大都市让我感到陌生,我就来到这里了,顺便看看大黑,黑子在部队的时候,就天天在我耳朵边上放风,尽夸大黑的好,可我一到这里,就天天尽受大黑的气。
央金开怀地大笑起来,她说:黑子说的没错,大黑是只好獒,通人性,很有爱心,她小的时候,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呢!大黑是只有神性的獒,知道做善事,积功德。
我不大相信央金的话,央金又告诉我,大黑救过不少人的命。
我说:怎么可能?她只不过是条獒。
央金沉默了一会,说:可能,她是一条不同寻常的獒吧?也可能,是上天赐给大草原的神物!
我拿了些草药给尼玛治感冒,尼玛躺着,非要搂着我的脖子,喊叔叔。
才让大叔的腿这几天就一直在痛,特别是到晚上,多吉大叔说:天就要冷了,风暴快来了,咱们得把帐蓬扎牢一点,羊圈也得加固。
这几天,就一直在做这些事情,我不能够有太多的时间陪大黑闲聊,我是个耐得住寂寞的人,而大黑也是一只耐得住寂寞的獒,除了每天和毛毛亲密一会,余下的时间,大黑就全部用来陪伴她的羊们一起度过。
一天,多吉大叔忽然找到我,我正趴在草地上,欣赏大黑在玩一只土鼠,她把土鼠按在爪子下面,土鼠一个劲地挣扎,大黑就放开爪子,土鼠抬腿要跑,大黑又一爪子按了上去,土鼠被打得晕头转向。
我正瞧得津津有味,多吉大叔走过来说:兵兵啊,有件事得麻烦你了。
我正为打扰了多吉家这么久而没有做过什么实事感到不安,一听这话,就跳了起来,问:什么事?
多吉大叔说:本来才让大叔的腿得去大城市里的医院瞧瞧,但是家里没人,走不开啊!央金她妈妈从小懂些草原上的药草,以前才让大叔的腿犯病的时候,就是央金她妈妈采了药草来治的,也管得上一阵子,现在央金妈妈去世了,央金也嫁了出去,就没有人采草药了。
我急忙说:我去,可是,我不知道采什么药。
多吉大叔说:央金说她知道,但是一个女人家,山上不安全,我又得照顾才让大叔和尼玛,所以,想让你和她一起去,顺便采些治咽喉的药,冬天来了,常常咳得睡不着。
我欣然同意,觉得在大草原上采草药应该是件很有趣的事情,说不定还会成为一趟有趣的探险。
多吉大叔还是有些不大放心,要让大黑陪我们一起去,我说:不用,家里的羊怎么办?万一狼又来了呢?
多吉大叔笑了起来:上次那群狼是不会来了,狼都是领地性极强的动物,每一群狼都会占据一片领地,别的狼群是不会轻易闯入这片领地来的,除非它们饿疯了。倒是秋天了,晚上其它饥饿的动物会有一些,没事,有我和格桑在呢!再说,还有条猎枪。
对于那条土猎枪,我没抱太大的希望,但是对于草原生活经验丰富的多吉大叔,我却是十分信任的。
我担心,大黑一路上要吃很多东西,多吉大叔笑着说,你可以路上多带点吃的,大黑自己也会寻找食物,你放心,饿不着她,要是把你和大黑放生在大草原上,几个月过去,说不定活着回来的还会是她呢!
我笑了起来,多吉大叔还不知道我的野外生存能力,就算是饿得吃草,我也要挺着回来。
出发前,我学着央金的样子,神情虔诚地围着草地上插起的经幡转了十多圈,央金又把一块泥土样的东西挂到了我的脖子上。
她告诉我:这是擦擦。
擦擦这个词的发音是从梵语而来的,其意思无法从字面上表达出来,指的是泥制小佛像。是西藏同胞们寄托自己心愿的圣物,也是一种宗教和艺术的结合品,有时人们也将擦擦随身携带,充当护身符。
我和央金带着大黑出发了,毛毛有些不舍地吼叫了几声,看着我们离去。
第二十八章、采药
路上,央金告诉我,本来想带毛毛去的,但是大黑比毛毛更熟悉这里的环境,毛毛性子急躁,远远比不上大黑的沉稳和机智,而且大黑知道辩路,就算是迷路了,大黑也能把我们领回来。
一路上,我听着央金和我说大黑所有的好处以及她令人惊奇的地方,听得我神往,对于大黑,我除了喜爱之外,更慢慢地加多了一分仰慕之情。
好奇怪,我竟然会仰慕一头獒,我可能是疯了。
我问央金:要去哪里采药?远吗?
央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和我说起草原上的事情。
她说:草原上的藏民们就是靠天吃饭,靠地活命,只有在水草丰美的牧区才会放牛放羊,有些地区是种植农作物的,而有些地区农作物种不好,牧场又长得不好,只能养两三头牛羊,但他们靠山近,平时一年的经济收入就全靠采草药卖钱了。
我这才明白央金的意思,我问她:进山里采,那还要走很远的路啦?
央金呵呵地笑起来,看了我一眼,反问:你怕远啊?我们藏族的姑娘走上两天两夜都不会觉得累呢!我们习惯了。
我笑了笑,没有跟她说,让我负重四十公斤走两天两夜都可以,那些过去的往事就过去吧,在大黑的面前,我没有任何可以拿出来炫耀的资本。
大黑为牧民们做了那么多事,为大草原做了那么多事,她也从来没有炫耀过自己,也从来没有向主人要求过什么回报,默默无闻,毫不起眼,我还有什么好厚着脸皮炫耀自己的呢?
央金又告诉我,她阿妈以前就是住在山区附近的,那里的人就是靠草药卖钱维生,采药最好的时候就是在夏季,当地组织起来一起进山采药,今年采山这边,明年采山那边,让山里的药草也有个休养生息的时候,天不绝人,人更不能自己绝了自己的后路啊!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感动,为什么在这片最纯朴的大草原上,我总是被最朴实最平凡的东西打动。
每一天每一刻,我都生活在被一种神圣的思想操度着的境界中,不知道是这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操度了我,还是大黑,或者就是生活在这大草原上的最朴实憨厚的人们。
大黑不紧不慢地走在央金的身旁,一点也没有担心前面的路会是什么样子,她完全一副老练的姿态,这令我想起一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囤”。
大黑就是这样一只獒,没有人会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但她又总能在突如其来的事情面前泰然处之,她那种平和的心境,是我期望拥有却又无法拥有的,我总是会想许多无关紧要的事。
有时候,我常常会想,为什么人类的杂念就那么多,反而不如一只獒,獒都能保持一种随遇而安的平常心态,为什么人类却不能?
到最近的山区要走一天,加上进山采药,一来一回也差不多三天的时间了,藏区的气候有些独特,因为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被称为除南极、北极外的地球第三极。
地理状况特殊,山区的气温落差就更为明显,提起“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这句话,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
我们要去的那座山,山顶上还没有积雪,但到冬天就会有,山脚下还是阔叶林,越往上走,树木就会越来越显得瘦小,央金还告诉我,路上可能会下雨,叫我做好准备。
我只知道在藏区,东面比西面雨水要多,南面又比北面雨水多,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应该还不算雨水最多的地方,何况藏区一年的降雨量百分之八十集中在夏季,现在正赶在夏季的尾巴上,已经入秋了。
我很佩服藏族的姑娘,体力真好,整整走了一天,央金不说累,大黑也没停步,就是饿的时候,也是一路走一路吃,我更不好意思提出要休息了。
快傍晚的时候,我们终于望见了不远处的那座山。
天快黑了,央金说:夜不入山,就在山脚附近搭个帐篷过夜,明天一早再进山采药。
这次搭的是外出旅行用的那种方便帐篷,搭这个最简单,打开来一抖就成了,我搭了两个小帐篷,一个给央金住,另一个我用。
央金从背包里拿出吃的来,先递给大黑吃,大黑陪我们走了一天,也累了,趴下来休息,一边吃着羊肉。
央金说:咱们是草原上的牧民,进山的时候少,进山如历险,得把大黑喂饱了,明天还要靠大黑领路呢,大黑鼻子可灵了,知道避开有危险的东西。
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在吃肉,肉啊肉啊,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成了一种可怕的东西,我现在渴望吃点蔬菜,哪怕是一棵最普通不过的大白菜也好。
我只吃了一点就吃不下了,我把手里没动过的肉递给大黑,她欣然接受了,虽然我很累,想休息,但看到大黑接受我给的食物,心里却开心得要死。
晚上,大草原上的风又刮了起来,大黑守在帐篷外面看夜,我有些心疼她,几次招唤她进我的帐篷休息,大黑都坚持不肯,她仿佛知道夜晚的大草原上随时都会有危险降临,显得格外的警惕。
大草原的夜晚很寒冷,我身上穿着的那套薄薄的迷彩并不能抵御那层层袭来的寒意,我索性也不想睡了,大黑不肯休息,我也睡不着,我从小帐篷里钻出来,仰躺在大黑身边,看大草原上开阔的天。
今晚没有星星,连月光也没有,天上的浓云一片连着一片,因为草原上没有什么阻挡物,既使天很沉,视线也还是很辽阔。
远远的,我似乎听到了一声枪响,从这声音上来听,不是普通的土制猎枪,应该是八一步,也可能是五六。
太远,枪声似有似无,我想,总不可能会是进口枪支,美国的M16或者比利时的FNC,在这茫茫的大草原上,那除非是职业的国际走私贩子。
我的心突然抖了一下,大黑也警惕地竖起了耳朵,仔细地收集声音的来源,但那声音太微弱了,如果不是凭借着我多年来对枪声的极其敏感,我也许根本就不会感觉到那蚊子叫似的声音。
第二十九章、翻车
我和大黑都在极力搜寻第二次枪响,但那声音再也没有响起来。
风突然刮得大了起来,小帐篷被吹得东倒西歪,还好帐篷的四角打得比较牢固,总算没有被掀翻过去。
草原上日照时间长,紫外辐射也大,有不少动物是在夜间出来觅食的,我看见两只豹猫慌慌张张地从我面前跳了过去,眨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还有几只臭鼬正在不远处探头探脑。
突然,一滴水滴落到我的脸上,接着,紧密的雨点就毫不留情地砸落下来,下雨了,夜间的雨,来得及,我钻进了帐篷,呼唤大黑。
大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她围着两个帐篷踱步,还是不肯进帐篷来,我除了对枪声敏感以外,对草原上别的声音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我也没发觉什么竟外的情况,就冒着豆大的雨点跑出去,把大黑拉进了帐篷。
雨点噼里啪啦地落下来,像洒豆子一样,打在帐篷上面,哐咚哐咚的响,在这样吵闹的环境中,我更加无法入睡,突然间,心头涌起了太多的心事,就慢慢地讲给大黑听。
今晚,大黑也似乎有心事,她对我的话提不起多少兴趣来,总是在帐篷里东张西望,有几次还想冲出帐篷去,我实在不忍心大黑站在大雨中守夜,无奈之下,只好把她脖子上的那根绳圈拴到了我的脚脖子上。
半夜,我迷迷糊糊的睡着了,脚脖子上剧烈的拉扯把我痛醒,我翻身起来,拧亮了手电,赫然发现在我的脚边竟然盘着一条粗大的蟒蛇。
这条蟒蛇有拳头粗,似乎有两米长,可能是夜间避雨取暖,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进来,蟒蛇无毒,但并不是说对人类就不构成危害。
可能是怕吵醒了央金,大黑并没有用力地吼叫,只是低低地吠了两声,然后把我拉醒,我跳下地来,不敢去惊动那条蟒,蟒的缠绕力巨大的惊人,一条巨大的蟒完全可以把人的胸腔挤碎。
外面的雨已经小了许多,淅淅沥沥的,夜色渐淡,草原上的夜很短,我知道天快亮了,就带着大黑走出帐篷去透气。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远山如黛,我正在欣赏黎明前的美景,突然身后一阵响动,央金也醒了,正走出帐篷,问我怎么起这么早?
我说:帐篷里有条蟒,反正也睡不着了,就出来走走,昨晚的雨好大,今天进山,路肯定很滑。
央金笑了一笑,掀开我的帐篷,那条大蟒还盘在帐篷里,正在享受夜晚消失前的最后一丝温暖。
央金说:昨晚下雨,山路肯定很险,今天必须提前进山,不然时间可不够用。她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小撮类似香料的东西,取了个打火机点燃,香气在帐篷里飘散开来,蟒蛇闻到香气,竟然乖乖地溜走了。
我问央金:那是什么东西?
央金告诉我:是草原上流传下来的一种驱虫蛇的药草,没有名字,山区里很常见,晒干以后才更有效。
我们拆了帐篷,雨也停了,就地用了些早餐,我们把大黑喂得饱饱的,就出发了。
山路真的很不好走,下了一夜的雨,地很滑,而且山路又窄又险,稍不小心就有可能顺着山坡滚下去。
我以为自己在攀援方面算是高手,但在这里却派不上用场,随手在山壁上一抓,就是湿湿滑滑的一把,央金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