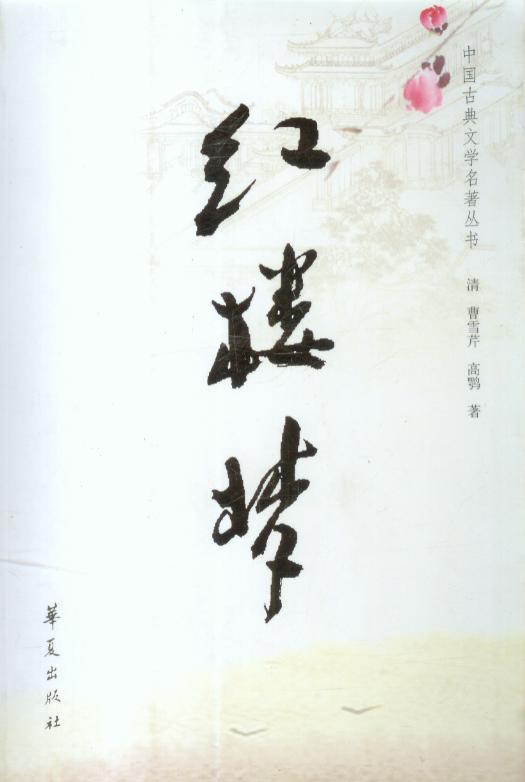读遍红楼-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相同的,“近”字原字应该是“诉”字,只是“近”与“诉”形近而讹。甲辰本作“正是:一觉黄粱犹未熟,百年富贵已成空”。己酉本作“正是:一场幽梦同谁诉,千古情人独我痴”。 除了甲辰本之外,其它各本文字基本相同,特别是后半句“千古情人独我痴”则全同。但是试魁抄本中作“半窗幽梦同谁诉,千古柔情独我痴”。
抄录第五回诗对异文 书影(六)
“半”字与“一”字形不相近,且笔划多,不会是形近而讹。“柔情”与“情痴”音不同形不近,也不可能是误抄所致。只有“诉”与“诉”当是形近而讹。因此可以说试魁抄本的诗对完全是独出,不同于其它抄本十分明显。
(4)抄本《红楼梦》第52回回目里“俏平儿情掩虾须镯,勇晴雯病补雀金裘”,书内有宝琴所写的一首五律:
昨夜朱楼梦, 今宵水国吟。
岛云蒸大海, 岚气接丛林。
月本无古今, 情缘自浅深。
汉南春历历, 焉得不关心。
抄录第52回回末诗对 书影(七)
试魁抄《词选》中选抄了这首五律之后,接着抄了一副诗对:“有隙怀疑终错误,无心生事自安宁”。查各脂评本均无此诗对。我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此诗对当是第52回的回后诗对。因为试魁抄诗对常随所选的同回诗词曲前后,而这副诗对恰在五律之后,应是回后诗对位置。其次,诗对的内容与平儿“情掩”而“无心生事”相关合。此一判断如不错的话,那么独此抄本回末或回前有此诗对,亦属一大收获。
(5)在列藏本发现之前,所有已发现的脂评抄本第64回均无回前诗,列藏本回前诗作:
深闺有奇女, 绝世空珠翠。
情痴苦泪多, 未惜颜憔悴。
哀哉千秋魂, 薄命无二致。
嗟彼桑间人, 好丑非其类。
这首五律中的“悴”原作“额”,圈去,旁加“悴”。“哀”原作“衷”,圈改为“哀”。“其类”原作“豈额”,点改为“其类”。 但在试魁的《诗词选》中不仅选抄了这首回前五律,而且是“原文”照抄,没有一个字被圈改、旁加、点改之痕迹。令人惊奇的是,同回回末王府本、甲辰本有诗对作:“只为同枝贪色慾,致叫连理起戈矛”。戚序本诗对的第一句同前,而第二句作“致教连理起干戈”。列藏本的回末诗对第一句也同于前三种本子,第二句则作“致教连理起戈矛”,又别于其它抄本。试魁抄录本回末诗对全同列藏本。由此我想到试魁抄录的《诗词选》的底本与列藏抄本极可能同属一个祖本的“姊妹本”或称“兄弟本”。这个事实同样有力地证明列藏本也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说的“伪造本”!
在试魁所抄的《诗词选》176首(篇)诗文中,同程甲本文字相异者几乎每首(篇)中都有,例如第3回写荣禧堂上,有一副联是“座上珠玑昭日月”而此抄本则作“照日月”, 与有的抄本相同,这里就不再列出。以上列举五条“异文”,足以说明试魁所据底本的重要性。尽管直到今日我们还无法一下子找到这个“底本”。以见“庐山真面目”,但它曾经存在过,并且其中的诗词曲文被抄存下来,使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本子于嘉庆初年尚在人间,已经是够庆幸的了。由于此,我深信凡是对脂评抄本《红楼梦》价值有所认识的真正学人,都会对试魁的抄录之功抱有崇高的敬意!
四、补抄的《红楼梦》后40回诗词
试魁所选抄的《红楼梦》诗词曲文最后一篇是第76回凹晶馆“联诗”,题目是“大观园中秋夜十三元韵”,并小字注明“六十八句”。但抄至妙玉“续诗”末四句时,只到“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谁言”而止。下面接抄“彻旦体云倦,烹茶更细论”二句及后面诗文完全是另一种笔墨:前面所抄文字可见抄者的书法圆熟,行书流畅,墨迹偏浓(见书影之三)。而接抄部分字迹拙硬,墨迹淡浅,如同钢笔学书。所抄的内容有:第37回探春写给宝玉的“小启,,全文;第87回宝钗写给黛玉的“书子”全文;第87回黛玉抚琴所吟唱的四首“悲往事”曲;第87回惜春口占偈语“大造本无方”四句;第89回宝玉祭晴雯词;第89回形容黛玉诗对:“亭亭玉树临风立,冉冉香莲带露开”;第99回周琼给贾政信;第116回宝玉梦中所见“真如福地”的匾额和对联;第118回宝玉所吟“内典语中无佛性’’二句;第120回“千古艰难惟一死”二句、“天外书传天外事”二句、“说到辛酸处”四句;最后是“我所居兮”“归彼大荒”一诗。令人惊疑的是,从“千古艰难惟一死”二句起到“归彼大荒”四首诗和诗对,又与前80回诗文抄录书法风格又完全一致,只是墨色略浅淡。接下所抄“续红楼梦酒令”则是工整的小楷,墨色亦较深。
应该指出,所抄后40回诗文与程甲本对照,异文极少。第87回所抄的宝钗”“书子”中有三处异文,“未尝不叹冷节遗芳”句的“冷”字,抄本作“吟”;“悲时序之递嬗兮”句的“递”字,抄本作“遽”;“静言思之兮恻肺肝”句的“恻”字,抄本作“测”。这些异文,我认为均是“形近而讹”。又如第99回周琼给贾政信中有两处异文,程甲本作“寸幅”,抄本作“寸福”,亦属“形近而讹”例,而非真正的“异文”。
从上面所列例文,结合抄录笔迹,我有两点印象颇深,在此提出来供读者思考。
(1)后40回诗文非与前80回同时一气抄录,字体和墨迹有明显区别,补抄部分与前80回是否一人虽不敢遽断,但我比较倾向于另一抄手所抄,而最后几首诗又由原抄者补抄完。
(2)后40回诗“底本”是程甲本。以梦稿本对照检查,出现多处异文。与程甲本对照则全同,由此可证抄者非据梦稿、甲辰等本所抄。大家都知道,程甲本印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乙本印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抄录者不论在京城还是在江南,都可购到或借到程本,从而据以补录后40回诗文是极为自然之事。
五、读抄本《红楼梦诗词选》感言
从一部看似极普通的抄本《红楼梦诗词选》,发现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的流传过程,令人意想不到。其实,这种意想不到既有偶然性,但内中也蕴含了它的必然性,这就是大千世界的奇妙之处——“缘”。有了“缘”可以千里来相会;无“缘”近在咫尺不相识。“缘”只可遇,而不可求!
抄本具有流动性、互递性、长久性,它在流传中是一种“载体”。对于这种“载体”的特殊功能,今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理解和体验的过程。我们之所以重视抄本,并非出于一己的某种嗜好,重要的是它承载了历史文化和学术信息。试魁的《红楼梦诗词选》得益于抄本的流动性和互递性,这是他的“缘份”。我们今天读到了试魁的抄本也是得益于它的流动性、互递性、长久性,从而由这部抄本的文字中发现了一部不同于程甲乙本又有异于其它已发现的十余种早期脂评抄本和近人抄本《红楼梦》。这部抄本所带给我们的版本信息和研究价值,至少证明了脂评抄本《红楼梦》的存在年代和流传的范围!
试魁抄录《红楼梦》诗文时非常用心,在抄录176首诗文中很少见到有点改和旁添文字。《芙蓉女儿诔》文字长,生僻字较多。他认真、细心地抄录,令我感动不已。就此一端,我们就应该感谢这位抄写人,向他表示由衷的崇敬之意!
早期抄本《红楼梦》存在的事实并非由近人发现的十余种抄本才为学人所重视。除了舒元炜、戚蓼生、梦觉主人的序文之外,清人诗文笔记中的无数记载,同样是可信的证据。这其中包括永忠、明义、周春、张汝执等人写下的文字。这些人生存年代有前有后,所居地域有南有北,而社会地位更是相去悬殊,为什么他们的记载如此的一致?难道他们都有未卜先知的本事并且联起手愚弄20世纪的胡适和他的“弟子”们?这种认识恐怕有违一般的常识常理,以至于让头脑正常的人有点“匪夷所思”!
至于说到“脂批”内容的优劣,是否可以引用,我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谓才力各有分限,尺寸不可强求。二是不能“舆论一致”。每一个读者、研究者知识素养有高低之分,兴趣偏好不同,感觉和认识事物的能力也不可能“齐步走”。但是,他们都有权利、有自由来选择自己所认同、所喜欢的东西。古语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如今,找不到一份“红头文件”上写着:凡研究《红楼梦》者必须承认“脂评”、必须“引用”脂评。也没有什么人撰文著书说“只准许说脂评好,而不能说低劣”。事实上,从打脂评本发现之后,说好者有之,说劣者也有之,大家平等。这如同每个人写文章要引用某个人的文字一样——“随你的便”。因为这是学术,学术是自由的、平等的,谁也不能强迫他人接受或者放弃!
所谓“脂评”抄本,一是指《红楼梦》早期流传的载体形式是手抄的,而不是活字摆印本;二是这些抄本都附有数量不同的“批语”,其中署名最多者叫“脂砚斋”,因而习惯上统称为“脂评”。这些抄本的抄录年代和批语作者的生存年代和批语的内容优劣,情形很复杂。每一个本子都需要进行认真的、负责任的鉴别,对其中的每一个疑点都要深入研究。怀疑并不等于结论,考察过程也不是结论。怀疑是对个人学养的考验,也是个人的权利。但结论则是关系到一个抄本的“生死存亡”,这是极严肃的大事,不能人为地制造“冤假错案”。对人要如此,对一个本子也必须如此。
应该指出的是,现今发现的早期脂评抄本绝大多数都可能是“过录本”,而不是曹雪芹的“原稿本”或是他亲自誉录的“清抄本”。有的本子甚至是“过录本”的“过录本”,时间已可能是在清嘉道以后过录的。但是,它的“底本”并非是无根无据、凭空编造出来的。由于抄本是在流动中、互递中产生的,所以出现“脂评”的“合并”、“脱漏”、“移位”、错白字等等现象,就需要研究者细心、认真的分析,而不是“一棍子”打死了事。例如,抄本上有些批语明显为嘉道以后或阅者或抄者后加上去的,需要细心辨识。陈庆浩先生在他的《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一书中就将“后人”的评语厘剔出来作为“附录”, 这是真正作学问的态度和眼光。
早期抄本上批语的作者,首先是这部小说的读者。他们利用传统的“评点”形式发表自己的读后感,尽管是即兴的、零碎的,但他们有权这样作。今人不是也在运用这种“评点”形式吗?作为读者,他们同我们在地位上人格上完全是平等的。我们不能由自己的好恶来剥夺古人的权利和自由。
由于在抄本上写“评语”的人非止一二人,所以出现批语之间相互矛盾,毫不足怪。如果几个人在批语行文风格、艺术见解完全一致,那倒可能是不真实的。
有人责问道:批者怎么知道那么多拟书“底里”,作者怎么可能让他人在自己书上写下那么多评语……其实这位先生忘记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气,不能用今日作家(不一定是全部)的创作生活实况、心态去套古人的心态和他们的创作实践。远的例子不说,曹雪芹祖父曹
寅创作《北红拂记》时就邀请了一群朋友相互切磋琢磨,边讨论边修改自己的作品。他还将自己的抄本分赠给友人批评。他的朋友朱彝尊、尤侗、毛际可等十来位不仅在抄本前后写了评论文字,而且还在本子中写了65条批语。难道这部戏(《北红拂记》)和这个抄本,也是他人“伪造”出来的?平心而论,古代作家对著作权的观念实在没有今人那么强烈,也没有“著作法”的约束。孔夫子一生“述而不作”,他的学问被他的学生记下来到处传扬,他仍然非常伟大,至今还被中国人所尊崇。其实,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古代小说、戏曲本子上有的是“佚名”,有的是署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诸如“逍遥子”、“西周生”、“兰陵笑笑生”等等,不胜枚举。时代不同,风气不同,人们即使考证不出真名实姓也不能说是“伪造”出来的。至于这些小说、戏曲本子加了批注,有的署了名字,多数署的是字号或别号,也很难考证出个结果来。《红楼梦》早期抄本上的批者署名也都是字号之类,并非是首创。我们大可不必为此制造新的“文字狱”,动不动就给加个“伪造”的罪名。考证,考证,要考而有证。古人考证是孤证不足信,说明前人作学问的认真和慎重,我们实在应该学习。所谓学问,不仅要学还要问,问书本,问贤人,就是调查研究。调查愈深入,研究的根基就愈牢实。做学问不能急功近利,为了扩大自己的“能见度”,就把自己的某种怀疑当作结论。特别是对待古人留下的文献要慎之又慎,万不可因为他们是“作古”之人,就可以随便罗织罪名。前人批评某些学人“凌虐古人,欺骗今人”,我们今人实在应该记住这些教训!
红学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困惑。新世纪更加需要大家脚踏实地的去作些力所能及的建设。否定一切,把20世纪百年红学描绘得一团漆黑,只剩下了“他”自己,这并不是真正红学史家的眼光!
2005年1月3日
注释:
① 明清期间,特别是清乾隆年间,京城和江南出版业出现了繁荣景象。但是当时许多文人写出的诗文集、小说、戏曲。仍然有许多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乾隆三十三年(1768)永忠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并写下吊曹雪芹三首诗,其所“观”《红楼梦》就是抄本,而他收入此诗的《延芬室集》也是抄本。其后有潞村张汝执忆及乾隆五十四年(1789)所见的《红楼梦》也是抄本,其序写在印本上(见北京图书馆藏程甲本)。同年还有舒元炜在一部抄本上写了“序”。这些事实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