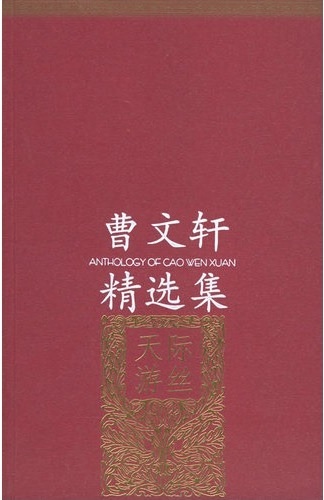曹文轩精选集-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秋秋,银娇奶奶就不太觉得寂寞了。要是秋秋几天不来,银娇奶奶就会拄着竹竿,站到路口,用手在额上搭着,朝路上望。
九月十三,是小巧的生日。一大早,银娇奶奶就坐到河边去了。她没有哭,只是呆呆地望着秋天的河水。
秋秋来了,就乖乖地坐在银娇奶奶的身边,也呆呆地去望那河水。
银娇奶奶像是对秋秋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我不该把她放在别人家就去了江南。她走的时候,才七岁。她准是想我了,跑到了河边上,用芦苇叶折了条小船。我知道,她想让小船带着她去找我呢。风把小船吹走了。这孩子傻,忘了水,连鞋也不脱,跟着小船往前走了。这河坎陡着呢,她一个悬空,滑倒了……”她仿佛亲眼看到了似的说着,“那天我走,她哭着不让。我哄她:‘妈妈给你买好东西。’小巧说:‘我要棒棒糖。’‘妈妈给你买棒棒糖。’小巧说:‘我要小喇叭,一吹呜呜打响的。’‘妈妈给你买小喇叭。’我的小巧可乖了,不闹了,拉着我的手,一直走到村口。我说:‘小巧回头吧。’小巧摇摇头:‘你先走。’‘小巧先走。’‘妈妈先走。’……我在外拼命挣钱,跌倒了还想抓把泥呢。到了晚上,我不想别的,就想我的小巧。我给她买了棒棒糖,一吹就呜呜打响的小喇叭。我就往回走。一路上,我就想:秋天,送小巧上学。我天天送她去,天天接她回来,要让她像她爸那样,识很多字……这孩子,她多傻呀!……”她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水,仿佛要从那片水里看出一个可爱的小巧来。
快近中午时,银娇奶奶说:“我生下小巧,就这个时辰。”她让秋秋搀着,一直走到水边,然后在河坎上坐下,摸摸索索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包,放在掌上,颤颤抖抖地解开,露出一沓钱来。“小巧要钱用呢。”她把钱一张一张地放在水上。河上有小风,大大小小的钱,排成一条长长的队,弯弯曲曲地朝下游漂去。
秋秋用双手托着下巴,默默地看那些钱一张一张地漂走。有时,风有点偏,把钱刮向岸边来,被芦苇秆挡住了,她就会用树枝将它们推开,让它们继续漂去。
离她们大约四五十米远的地方,一个叫九宽的男孩和一个叫虾子的男孩把一条放鸭的小船横在了河心,正趴在船帮上,等那钱一张一张漂过来。他们后来争执起来了。九宽说:“明年让你捞还不行吗?”
虾子说:“不会明年让你捞吗?”
争来争去,他们又回到了原先商定好的方式:九宽捞一张,虾子捞一张。
秋秋终于发现了他们,沿着河边跑去。她大声地说:“不准你们捞钱!”
九宽嬉皮笑脸地:“让你捞呀?”
“呸!”秋秋说,“这是给小巧的钱!”
虾子“咯咯咯”地笑了:“小巧?小巧是谁?”
九宽知道一点儿,说:“小巧早死了。”
秋秋找来三四块半截砖头,高高举起一块:“你们再不走开,我就砸了!”她的脸相很厉害。
九宽和虾子本来就有点儿怕秋秋,见秋秋举着砖头真要砸过来,只好把船朝远处撑去,一直撑到秋秋看不到的地方,但并未离去,仍在下游耐心地等着那些钱漂过来。
秋秋坐在高高的岸上,极认真地守卫着这条小河,用眼睛看着那钱一张一张地漂过去……
五
这地方的帮哭风曾一度衰竭,这几年,又慢慢兴盛起来。这年春上,往北边两里地的邹庄,一位活了八十岁的老太太归天了。儿孙一趟,且有不少有钱的,决心好好办丧事,把所有曾举办过的丧事都比下去。年纪大的说:“南边银娇回来了,请她来帮哭吧。”年纪轻的不太知道银娇奶奶那辉煌一哭,年纪大的就一五一十地将银娇奶奶当年的威风道来,就像谈一个神话般的人物。这户人家的当家主,听了鼓动,就搬动了一位老人去请银娇奶奶。
银娇奶奶听来人说是请她去帮哭,一颗脑袋便在脖子上颤颤悠悠的,一双黑褐色的手也颤动不已。这里还有人记得她呢!还用得着她呢!“我去,我去。”她说。
那天,她让秋秋搀着,到小河边去,用清冽的河水,好好地洗了脸,洗了脖子,洗了胳膊,换了新衣裳,又让秋秋用梳子蘸着清水,把头发梳得顺顺溜溜的。秋秋很兴奋,也就忙得特别起劲。最后,银娇奶奶让秋秋从田埂上采来一朵小蓝花,插到了头上。
银娇奶奶是人家用小木船接去的。秋秋也随船跟了去。
一传十,十传百,数以百计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想看看老人们常提到的银娇奶奶,要领略领略她那闻名于方圆几十里的哭。
大多数人不认识银娇,就互相问:“在哪儿?在哪儿?”
有人用手指道:“那就是。”
人们似乎有点儿失望。眼前的银娇奶奶,似乎已经失去了他们于传说中感觉到的那番风采。他们只有期待着她的哭泣了。
哭丧开始,一群人跪在死者的灵柩前,此起彼伏地哭起来。
银娇奶奶被人搀扶着,走向跪哭的人群前面。这时,围观的人从骚动中一下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皆跟随着银娇奶奶移动着。银娇奶奶不太利落地跪了下来,不是一旁有人扶了一下,她几乎要歪倒在地上。她从领口取白手帕时,也显得有点儿拖泥带水,这使从前曾目睹过她帮哭的人,觉得有点儿不得劲。她照例仰起脸来,举起抓手帕的手,然后朝地上拍下,但拍得缺了点儿分量。她开哭了。她本想把声音一下子扯得很高的,但全不由她自己了,那声音又苍老,又平常,完全没有从前那种一下子抓住人并撕人心肺的力量了。
围观的人群失去了平静,开始乱动起来。
钻在最里边的秋秋仰起脸,看着那些围观的人。她瞧见了他们眼中的失望,心里不禁为银娇奶奶难过起来。她多么希望银娇奶奶把声音哭响哭大哭得人寸肠欲断啊!
然而,银娇奶奶的声音竟是那样的衰弱,那样的没有光彩!
从前,她最拿手的是数落,那时,她有特别好的记忆和言语才能,吐词清晰,字字句句,虽是在哭泣声中,但让人听得真真切切,而现在,她像是一个人在僻静处独自絮叨,糊糊涂涂的,别人竟不知道她到底数落了些什么。
跟大人来看热闹的九宽和虾子爬在敞棚顶上,初时,还摆出认真观看的样子,此刻已失去了耐心,用青楝树果子互相对砸着玩。
秋秋朝他们狠狠瞪了一眼。
九宽和虾子却朝秋秋一梗脖子,眨眨眼不理会,依然去砸楝树果子。
当虾子在躲避九宽的一颗楝树果子,而不小心摔在地上,疼得直咧嘴时,秋秋在心里骂:“跌死了好!跌死了好!”
这时死者的家人,倒哭得有声有色了。几个孙媳妇,又年轻,又有力气,嗓子也好,互相比着孝心和沉痛,哭出了气势,把银娇奶奶的哭声竟然淹没了。
人们有点儿扫兴,又勉强坚持了一会儿,便散去了。
秋秋一直守在一旁,默默地等着银娇奶奶。
哭丧结束了,银娇奶奶被人扶起后,有点儿站不稳,亏得有秋秋作她的拐棍。
主人家是个好人家,许多人上来感谢银娇奶奶,并坚决不同意银娇奶奶要自己走回去的想法,还是派人用船将她送回。
一路上,银娇奶奶不说话,抓住秋秋的手,两眼无神地望着河水。风把她的几丝头发吹落在她枯黄的额头上。
秋秋觉得银娇奶奶的手很凉很凉……
六
夏天,村里的贵二爷又归天了。
银娇奶奶问秋秋:“你知道他们家什么时候哭丧?”
秋秋答道:“奶奶说,明天下午。”
第二天下午,银娇奶奶又问秋秋:“他们家不要人帮哭?”
秋秋说:“不要。”其实,她听奶奶说,贵二爷家里的人已请了高桥头一个帮哭的了。
“噢。”银娇奶奶点点头,倒也显得很平淡。
这之后,一连下了好几天雨。秋秋也就没去银娇奶奶的茅屋。她有时站到门口去,穿过透明的雨幕看一看茅屋。天晴了,家家烟囱里冒出淡蓝色的炊烟。秋秋突然对奶奶说:“银娇奶奶的烟囱怎么没有冒烟?”
奶奶看了看,拉着秋秋出了家门,往小茅屋走去。
过不一会工夫,秋秋哭着,从这家走到那家,告诉人们:“银娇奶奶死了……”
几个老人给银娇奶奶换了衣服,为她哭了哭。天暖,不能久搁,一口棺材将她收殓了,抬往荒丘。因为大多数人都跟她不熟悉,棺后虽然跟了一条很长的队伍,但都是去看下葬的,几乎没有人哭。
秋秋紧紧地跟在银娇奶奶的棺后。她也没哭,只是目光呆呆的。
人们一个一个散去,秋秋却没走。她是个孩子,人们也不去注意她。她望着那一丘隆起的新土,也不清楚自己想哭还是不想哭。
田埂上走过九宽和虾子。
九宽说:“今年九月十三,我们捞不到钱了。”
虾子说:“我还想买支小喇叭呢。”
秋秋掉过头去,见九宽和虾子正在蹦蹦跳跳地往前走,便突然打斜里拦截过去,并一下插到他俩中间,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她已用两只手分别揪住了他俩的耳朵,疼得他俩吱哇乱叫:“我们怎么啦?我们怎么啦?”
秋秋不回答,用牙死死咬着嘴唇,揪住他俩的耳朵,把他俩一直揪到银娇奶奶的墓前,然后把他俩按跪在地上:“哭!哭!”
九宽和虾子用手揉着耳朵说:“我们……我们不会哭。”他们又有点儿害怕眼前的秋秋,也不敢爬起来逃跑。
“哭!”秋秋分别踢了他们一脚。
他们就哭起来。哭得很难听。一边哭,一边互相偷偷地一笑,又偷偷地瞟一眼秋秋。
秋秋忽然鼻子一酸,说:“滚!”
九宽和虾子赶紧跑走了。
田野上,就秋秋一个人。她采来一大把小蓝花,把它们撒在了银娇奶奶的坟头上。
那些花的颜色极蓝,极鲜亮,很远处就能看见。
秋秋在银娇奶奶的坟前跪了下来。
田野很静。静静的田野上,轻轻地回响起一个小女孩幽远而纯净的哭声。
那时,慈和的暮色正笼上田野……
阿雏
一
阿雏坚决地记住:他的双亲亡于他六岁那年一个秋天的夜晚。
那天,有路人捎来消息:五里外的邹庄要放电影。路远,父母怕阿雏睡沉了骨头软,难抱,便掏给他五分钱买糖嗍,软硬兼施,终于将他哄住,跟老祖母待在了家中。
看电影的人很多,田埂上行人缕缕行行,互相呼唤着,黑空下到处是远远近近的人声和小马灯闪烁的黄火。
要过渡。
河边站满了急匆匆的人,船一靠岸,逃难一般都抢着上,船舷离水面只剩两三寸了,还又爬上两个大汉来。船离了岸,船上人一个挨一个,挺直了身子,棍子似的立着,战战兢兢,全不敢看水。船歪歪地行至大河中心,远处一艘轮船驶过,把波浪一层层地扩大过来,人一摇,船一晃,翻了。
各人顾各人,赶紧逃命,河上一片呼爹叫娘。会水的,自然不在乎。半会水的,呛几口水,也翻着白眼上了岸,直着脖子吐水。阿雏的父母皆是“旱鸭子”,听见喊了几声,沉了。
上了岸的人忽然想起似乎该下河救人,无奈天阴黑得让人胆怯,几个下河的光在水面上乱喊乱抓,动作不小,却是虚张声势,没有一个敢往河水深处扎的。待有胆大的赶到,时间又太迟了。
出事后几日,大狗的老子在河边村头说,当时,船翻了,阿雏的父亲一把死死抱住他的胳膊,两人就一起沉到了河底。他就又掐又拧,可阿雏的父亲任掐任拧死不撒手。他想自己小命这回要玩完了。吃了一嘴河底烂泥,他兀生一个大的智慧:拔出口袋里的手电筒,往阿雏父亲手里一塞!灵!阿雏父亲呛蒙了,以为一定抓住了什么救命的东西,松了他,却抓住那手电筒。他乘机一松手电筒,摆脱了阿雏父亲,钻出水面,一人爬上了岸。
说这话时,大狗老子的脸很活,很有光泽,显得自己的智慧比别人优越许多。
而那些听的人都惊呼:“险啊!”很有些佩服大狗老子的聪明和狡猾。
“放在我,早就跟着去阴曹地府充军了。”
“那你就不能抱着你胖老婆睡觉了。”
“嗤嗤”地,有两个女人笑。
说到最后,大狗的老子不免有点儿惋惜,道:“那只手电筒,我是刚买的。”
夹杂在人群中的阿雏,一直无声无息地听着,后来就蹲在了地上。人群散了,他还蹲在地上。蹲不住了,就瘫坐在地上,用目光呆呆地看着河水,看着河上漂过一段朽木、一只死鸡、一朵硕大的菊花……天黑了,还看。
过了三年,老祖母不在了,阿雏就一人过,有时到外祖母家混几顿,有时就在村子里东一家西一家地吃。他固执地认为村里人都欠他的。他的吃相很凶,像条饿极的荒原狼崽,不嚼光吞,饭菜里一半外一半,撒一桌、一地,鼻尖上常沾着米粒在外面闲荡。
二
阿雏养得极壮实,比同龄孩子足高一头。天生一头又黑又硬的鬈发,像一堆强力螺旋弹簧乱放着。眼睛短而窄,目光里总是藏着股小兽物的恶气。
村里的孩子都怕他,尤其是小他两岁的大狗。
他上学时,很气派,前呼后拥地跟着一大帮孩子。他让他们用一张凳子抬他走,这几乎成为一种嗜好。一到雨天,他越发地爱这样做。他要看那些小轿夫们在泥泞中滑得东倒西歪,滑得“嘟嘟”放屁。要是把他摔了,他就一定用脚踢他们的肚子或屁股。他很少亲自做作业,他指定谁代做,谁就得做。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他几乎就没在家里吃过一顿早饭。他把谁的鼻子一点,说声“你!”谁就得带煮熟的鸡蛋。那回轮到大狗带鸡蛋,恰好家里刚将鸡蛋卖掉,他便只好去偷,被人家抓住,连拍了三个后脑勺。
这里没有敢不听他话的孩子。不听?他会刁钻古怪地惩罚你:把你诓到麦地里,扒了你的裤子,让你露出“小茶壶”,光腚儿蹲着,羞得没法出去;逼你沿着梯子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