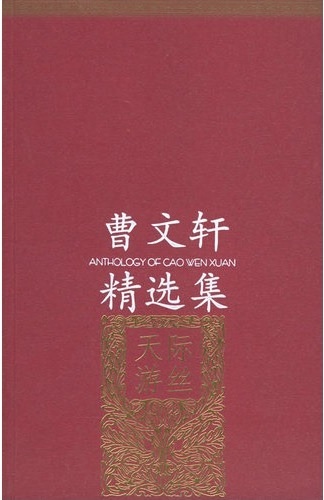曹文轩精选集-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时候,我喜欢我的女老师……
一
我父亲是一所农村小学校的校长。我们家就跟随着他,安在这所小学校里。
我七岁那年,她从城里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到了父亲的学校。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我们家门前。当时,门前那棵栀子树开花了,一树纯白的花朵。她就站在它下面,翘首望着其中一朵盛开着的。她的肤色很白,跟栀子花的颜色十分相近。十点钟的太阳正从天上斜照下来,她满脸阳光。阳光下,她脸上的茸毛闪着淡金色,像一枚刚刚成熟的桃子。对于那对眼睛,我当时只觉得我从未见到过,但却说不出感觉。后来多少年,那对眼睛时时浮现,但也始终不能用语言将它们表述。前年,我到南方一个山青水秀的风景区去游览,偶然间又获得了那种感觉。当时,我正跳到一条清澈的山溪中的一块石头上,刚要用手撩水玩,却又忽然停住了:深深的、凉匝匝的水底,有两卵黑亮的石子,本是溪水被微风所吹,轻轻波动,但我却觉得是那两卵黑石子像谜一样在闪动。就在那蓝蓝的山溪里,我又看到了她的眼睛。
“这花真好看。”她说。空气似乎立即变得甜丝丝的。
我呆呆地坐在门槛上,嘴里正很不雅观地啃着一大块白薯干,趁她没注意,我把那块白薯干悄悄地塞进怀里。
“这花真好看!”
我转身进屋搬出一张凳子,爬上去,把那朵花摘了,又跳回到地上,把它送到她面前。
她接过那朵清香清香的栀子花,朝我一笑:“你是校长家的?”
我点点头。
她把花戴在了头上:“好看吗?”
我点点头。
“以后我每天摘一朵,行吗?”
我点点头。
她又朝我一笑,走了。
过不一会儿,前面的屋子里传来了轻轻的、水一样的歌声。现在想起来,她并不会唱歌。我也从未听到过她真正地唱过歌。但,她的声音我却是永远忘记不了。那声音纯静而欢乐,像是从心的深处细细地流出,像是月光洒在夜晚的田野上。
她是在她的宿舍里唱的。后来,我常常听到她唱。她一唱,我就坐到门槛上去啃白薯干。啃着啃着,不知为什么停住了,待一串口涎“噗嗒”掉到手面上,才又拉回魂儿来继续啃。
后来,来了一个吹笛子的男人,我就只能听到笛子声了。
在她的宿舍与我们家之间,没有一堵高墙,只有一道矮矮的木栅栏。
那天,我从外婆家回来,就觉得在绿树中间忽然地有了一道闪光,定睛一看,发现那道木栅栏忽然都变成了白色。
是她从父亲那里要来了一桶白漆刷成的。
正是秋天,地上到处开着淡蓝色的野菊花,映衬得那道白栅栏更加好看……
二
当她站在讲台上,微微羞涩地朝我们笑时,我才知道,她现在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一年级小学生最难管教,一个个都是不安分的猴子,坐没坐样,站没站相,凳子没有被屁股焐热,就刺闹闹地难受。这时,就会做些小动作。记得小时候做作文,做到心中油然升起一股痛改前非的情感时,每每总要来这么一句:“我以后一定不做小动作。”其他孩子几乎也是千篇一律地有这么一句。这次的作文里有这么一句,下一次的作文里依然还会有这么一句,可见小动作是那个年纪上最容易犯的毛病。只有那么十分钟的安静,就开始捏鼻头,扭身体,抓耳挠腮,像是满屋里蚊蚋横行。要不就交头接耳,或在桌肚里玩玻璃球和从家中箱底里盗出的铜板。老师说些什么,干脆全没听见。小时还尤其善于流鼻涕,一走神,那鼻涕就双双“过河”了。不知是谁“嗤”的一声,于是大家都忽然想起了鼻涕,教室里便“飒飒”有声,像夜风掠过林梢。这时再抬头看,讲台上的老师正把目光从眼镜上方射出来,狠狠的。我们屏住呼吸,把眼睛瞪得灯盏一般,意思是说:我们在听呢!过一会儿,教室里就又开始动作起来,起先声音如蚕食桑叶,最后就如同雨滴纷纷打在芭蕉叶上,盛时,教室里“轰轰嗡嗡”,像远处传来的山洪声。
谁也不愿教一年级。
她来了,并且还微笑。过去的几个老师大概都不会笑,因为我们就没瞧见他们笑过。她头上戴着栀子花,不一会儿,教室里就飘起淡雅的清香。我们没有做小动作,以后一直也没有做。几十双眼睛全神贯注地看着她。看她的眼睛,看她说话时弯曲的嘴形,看她捏着粉笔的手——她用三根手指捏粉笔,无名指和小拇指像兰花的花瓣儿开着。我们只看见她,却听不见她的声音——不,听见她的声音了,仅仅是声音而已,但不知她说了些什么。
当时,我们傻乎乎的样子一定非常可笑。
而且,我们竟然没有鼻涕了。其实鼻涕还是有的,只是不愿让她看见,用劲把它憋住罢了。
只要她一进教室,教室就像秋天的池塘那么安静。
可是期中考试,我们考得糟不可言,及格的才四五个人。父亲把她找了去,态度和蔼地问了情况。晚上,隔着那道白色的栅栏,我听见她在宿舍里哭了。
她再进教室时,不笑了。她从前排第一个孩子问起:
“为什么没有考好?”
那孩子叫大国。他只顾看着她的眼睛,却不回答。
“问你哪!为什么没有考好?”她生气了。她生起气来时,我们就会觉得她更好看。
大国结结巴巴:“我……我上课看你……”
“看我?看我什么?”
“看你眼睛了!”
她想笑,但却用洁白的牙齿咬住了嘴唇。她挨个问下去,回答如出一辙:
“我看你的眼睛了!”
当我低着头也这么回答时,我听见了她急促的喘气声。过了一会儿,她骂了一句:“你们是群坏蛋!我不教你们了!”我们抬起头来时,她已经跑出了教室。
我们坐在那里半天没动,心里感到非常害臊和难过,一个个像罪犯似的耷拉着脑袋。我们来到她的房间门口,靠着墙壁,一个挨一个地站着往她的门口挤。被挤到门口的,转身又挤进来,实在挤不进来的,就跑到队伍的尾巴上再拼命往门口挤。有几个女孩把耳朵贴到门上听,然后小声说:“她哭了。”于是一个传一个,像传口令似的传下去,“她哭了。”“她哭了。”“她哭了。”……
门打开了,她走了出来。
我们赶紧像一群小耗子闪到一边。
她轻声问:“以后上课,你们还看我的眼睛吗?”
我们全体立直了身子,几乎同时像呼口号一样:“不——看——了——!”
三
她既文静又活泼,常和我们一起玩。玩起来,她纯粹是一个孩子,混在我们中间,她忘了她是老师。她有时把我们带到空旷的田野上,我们就像一群麻雀“唧唧喳喳”地围绕着她。她跑到哪儿,我们就呼呼地跟到哪儿。有时,她忽然跑起来,我们就欢叫着追赶她。见我们追不上了,她又回过头来望望。待快要追上她了,她又跑了。那回我去东北,在森林里追一头小鹿,就又想起她这副形象来。那小鹿伶俐可爱,用温柔而淘气的眼睛望着我。我向它走去,它又活活泼泼地跑了,像股轻风,像团柔云。可是跑了一阵,它又停住,回头望着我,那样子很让人怜爱。
她喜欢我们,尤其是我。
据母亲讲,我小时候长得很体面,十分讨人喜欢。两岁之前,我就很少在家喝母亲的奶,因为总是被邻居家抱了去玩,然后从这家传到那家,能顺着河边传出去一里多地。饿了,就喝也正在奶孩子的其他母亲的奶。母亲自己的奶水将衣服洇湿了,胀得受不了时,就沿着河边去找我,总要找半天才能把我找回家。七岁时,我很懂事了,说话很甜,品行不恶,不会骂人,很少做讨人嫌的坏事。大概是因为这些因素,所以她很喜欢我。
也正是这份喜欢,她让我生了一场病——
她家离这儿有十里地。每个星期六下午,她差不多都要回家去。她又要回去了,忽动了念头,将手放在我的肩上,对我母亲说:“我带他去我家,行吗?”
母亲同意。
她又低头问我:“去吗?”
我连忙点点头。
我跟着她,高高兴兴地走了十里路。
她也很高兴,一路上老轻声唱歌,还不时地顺手掐一两根已经枯萎了的狗尾巴草。
那时候没有电视,晚饭后洗洗脚,嗑嗑瓜子,就得睡觉。她家不穷,可也不能为我一个八岁的小孩专支一张铺,再说农村也没有这个习惯,来个人,都是与别人挤一挤。
“我要睡在谁的脚底下呢?”我心里在想。
“跟我睡。”她说。
我站着不动。
她端着油灯往里屋走去:“跟着我呀。”
我磨磨蹭蹭地跟着。
她把油灯挂在墙上:“你睡那头,我睡这头。”
我还是站着不动。
“脱衣服呀。”
我记得我脱得极慢,脱一件衣服像是足足花了一年时间。不像是脱衣服,倒有点儿像剥皮。
“快脱了钻被窝呀,冷。”
当时的农村孩子睡觉都没有衬衣衬裤,赤条条,一丝不挂,像个浪里白条。我终于剥光了上身。我低下头,很害羞地看着自己赤裸着的扁平的瘦胸脯,从未觉得光身子有那么难看,有那么别扭,情不自禁地用胳膊搂抱着自己。下面的裤子,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脱了。
“把裤子脱了呀。”
我低头望着床上一条已经放开的花被子。
我窘极了,一点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难堪的场面,额上竟汗津津的。我真想逃进黑暗里去。她却毫不在意,去外屋取东西去了。趁这当儿,我立即扒光了裤子。像一只被穷追的野猫忽然瞥见一方洞口,我爬上床,仓皇钻入被窝——啊,她终于看不见了!
“怎么这样快呀?”她说了这么一句,先摘下了头上的发卡,解掉了头绳,甩了甩头发,那些头发就一下子飞扬起来,仿佛被捆绑了一整天,现在终于得到了自由。然后,她就开始脱衣服。
我像巢中小鸟忽然看见了人,立即将脑袋缩进了被窝。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我还是把双眼紧闭,仿佛一睁了眼,还是能看到什么魔鬼似的。但我的耳朵和鼻子却是无法设防、堵住的。我听见了她脱衣服时的声,闻见了她脱去衣服后身体散发出的那种温暖、新鲜、带着某种特别气息的味道。那气味永远流散在了我的记忆里。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心里似乎是有点喜欢听那声音和闻那气味的,虽然战战兢兢的像一只被人缚住了的小猎物。
大概是她用手掀起了被子的一角,因为我感觉到有一股凉气从被子的那头过来了。
她进了被窝。她的脚伸过来了。当碰到我的身体时,我如同被电猛击了一下,随即,一股温热的暖流,刹那间流遍全身,一直流到我的胸腔里,使心突突地剧跳起来。除了母亲和奶奶,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在同一个被窝里接触一个成年女性。我有点儿发抖了,像是一只小鸡雏掉进了冰窟。
“冷吗?”她问。
“不……不冷。”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在打颤。
“把被头压紧。”
由于我的胆怯,我不敢把被头掖得很紧。
“压紧呀。”她用脚背轻轻地磨擦着我的身子,脚背有点儿凉。
灯还未熄灭,在掖被子的时候,一束灯光照进被窝,我一眼瞧见了她赤裸的脚。脚弓弯弯的,脚趾头像一枚枚鲜嫩的新蒜。我赶紧把被子压住。
我不敢靠她。我只觉得她的身体很烫很烫,而且柔嫩得使我不好意思。我被一种八岁孩子所有的害臊弄得浑身紧张,一阵阵发热。于是,我就往墙壁那边靠、靠……
“冷。”她说了一声,却将身体往我这边紧紧地靠了过来。
我已经抵着墙了,毫无退路,再也无法躲让她的身体。
她仿佛真有点儿冷似的,欲从我身上取得一些温暖,便将身体紧紧地贴着我光光的后背。
在那个时刻,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自己的身上能有一层布。我再也无法挣扎了。我只有闭起眼睛。我想起了自己一次抚弄刚出壳的毛茸茸的小鸭。我把它放在手上。它想跑,可是它跑不了。它试了几次,见根本没有可能了,也就死心了,老老实实、温温顺顺地由着我了。
现在,我就是那只小鸭。
我对她身体的感觉,起初很不清楚,只是觉得烫。不像是睡在被窝里,倒更像是沐浴于流动的温水里。后来,才慢慢有了一些其他的感觉。随着长大,经验的日益丰富,那些感觉便有了细微的层次,并且还在不断地增加着印象。我发现,有些感觉是不会消失的,会一辈子存活在你的灵魂里,并且会不时地复活生长,反而将当初还很朦胧的感觉丰满起来,明晰起来。她的身体特别光滑,像春风吹绿的油亮亮的白杨树叶那么光滑,像平静的湖水那么光滑,像大理石那么光滑。非常柔软,像水那么柔软,像柳絮那么柔软。渐渐地,我不再觉得她的身体烫人了,反而觉得她的身体有点凉阴阴的,像雪,像晨风,像月光,像深秋时的雨,像从阴凉的深水处刚刚取出的一支象牙色的藕,又像是从林间深处飘来的略带悲凉的箫声。
我睁开眼睛,望着天窗。
天上有一枚月亮,很纤弱,只淡淡地亮,像涂了一层薄薄的霜。天很蓝,河水那样的蓝。
或许是出于好奇,或许是因为空气清冷而一时难有睡意,她开始用手指抚弄我的脚趾。她的柔指是温暖的。我的脚微微有点发痒,但我坚持着没有动弹。像是怀疑我脚趾的总数可能不对似的,她一个个地核实着。数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好像终于弄清楚了脚趾的数量,一个也不少,就放下心来,不再数了。但,她的手并没有离去。她开始用手指捏我的脚。捏了左脚捏右脚,捏了右脚又捏左脚。先是轻轻地捏,然后就逐步加大了力量。有时捏得狠了点,让我生疼,可我不叫唤,随她捏去。奇怪的是,我的注意力并不都在脚上,我想到了我的那群鸽子,想到了在田野尽头的水塘里抓鱼,想到了妈妈、妈妈的手镯、妈妈的耳环,想到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