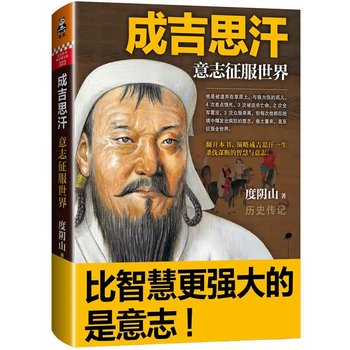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性的了;而其实呢,认识倒真是第二性的。意志甚至于被看作一个思维活动而等同于判断;在笛卡儿和斯宾诺莎那里就是这样的。根据这种说法,任何人之所以是他,是由于他的认识然后才成为他的。他是作为道德上的零而来到这世间上的,是在世上认识了事物之后,然后才作出决定要成为这,要成为那。要这样作,要那样作的。他还可以由于新的认识又抓住一种新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又变为另一个人。再进一步,照这种说法看来,人将首先把一个东西认为是好的,因为有了这认识才要这东西;而不是他先要这东西然后才说它是好的。从我全部的基本观点看来,这一切说法都是把实际的关系弄颠倒了。意志是第一性的,最原始的;认识只是后来附加的,是作为意志现象的工具而隶属于意志现象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是由于他的意志而是他,而他的性格也是最原始的,因为欲求是他的本质的基地。由于后加的认识,他才在经验的过程中体会到他是什么,即是说他才认识到自己的性格。所以他是随着,按着意志的本性而认识自己的;不是如旧说那样以为他是随着,按着他的认识而有所欲求的。按旧说只要他考虑他最喜欢是如何如何,他便是如何如何了:这就是旧说的意志自由。所以旧说'的旨趣'实际上是在说:在认识之光的照耀下,人是他自己的创造物。我则相反,我说:在有任何认识之前,人已是他自己的创造物;认识只是后来附加以照明这创造物的。因此,人不能作出决定要做这样一个人,要做那样一个人,也不能'再'变为另一个人;而是他既已是他,便永无改易,然后,逐次认识自己是什么。在旧说,人是要他所认识的'东西';依我说,人是认识他所要的'东西'。
古希腊人把性格叫做“埃多斯”,又把性格的表现,亦即生习,叫做“埃德”。这两个词都是从“艾多斯”,亦即从“习惯”一词来的。他们所以选用这个词儿是要用习惯的有恒来比喻性格的有恒。亚里士多德说:“埃多斯(性格)这个词儿的命名是由艾多斯(习惯)来的,因为伦理学这个名称就是从‘习于是’来的。”(《大伦理学》第一卷第六篇第1186页,《倭依德摩斯伦理学》第1220页,《尼柯德摩斯伦理学》第1103页,柏林版)斯多帕阿斯曾引用过这样一句话:“芝诺的门徒把习惯比喻为生命的源泉,由此源泉产生个别行为。”(第二卷第七章)——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我们看到由恩选和非恩选(《给罗马人的信》9,11—24)而来的命运注定说。这一信条所从出的见解显然是:人不自变,而他的生活和行藏,亦即他的验知性格,都只是悟知性格的开展,只是固定的,在童年即可认识的,不改变的根性的发展。这就好象是人在诞生的时候,他一生的行事就已牢固地被决定了,基本上至死还是始终如初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也表示同意,不过有些后果是从这种完全正确的见解和犹太教原有的信条两者的统一中产生出来的,这就发生了最大的困难,出现了永不可解的戈第安无头死结。教会里绝大部分的争论就是围绕这一死结而进行的。这样一些后果诚然不是我想承担出头来主张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即使是使徒保罗本人曾设了一个制钵匠的比喻,也未见得他就真是成功了,因为即令他是成功了,那最后的结果仍不外是:
“敬畏诸神罢,
'你们'人类!
神们握着统治权
在它们永恒的两手。
它们能够——
要如何,便如何!”
可是这样一些考察本来就和我们的题材不相于,更符合我们日的的倒是应对性格和它的一切动机所依存的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作几点说明。
动机既然决定性格的显现,亦即决定行为,那是通过认识这个媒介来影响性格的。但认识是多变的,常摇摆于正误之间,不过一般总会在生活进程中逐渐得到纠正的,只是纠正的程度不同罢了。那么,人的行为方式也就可以有显著的变化,只是人们无权由此推断人的性格也变了。凡是人在根本上所欲求的,也就是他最内在的本质的企向和他按此企向而趋赴的目标,决不是我们以外来影响,以教导加于他就能使之改变的;否则我们就能够重新再制造一个人了。辛乃加说得很中肯:“意欲是教不会的”。斯多噶派倡导“德性是可以教得会的”,但在这问题上辛乃加宁可把真理置于他'所推崇'的斯多噶派之上。从外面来的只有动机能够影响意志,但是这些动机决不能改变意志本身,因为动机只在这人'本来'是怎样的便是怎样的这个条件之下才能对他发生力量。所以动机所能做的一切一切,充其量只是变更一个人趋赴的方向,使他在不同于前此的一条途径上来寻求他始终一贯所寻求的'东西'罢了。因此,教导,纠正了的认识,也就是外来影响,固然能告诉他是在手段上弄锗了,从而使他又在完全不同于前此的途径上,甚至在完全不同于前此的另一对象上来追求他按自己的内在本质曾经追求过的目标,但决不能真正使他要点什么不同于他前此所要过的。前此所要过的保持一贯不变,因为他原就只是'这个“要”,'这欲求本身,否则就必须取消这欲求了。同时,那前者,也就是“认识”的可纠正性,从而也是行动的可纠正性,竟能使他在他企图达到他不变的目的时,可以一会儿是在现实世界,一会儿在幻想世界,并分别为之考虑手段。例如这目的是摩罕默德的天国,那么,要在现实世界达成这一目的就使用机智、暴力和欺骗为手段;要在幻想世界达成这一目的就用克己、公道、布施、朝拜圣城麦加为手段。但是并不因此他的企向本身就有了什么变更,至于他自己本身则更说不上什么变更了。尽管他的行为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很不相同,但是他所欲求的依然完全如故。“意欲是教不会的。”
要使动机发生作用,不仅需要动机已经具备,而且要求这动机是被认识了的:因为依前面曾提到过一次的经院学派一个很好的说法,“动机不是按其实际存在,而是按其被认识的存在而起作用的。”譬如说:要使某人的利己心和同情心的相互关系显露出来,单是这个人拥有些财富,看到别人的穷困,那是不够的;他还必须知道用他的财富可以为自己,又可以为别人做些什么;不仅是只要别人的痛苦出现在他眼前而已,他还必须知道什么是痛苦,当然也得知道什么是享受。当这个人第一次碰到这种机缘时,也许还不能如在第二次的时候那么透彻知道这一切;如果现在是机缘相同而他前后的作法不同,那么,尽管看来似乎前后都是那些情况,其实是情况已有所不同了,即是说有赖于他对此机缘的认识那一部分情况是已经不同了。——'一面是'对于真正实有的情况无所认识将取消这些情况的作用,另一面全是幻想的情况却也能和真实情况一样的起作用;并且不只是在个别的一次幻觉上,而是整个儿持久地起作用。例如说一个人已确确实实被说服了,深信做任何一件好事都会在来生得到百倍的善报,他这信心的功效和作用就会完全等于一张信用昭著的远期支票一样,并且他可以从这自私心出发而施舍,正如他在换了别的见解时又可从这自私心出发而取之于人一样。他并没有变。“意欲是教不会的。”在意志不变的时候,借认识对于行为的这种巨大影响,'人的'性格才得逐渐展开而现出它不同的轮廓。因此,年龄不同,性格也每每不同;随暴躁不驯的青年时代而来的可以是一个沉着的、有节制的壮年时代。特别是性格上的恶将要随年龄而更显著有力;不过有时候青年时代所沉溺的情欲后来又自动被驯服了;但这不过是因为后来又在认识上出现了相反的动机罢了。也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大家在“人之初”的时候都是天真无罪的,而这也不过是等于说我们自己和别人都不能'在那时'看到自己天性上的“恶”罢了。天性上的“恶”是有了动机之后才现出来的,而动机又是随着岁月'的增长'而被认识的。到我们'年高'在最后认识自己时,那已完全是另外一个自己,不同于我们先验地所认为的那个自己了,因而我们往往要为这个自己愕然一惊。
懊悔的产生决不是由于意志已有所改变(那是不可能的),而是由于认识有了变化。凡是我曾一度欲求过的东西,就其本质和原来的意欲说,到现在也必然还是我所欲求的,因我自己就是这一意志,而意志是超乎时间和变化之外的。因此,我决不能后悔我所欲求过的,但很可以后悔我所作过的;因为我可以是被错误的概念所诱导而作出了什么与我的意志不相符合的事,而在'事后'有了较正确的认识时看透这一点就是懊悔。这不仅是对生活上的明智,对手段的选择,对目的是否符合我本意这种判断而言,而且也是对真正的伦理意义而言。例如我可以作出一些过分自私而不符合自己性格的行为,这就是误于夸大地想象自己所处的困难或别人的狡诈、虚伪、恶毒,或是误干燥之过急。而操之过急也就是未加考虑而行动,'行动'不是被在普遍性中明确认识了的动机所决定,而是被直观的动机,眼前的印象和这印象所激起的情
感所决定。这些情感又如此激烈,以致我未能真正运用自己的理性;所以思考的回复在这里也只是纠正懊悔所从产生的那认识,懊悔也就每次都是以尽可能弥补往事而表现出来。不过也得指出有些人为了欺骗自己,故意安排一些操之过急的情况,而实际上却是些暗地里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这是因为我们使用这样细腻的手法,并不在欺骗或奉承别的什么人,而只是为了欺骗和逢迎自己。——此外还可以发生和上述例子相反的情况:对别人的过分信任,对生活资料的相对价值认识不足,或是我已失去信心的某一抽象教条,都可以引导我做出一些事情较少自私而不符合自己的性格,这就又为我准备了另外一种懊悔。因此懊悔总是纠正对行动和本来意图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单就意志要在空间上,也就是要只从形态方面来显示它的理念说,原已为其他理念所支配的物质就不免对这意志有所抗拒——在这里其他理念即各种自然力——,常不让这儿向明朗化挣扎的形态出落得完全纯洁,鲜明或优美。与此相同,要是意志单是在时间上,也就是只以行为显示自己,就又会在认识上碰到类似的阻碍。认识常不以正确的资料根据供应意志,从而行为的发生也就不能完全准确地与意志相符。这就导致懊悔。因此懊悔总是从纠正了的认识中产生的,而不是从意志的改变产生的;改变意志也是不可能的。至于对做过的事发生良心上的不安,这却一点也不是懊悔,而是对于认识到自己本身,亦即认识到作为意志的自己,所感到的痛苦。良心不安正是基于人们确知自己总还是有着原来的意志。假如意志改变了,那么良心不安也就只是懊悔了,从而良心不安也就自动取消了。这因为往事既然是表现着一个意志的某些面貌,假如作出那事的意志已不是懊悔者'现在'的意志,那么往事也就不能再唤起良心不安了。在更后面的地方我们还将详细阐述良心不安'的问题'。
认识作为动机的媒介,虽不影响意志本身,却影响意志的出现为行为。这一影响,由于人禽的认识方式不同,就奠定了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之间的区别。动物只有直观的表象,人由于有理性还有抽象的表象——概念。人虽和动物一样都是以同等的必然性而为动机所决定的,然而人却以具有完整的抉择力而优胜于动物。这种抉择力也常被认作个别行动中的意志自由,其实这并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在几个动机之间经过彻底斗争过来的冲突的可能性,其中较强的一个动机就以必然性决定意志。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动机就必须具有抽象思维的形式,因为只有借助于这种形式才可能有真正熟虑的权衡,即是说才能衡量相反的理由而发为行动。动物则只能在直观地出现于眼前的动机之间进行选择,因此这选择也是局限于它当前直观觉知的狭窄范围之内的。所以由动机决定意志的这一必然性——这是和原因决定后果的必然性相同的——只在动物才可以直观地直接表达出来,因为在这里旁观者也直接目睹这些动机及其作用。在人可不是这样,动机几乎总是抽象的表象,是旁观者看不到的,甚至在行为者本人,动机起作用的必然性也是隐藏在动机间的冲突之后的。这是因为只有在抽象中才可能有好几个表象作为判断和推论联锁而并列于意识之中,不受一切的时间制约而相互影响,直至其中最强的一个压倒了其余的而决定意志为止。这就是完整的抉择力或熟虑的权衡能力。这就是人所以优越于动物的地方。人们就因这种权衡能力而把意志自由赋予人,误以为人的欲求是智力开动的结果,并不需要某种冲动作为智力的基地;而实际上却是动机只有在人的一定冲动的基础上,在人的一定冲动的前提下才有发动的作用。在人,这种一定的冲动是个别的,也就是'人各'有一性格。人们可以在《伦理学的两个根本问题》(第一版第35页起,第二版第33页起)中看到我已详细论述过这种熟虑的权衡能力和由此引起的人禽意向的不同,因此我在这里指出这一段作为参考。此外,人的这种熟虑权衡能力又是属于使人的生存比动物的生存更为痛苦的那些东西之内的,因为我们最大的痛苦根本不是作为直观表象或直接感受而存在于当前的东西,却是作为抽象的概念,恼人的思虑而存在于理性之中的东西;至于逍遥于这些之外的则是只在当前“现在”中生活的,从而也是在可羡的无忧无虑中生活的动物。
上面已论述过人的权衡能力有赖于抽象中的思维能力,也就是有赖于判断和推理。既是使笛卡儿又是使斯宾诺莎走入迷途的好象就是这'“有赖于”的'依赖性,他们把意志的决断和肯定否定的能力(判断力)等同起来。笛卡儿由此引伸而认为不受制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