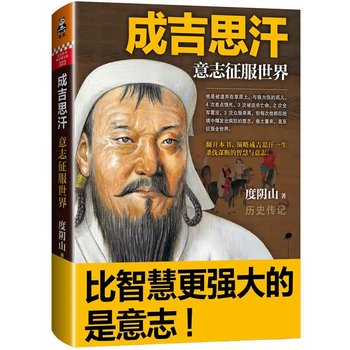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5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它们的羔羊。于是上半幅里人的每一头面,每一姿态,都在下半幅里和有类似情态的动物头面,姿态一一成为对照。这样,人们就看清了,在动物的模糊意识里可能的痛苦感和'所遭'巨创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还可看到真正的痛苦只是由于认识的明确性、意识的清晰性才可能的。
因此我们要在人的生存中来考察意志的内在的、本质的命运。任何人也将容易在动物生命中看到意志的这种命运。不过要黯淡一些,表现的程度也不同而已;并且还可从痛苦的动物界得到充分的证验,证实一切生命如何在本质上即是痛苦。
§57
在认识所照明的每一级别上,意志都是作为个体而显现的。人的个体在无际的空间和无穷的时间中觉得自己是很有限的,和无尽的时间空间相比是一个近于消逝的数量,是投入到时间空间中来的。时间空间既无际限,人的个体也就永远只有一个相对的而决不是有一个绝对的某时某地,个体所在的地点和时间原是无穷无尽中的'极'有限部分。——真正个体的生存只在现在。现在毫无阻碍地逃入过去,也就是不断过渡到死亡,也就是慢性的死。个体的以往的生命,除开对现在有某些后果,除开在过去铭刻了有关这个体意志的证据不论,既已完全了却,死去,化为乌有了,那么,在合理情况下个体就必然要把过去置之淡然,不管那过去的内容是苦是乐了。可是在个体手里现在又不停地变为过去;将来则全不可捉摸,并且总是短促的,所以单从形式方面看,人的个体生存已经就是现在不停地转入逝去的过去,就是一种慢性的死。如果我们现在从形体方面来看个体生存,那么很显然,和大家知道我们'身体'的走着走着只是经常被拦阻了的未即跌倒一样,我们肉体的寿命'活着活着'也只是不断被拦阻了的未即死亡,只是延期又延期了的死亡。最后,我们精神的活跃也只是不断被推迟了的未即闲着无聊。每一口气都在击退时时要侵入的死亡。在每一秒钟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死亡进行着斗争;而在较长的间歇之间则以一日三餐、'夜间'入睡、'时时' 取暖等等为斗争方式。到了最后必然还是死亡战胜,因为我们的诞生就已把我们注定在死亡的掌心中了:死亡不过是在吞噬自己的捕获品之前,'如猫戏鼠'逗着它玩耍一会儿罢了。在这未被吞灭之际我们就以巨大的热诚和想方设法努力来延长我们的寿命,愈长愈好,就好比吹肥皂泡,尽管明知一定要破灭,然而还是要尽可能吹下去,吹大些。
我们既已在无知无识的自然界看到大自然的内在本质就是不断的追求挣扎,无目标无休止的追求挣扎;那么,在我们考察动物和人的时候,这就更明显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了。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除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基地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即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成为他不可忍受的重负。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分。下面这一事实很奇特地,也必然地道破这一点:在人们把一切痛苦和折磨都认为是地狱之后,给天堂留下来的除闲着无聊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
那不断的追求挣扎构成意志每一现象的本质,其所以在客体化的较高级别上获得它首要的和最普遍的基地,是由于意志在这些级别上显现为一个生命体,并附有养活这生命体的铁则;而赋予这铁则以效力的又恰在于这生命体就是客体化了的生命意志本身而不是别的。据此,人作为这意志最完善的客体化,相应地也就是一切生物中需要最多的生物了。人,彻底是具体的欲求和需要,是千百种需要的凝聚体。人带着这些需要而活在世上,并无依傍,完全要靠自己;一切都在未定之天,唯独自己的需要和困乏是肯定的。据此,整个的人生在这样沉重的,每天开门相见的需求之下,一般都充满着为了维护那生存的优虑。直接和这忧虑连在一起的又有第二种需求,种族绵延的需求。同时各种各样的危险又从四方八面威胁着人,为了避免这些危险又需要经常的警惕性。他以小心翼翼的步伐,胆战心惊地向四面瞭望而走着自己的路,因为千百种偶然的意外,千百种敌人都在窥伺着他。在荒野里他是这样走着,在文明的社会里他也是这样走着,对于他到处都没有安全。'有诗为证:'
“在这样黑暗的人生中,
在如此之多的危险中;
只要此生还在延续,
就是这样、这样度过!”
(路克内兹:《物性论Ⅱ》)
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也只是一个为着这生存本身的不断的斗争,并且明知最后还是要在这斗争中失败。使他们经得起这一艰苦斗争的,虽也是贪生,却更是怕死;可是死总是站在后台,无可避免,并且是随时可走到前台来的。——生命本身就是满布暗礁和漩涡的海洋。人是最小心翼翼地,千方百计避开这些暗礁和漩涡,尽管他知道自己即令历尽艰苦,使出“全身解数”而成功地绕过去了,他也正是由此一步一步接近那最后的、整个的、不可避免不可挽救的船沉'海底',并且是直对着这结果驶去,对着死亡驶去。这就是艰苦航行最后目的地,对他来说,'这目的地'比他回避过的所有暗礁还要凶险。
然而现在就很值得注意,一方面,人生的痛苦和烦恼是这样容易激增,以致死亡——整个生命即以在它面前逃避为事——竟406变为人所企求的'东西',人们自愿向它奔去;另一方面,困乏和痛苦如果一旦予人以喘息,空虚无聊又立即如此围拢来,以致人必然又需要消遣。使一切有生之物忙忙碌碌运动不停的本是对于生存的挣扎,可是如果他们的生存已经巩固,他们却又不知道要拿这生存怎么办了。因此推动他们的第二种'动力' 就是摆脱生存这负担的挣扎,使生存不被感觉,也就是消灭时间,逃避空虚无聊的挣扎。这样,我们就看到几乎所有无虞困乏和无忧无虑的人们在他们最后丢了一切其他包袱之后,现在却以他们自己为包袱了;现在是把消磨了的每一小时,也就是从前此全力以赴,尽可能延长的生命中扣除了一分,反而要算作收获了。可是空虚无聊却也不是一件可以轻视的灾害,到了最后它会在人的脸上刻画出真正的绝望。它使像人这样并不怎么互爱的生物居然那么急切地互相追求,于是它又成为人们爱社交的源泉了。和对付其他一般灾害一样,为了抵制空虚无聊,单是在政治上考虑,就到处都安排了些公共的设备;因为这一灾害和相反的另一极端,和饥饿一样,都能驱使人们走向最大限的肆无忌惮。“面包和马戏”是群众的需要。
费城的忏悔院以寂寞和闲着无事使空虚无聊成为惩罚的工具;而这是一种可怕的惩罚工具,已经导致囚犯们的自杀。困乏是平民群众的日常灾难,与此相似,空虚无聊就是上层社会的日常灾难。在市民生活中,星期日代表空虚无聊,六个工作日则代表困乏。
于是任何人生彻底都是在欲求和达到欲求之间消逝的。愿望在其本性上便是痛苦。愿望的达到又很快的产生饱和。目标只是如同虚设:占有一物便使一物失去刺激:于是愿望、需求又在新107的姿态下卷土重来。要不然,寂寞,空虚无聊又随之而起;而和这些东西作斗争,其痛苦并无减于和困乏作斗争。——'只有'愿望和满足相交替,间隔不太长亦不太短,把两者各自产生的痛苦缩小到最低限,'才' 构成最幸福的生活过程。因为人们平日称为生活中最美妙的部分,最纯粹的愉快的,——这又只是因为这种愉快把我们从现实生存中拨了出来,把我们变为对这生存不动心的旁观者了———也就是纯粹的,和一切欲求无关的认识,美的欣赏,艺术上的真正怡悦等,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因为这已要求罕有的天赋——,而就是在这些少数人,这也只是作为过眼烟云来享受的。并且这种较高的智力又使这些少数人所能感受的痛苦要比那些较迟钝的人在任何时候所能感受的都要大得多;此外还使他们孤立于显然与他们有别的人物中,于是连那一点'美的欣赏'也由此而抵消了。至于绝大部分的人们,他们可无法获得这种纯粹智力的享受,他们几乎完全无力享受纯粹认识中的怡悦而是完全在欲求的支配之下的。因此,如果有什么要赢得他们的关心,使他们感兴趣,就必须(这已包含在'兴趣'这个字义里)在某种方式上激动他们的意志,即令只是遥远地,只在可能性中关涉到意志都行,但决不可没有意志的参预,因为他们在欲求中生存远过于在认识中生存:作用和反作用就是他们唯一的'生活'要素。这种本性常常天真地流露出来,人们可从细微末节和日常现象中搜集这种材料,例如他们常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他们游览过的名胜地,因为这地方既不对他们起'什么别的'作用,他们就以此来表示他们对这地方的反应,以此对这地方起些作用。还有,他们也不容易止于只是观看一只来自远方的罕见动物,而必然要去刺激它,狎弄它,和它玩,而这都只是为了感到作用与反作用。在扑克牌的发明和流传上特别看得出意志奋起的那种需要,而这恰恰是表现着人类可怜的一面。
但是不管大自然作了什么,不管命运作了什么:不管人们是谁,不管人们拥有什么;构成人生本质的痛苦总是摆脱不了的;'正是':
“柏立德斯正浩叹,
举眼望苍天。”
又:
“虽是克罗尼德,宙斯的宠儿,
也不免,真正的忧伤,忍痛没完!”
消除痛苦的不断努力除了改变痛苦的形态外,再也作不出什么。痛苦的形态原来是缺陷,困乏,保存生命的操心虑危。如果消除这一形态中的痛苦成功了——这已极不容易——,立刻就有千百种其他形态的痛苦接踵而来,按年龄和情况而交替变换,如性欲、狂热的爱情、嫉妒、情敌、仇恨、恐惧、好名、爱财、疾病等等。最后,痛苦如果再不能在另一形态中闯进门来,那么它就穿上无名烦恼和空虚无聊那件令人生愁的灰色褂子而来。于是又得想办法来消除空虚无聊。即令后来又把无聊撵走了,那么,在撵走无聊时就很难不让痛苦又在前述那些形态中跨进来而又从头开始跳那'原来的'舞,因为任何人生都是在痛苦和空虚无聊之间抛来掷去的。尽管这一考察是这么使人沮丧,我却要引起人们注意这考察的另一方面与此并列,人们从这另一方面可以获取一种安慰,是的,甚至可以获得一种斯多噶派的满不在乎以对付自己眼前的不幸。原来我们对于不幸的不耐烦之所以产生,大半是由于我们把这不幸看成是偶然的,看成是一串可以轻易更换的原因锁链所促成的,因为我们经常并不为直接必然的,完全普遍的不幸,如年龄'日增'的必然性,死亡的必然性以及其他日常的不如意等而自寻烦恼。其实更应该说,使人感到刺的,是看到正在给我们带来痛苦的那些情况具有偶然性。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认识到痛苦之为痛苦是生命上本质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认识到随偶然而转移的只是痛苦用以出现的形式,只是痛苦的形态而不是别的什么,也就是认识到我们现在目前的痛苦只是填充着一个位置,在这位置上如果没有这一痛苦,立刻便有另一痛苦来占领;不过这另一痛苦现在还是被目前的痛苦排拒在'这位置以'外罢了;认识到依此说来,命运在基本上并不能拿我们怎么样;那么,当这种反省思维成为有血有肉的信念时,就会带来程度相当高的斯多噶派的不动心而大可减少围绕着个人幸福的焦虑操劳。不过在事实上很难看到或决不可能看到理性有如此广泛的权限,足以支配直接感到的痛苦。
除此之外,人们由于观察到痛苦的不可避免,观察到痛苦是一个挤掉一个,前一痛苦的下台随即又带来新的痛苦,甚至就可以导致一个似乎矛盾的然而并非不可言之成理的假设,即是说每一个体在本质上少不了的痛苦,不管痛苦的形式是如何变换,而痛苦的定额却是由于个体的天性一劳永逸地被决定了的,在定额之内既不能有所欠缺,也不能超额有余。依此说来,人的痛苦和安乐根本就不是从外面而恰好只是由于这定额,这种天禀所决定的,这种天禀虽然也可在不同的时期由于生理状况'的变化'而经历一些增减,但整个却是一成不变的。并且这也不是别的而就是被人们称为他的性情的东西;或更精确些说,就是一种程度,在这程度上他如柏拉图在《共和国》第一卷所说的,或是情绪昂扬或是情绪低沉。支持这一假设的不仅有大家知道的这一经验:即巨大的痛苦使一切较小的痛苦完全感觉不到了,相反,在没有巨大痛苦时,即令是一些最琐细的不舒服也要折磨我们,使我们烦躁;而且经验还告诉我们:如果有一巨大的不幸,'平日'我们只要一想到它就会战栗,现在果然真的发生了,我们这时的情绪,整个说起来,只要忍过了第一阵创痛,以后也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了。相反也是如此,我们想望已久的幸福到来之后,整个说来和持久下去,我们也就不觉得比前此更显著的好受些,舒适些。只有在变化初发生的那一瞬间才异乎寻常地激动我们,或是作为低沉的苦恼,或是作为昂扬的欢乐激动着我们,但是音乐双方都很快就消逝了,因为两者都是基于幻党的。原来苦乐都不是在眼前直接的享受或创痛上产生的,而是在一个新的将来的开端之上产生的,这开端又是人们在眼前享受或创痛中所预期的。只有从“将来”借支苦乐,音乐才能反常地加强,因而也就不能持久。——还“可引用下面这一观察作为上述假设的佐证,——按这假设,无论是在音乐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