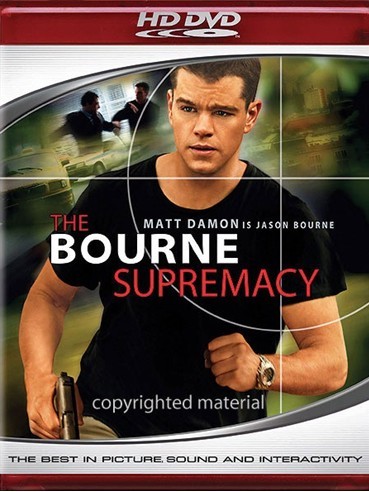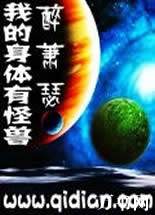伯恩的身份(电影版:谍影重重)-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信你说的?”
“我说过,我们是朋友。她知道我安然无事,也许有点激动,可没事。而且我要她按我的要求去办。”玛丽又停了一下。“她也许认为我对她讲的是真话。”
“往下说。”
“我打第二个电话去的时候她已经拿到了我的衣物。”
“那意味着另外两位代表没有把你的名字告诉警方,不然你的房间准有人看守着不让进了。”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告诉。如果告诉了,我的朋友受到盘问,她一定按照我交代她的话去讲。”
“她在卡里隆,你在河边,你怎样拿到你的东西?”
“十分简单。有点不大雅观,但是很简单。她告诉值晚班的女服务员说我在避开饭店里的一个男人,和外面另一个人会面。我需要衣箱,看她能不能想办法把它交给我。送到一辆汽车里……在河边。一个下了班的服务员把它带给了我。”
“看到你那副模样他不感到惊讶?”
“他没有机会看到任何东西。我打开行李箱,人留在车上,告诉他把箱子放在后面。我在备用胎上放了一张十法郎的钞票。”
“你不只是有条不紊,你简直是了不起。”
“有条不紊就行了。”
“你怎样找到医生的?”
“就在这里。那门房——不知在瑞士是不是这样叫法。记得吗?我已经尽量把你包扎过了,把流血止到最小限度。象多数人那样,我有急救的实际知识,这意味着我必须替你脱掉一些衣服,于是我发现了那些钱,明白了你说的花得起钱找医生是什么意思。你身上美元一大堆。我知道汇率是多少。”
“这只是开始。”
“什么?”
“没什么。”他又试图坐起来。太困难了,起不来。“你不怕我吗?不怕你所做的事?”
“当然怕。可是我知道你为我做了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你比我轻信他人。”
“也许你还没有意识到现在是什么情况。你仍旧很虚弱,而且我有枪,你没有穿衣服。”
“没有?”
“甚至一条短裤都没有。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扔掉了。若是光拴着一条里面装着钱的塑料裤带在街上跑,你会显得可笑。”
伯恩忍着痛大笑,想起了西奥塔和尚福侯爵。“有条不紊,”他说。
“十分。”
“如今怎样?”
“我记下了医生的名字,并且为这房间付了一星期租金。从今天中午起门房开始给你送饭。我将在这里留到十点左右。现在快六点了,天快亮了。我要回饭店去取其它东西同机票。我将尽力避免提到你。”
“若是避免不了呢?若是你被认出来呢?”
“我可以否认。当时那么黑,何况乱成一团。”
“现在你可不是有条不紊了。至少不象苏黎世警方那样有条不紊。我有个更好的办法。打电话给你朋友,请她帮你收拾衣服和结账,钱从我这里拿,要多少拿多少,去赶第一班去加拿大的飞机。在长途电话里抵赖起来比较容易。”
她一语不发望着他,然后点点头。“这办法很有诱惑力。”
“很合逻辑。”
她又望了一会,眼神里露出心情在紧张起来。她转身走到窗口,望着窗外黎明的晨曦。他注视着她,感受到这种紧张,懂得它的原因。他在昏黄的微曦里看着她的脸,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她已经做了她认为必须做的事,因为他把她救出了恐怖,救出了男人无法能真正的理解的可怕屈辱,救出了死亡。而她为他所做的事也完全离经叛道。
她突然把头转向他,张大了眼睛。
“你是什么人?”
“你已经听到他们是怎么讲的。”
“我相信我所看到的!我所感觉到的!”
“不必为你所做的事找理由。做也已经做了,由它去算了,不要去理它。”
不要去理它。噢,上帝,你本可以不要理。本来一切都会安宁。但现在你把我生命的一部分归还了我,于是我又必须去挣扎,去抵抗。
忽然她站到了床尾,手上拿着枪。她把枪指向他,声音颤抖着:“那么是不是我该挽回这一切?是不是我该打电话叫警方来抓你?”
“几小时前我会说请便。现在不能这样说了。”
“那么你是谁?”
“他们说我的姓,伯恩。贾森·查尔斯·伯恩。”
“‘他们说’?什么意思?”
他注视着枪,注视着枪筒的黑色圆环。除了真情再也没有其它可言——他所知道的真情。
“什么意思,”他重复说,“你差不多同我知道得一样清楚,博士。”
“什么?”
“也许让你听听也好。听了,你或许觉得好受些,或许更不好受,我不知道。可你听听也好,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可以告诉你。”
她放下了枪。“告诉我什么?”
“我的生命开始在五个月前,在地中海一个名叫诺阿港岛的小岛上……”
太阳已经升到周围树林的树梢,光线穿过迎风摇曳的枝叶照入窗户,不规则的光影在壁上映出斑驳的花纹。伯恩背靠在枕头上,筋疲力尽。他话已说完;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讲了。
玛丽坐在斜对面一张皮扶手椅上,两条腿弯在下面,香烟和手枪在她左边的小桌上,她几乎不曾动弹过,凝视的目光盯在他脸上,甚至吸烟时眼睛也从不移动,从未离开他那双眼睛。她是一名分析专家,惯于评估数据,过滤事实,好象树林过滤阳光一样。
“你不断说两句话,”她温和地说。“‘我不知道’、‘我要知道倒好了’。你会凝视某些东西,我看了害怕,问你为什么?干什么?于是你又重复说,‘我要知道倒好了’。我的上帝,你经历了些什么?”
“我那样对待你,你还能够想到我的遭遇、我的事情?”
“事情分两条不同的线发展,”她心不在焉地说,皱着眉头深思着。
“不同——”
“根源有联系,但分别发展。那是经济学中的废话……后来,在列文大街,就在我们走上歇奈克的公寓之前,我请求你不要强迫我同你一起走,因为我相信我再多听到些事情你会杀了我,那个时候你讲出了最奇怪的话。你说,‘你所听到的东西对于我跟对于你一样没有意义,或许更没有意义……’我以为你神经不正常。”
“应该说某种神经不正常。神经正常的人有记忆,我没有。”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歇奈克想杀你?”
“当时人没有时间,而且我认为没必要。”
“在那时候没必要——对你。对我有必要。”
“为什么?”
“因为我抱着一种天真的希望,希望你不要对并未先动手想杀你的人开枪。”
“但是他先开了枪。我受了伤。”
“我当时不知道事情的先后。你没告诉我。”
“我不明白。”
玛丽点了一支烟。“这很难解释。你的把我当人质,甚至打我、拖我,还把枪抵着我肚子并顶着我的头——上帝知道,我吓坏了——但是,自始至终,我想我在你眼中看到一样东西,可以称之谓‘不情愿’。这是我所能想出来的最恰当的字眼。”
“可以这样说。你想说明什么?”
“我说不准,也许要追溯到你在‘三家农舍’里说过的一句话。那个胖子走过来的时候,你叫我面对着墙,用手把脸捂起来,‘为了你好,’你说。‘没必要让他认出你来。’”
“是没必要。”
“‘为了你好。’冷血的杀人狂不会说这种话。老想到这句话——也许是为了我自己保持神志清楚。还有你眼睛里的神色。”
“我仍旧不明白你的意思。”
“戴金丝眼镜的人骗我说他是警方人员,说你是残忍的杀手,要在你再行凶之前制止你。若不是出了歇奈克的事,我决不会相信他。那两件事警察都不会干。他们不会在黑暗里和拥挤的地方开枪。而且你是为了逃命——为了活命而逃,不是杀人狂。”
伯恩举起一只手。“对不起,可是听起来你是根据虚假的感恩思想作出判断。你说你尊重事实——那么看看事实吧。我重复一遍:你听到了他们所说的话——不管你认为你看到了和感觉到了什么。长话短说,信封里装满了钱,给我是要我去执行某项任务,这任务是什么应该说很清楚,但是我接受了。在联合银行我有一个数码户头,存款大约五百万美元。从哪里来的钱?象我这样的人,一个有我这些明显的技能的人,从哪里弄以这笔钱?”贾森望着天花板。疼痛又来了,无能为力的感觉也来了。“这些就是事实,圣雅克博士。你该走啦。”
玛丽从椅子站起来,熄灭了手中的香烟,拿起枪,走到他的床边。
“你非常急于谴责你自己,是不是?”
“我尊重事实。”
“那如果你说的是实情,我也有份责任,不是吗?作为社会秩序中守法的一员,我必须打电话向苏黎世警方报告你现在哪里。”她举起手枪。
伯恩看着她。“我本以为……”
“为什么不?”她抢过话头。“你是个该死的人,想了结自己的罪孽,不是么?你躺在那里给自己盖棺论定,可是那口气,对不起,带着不是一点点的自我怜悯,希望博得我的……那个什么?虚假的感恩?好吧,我想你最好能理解一点。我就不会在这里,你也不会。凡是不能被证实的,根本不能称这为事实。你没有事实,只有结论,根据那些你知道是渣滓的人的谈话作出的结论。”
“还有找不到解释的五百万美元银行存款。不要把它忘了。”
“我怎能忘?我一向给人称为财务天才。那存款也许不能按你的方式去解释。可是它的一个附带条款可以提供很大程度的合法性。它可以由一个名叫什么七十一号的公司派人去检验或者拆看。那不可能是一个被雇佣的杀手的附属机构。”
“那公司可能是假名字。查不到它的名字。”
“电话簿里?你太天真了。可还是回过来谈你的问题吧。此刻要不要我去喊警察?”
“你知道我的回答是什么。我不能阻止你,可是不想你这么做。”
玛丽把枪放下。“我不会去,理由同你一样。我同你一样不相信他们嘴里所说的你是什么人。”
“那你相信什么?”
“我对你说过,我拿不准。我真正知道的就是七小时前我被压在一个禽兽下面,他在我身上到处乱吻,双手乱抓……我知道我快没命了。后来,一个人为了我跑回来——一个本来可以逃生的人——可是他为我跑了回来,宁愿替我去死。我相信他。”
“假如相信错了呢?”
“那我就犯了严重错误。”
“请问你。钱在什么地方?”
“在柜子里。在你的护照夹和钱夹里。里面还有医生的名字和房钱收据。”
“请把护照给我,好吗?那是瑞士货币。”
“我知道。”玛丽把它递给他。“我给了看门的三百法郎房钱和介绍医生的两百法郎。医生的诊金总共花了四百五十法郎,我又另加了一百五十法郎感谢他的合作。我总共付了一千一百法郎。”
“不必向我报账,”他说。
“应该让你知道。你想做什么?”
“给你钱回加拿大。”
“我意思是说以后。”
“看我的情况而定。或许该给门房几个钱叫他给我买几件衣服。问他几件事。我不会出事。”他拿出一叠大票交给她。
“这不止五万法郎。”
“我给你添了许多麻烦。”
玛丽·圣雅克看看钱,又看看手里的枪。“我不要你的钱,”她说,把枪放在床头柜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走回扶手椅,转过身来眼望着他坐了下来。“我要帮助你。”
“等一等——”
“不,”她打断说。“请不要问我任何问题,暂时什么也别说。”
第二部
10
他俩谁也不知道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或者到底有没有发生,如果发生了,双方又愿意维持多长时间,加深到什么程度。没有戏剧性的冲动,没有冲突要克服或障碍要排除。全部需要的是思想的交流——语言和目光的交流,同这两者也许同等重要的是频繁伴随它们的轻轻笑声。
乡村客店房间里的生活安排得同医院病房差不多。白天,玛丽料理各类实际工作,衣着、饭菜、地图、报纸都由她照料。她把偷来的汽车开到莱纳哈小镇以南十英里的地方丢在那里,然后乘出租汽车回到连斯堡。她不在的时候,伯恩静心休养和练习活动。从他忘却的过去里,他曾在某个地方学会恢复健康要依靠这两个方面,于是他对两者都按照严格的计划实行,那个地方以前到过——在诺阿港之前。
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交谈,起初有些尴尬,这对萍水相逢却偏偏患难与共的陌生人之间的问答很象辩论,他们进行正常交谈的尝试失败了。因为两人之间本来不存在正常关系。谈话比较顺当是在他俩都接受了关系反常这一基本事实之后。
在这些时刻里,贾森知道了救他性命的女人的基本情况。他抱怨说她对他的了解象他自己一样多,但他对她却什么也不了解。她是哪里蹦出来的?这么一位显然是在农场长大的一头暗红色美发和健康肤色的美貌女子怎么成了经济博士?
“因为她厌恶农场,”玛丽回答。
“没开玩笑?农场,真的?”
“嗯,说小农场更确切些。所谓小是和阿伯塔的大牧场比较而言。在我父亲的时代,法裔加拿大人到西部去购买土地是有不成文的限制的。不要同比你地位高的对手在规模上竞争。他常说,如果他姓圣詹姆士而不是姓圣雅克,今天一定有钱得多。”
“他是个牧场主?”
玛丽笑了。“不,他以前是个会计,可是在战争中驾驶过一架维克斯轰炸机,以后成了牧场主。他是加拿大皇家空军的驾驶员,我猜他在看惯了蓝天之后觉得会计坐的办公室有点乏味了。”
“那需要胆量。”
“胆量不小。他还没买下牧场之前就把在尚未属于他的草地上的不属于他的牛卖掉了。十足的法国佬,人家说。”
“我想我会喜欢他。”
“你会的。”
她同双亲和两个哥哥在卡加里生活到十八岁,然后去蒙特利尔进了麦吉尔大学,开始了她从来不曾料想到的生活。以前她不爱读书,宁可骑上马背在田野里奔跑,也不喜欢坐在阿博特女修道院学校里上课,可此时她发现了使用头脑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