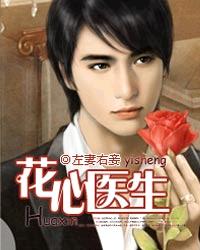心理医生在吗-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谢谢,我自己来。时间到了请告诉我。
已经超过了吗?
真的不在意?那我再继续一会儿?
是的,我父亲。他的善良、软弱、多愁善感是一目了然的。他以咋咋呼呼、哈哈大笑来使别人把他当成相反的一种人,那种对宠辱迟钝的人。大致上就像贺叔叔这样的人。多数人在一两个回合的交往之后发现我爸的致命处。一旦被诘问,他会有个哑口无言的瞬间,一对大眼空白地鼓胀。已自认理屈却要殊死防御。两根女性的弯眉越发倒垂得彻底,显出他不屑再辩解,他气息奄奄地容忍。
比如我妈见他手里的罐头说:你跑哪儿去了?
第一部分 6。心理医生在吗(6)
他当然听出她对额外花销的追究,因此眼珠立刻空白一瞬,理屈词穷地大声回敬:没去哪儿啊,就去了马路对过的食品公司啊!
妈扭头对贺叔叔笑着说:没什么菜呀。
贺叔叔被爸妈关照着朝油烟辣眼的另一间屋走,想起什么,回来拍拍我的头,说:闺女先来。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了解了那个晚餐的真正意味。在当时,那餐饭由于番茄鸡罐头和面目悦然的贺叔叔而显得美味。一个小圆餐桌,上面铺着淡绿绣花台布和玻璃板。一进门你就可以看见妈妈的一个家和爸爸的一个家如何互不相识互不相让地占据着同一个地盘。
我吃到半途,落了一块骨头到地板上。现在我怀疑那不是失手,是存心。需要一个道理离开同一海拔层面,潜入深部。在桌子下面你能看见三个成年人的脚。小时我有看人脚的癖好。我刚才讲到我从我爸的特定站立姿态发现了他时常感到的不自在。此发现不是我在那个年龄就能够诉诸言辞的。我在成长过程中持续观察,持续给这观察以解说。
这个时刻,我在桌下。那块淡绿色小家碧玉的台布,它切割了那三双脚和上身的联系。很暗,我却也不费力地辨出三双脚的紧张和兴奋。我得说我现在用来描述的语言绝对不微妙不够切中要害。英文,更得将就。用〃紧张和兴奋〃形容那些脚只能说是十分十分的将就。朦胧诗人就是在一番对语言的武断性粗浅性彻底失望之后产生的。暂且说这三双脚紧张和兴奋吧。
不必去听台布上面他们在谈什么,他们的笑何等开怀。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个人真正在笑。
笑声从贺叔叔那儿出来时,他那对大而方正的大足趾突然死死扣住鞋底。他穿一双精细草鞋,所有脚趾网在细麻线里,不断与束缚挣扭。
爸爸的脚仍是掌心对掌心,不同平常的是,他一刻不停地颠晃哄拍它们;只要停下颠晃,停在一个不舒适的僵滞上,必定是爸爸在哈哈大笑。
妈妈穿一双黑珠子绣面的拖鞋。那阵子中国在还苏联的债,妈妈常买些便宜而华丽的绣品,从她身上的小腰身绣花衫到淡绿台布和珠子绣鞋,都是国家用去抵债却不合债主的意,给退回来的。妈妈一时把这只脚从鞋中抽出,一时又是那只;不是左脚搭在右脚上就是右脚踩住左脚。偶然地,她会在爸爸腿肚子上踢一下;那秀雅的脚如此识途,迅猛而干练,爸爸那无逻辑缺上下文的哈哈笑声会在挨这一踢时小小冒个调儿。
第一部分 7。心理医生在吗(7)
更有看头的,是三双脚中的一只不当心碰到了异体:贺叔叔赤裸的足趾在他伸展长腿时碰到了妈妈刚脱下珠鞋的脚尖,或者爸爸两个扁薄足掌在动乱无定时出了格局,触到了贺叔叔的草鞋,脚都会电打一般弹开,之后飞快缩回,在空中举一刻,脚尖再探测一番地面的安全范围,最后才缓慢地着陆于自己座位下面。要静很大工夫,才又回到先前的姿势,继续先前的动作。
还是不给那些脚的行为下定义吧。只能原状展示,无法对那番生动进行推敲。也许我的记忆不准确,不能去信任。很可能的,在这三十九年三十九个夏天中它把那个冷却的暮夏黄昏,那个淡绿台布下的激烈场面漫画化了。该这么说,那场面是独立于台布之上的,它是对台布上那个理性舞台的背叛。
只有这么多,至于我爸对贺叔叔的求救,自然在桌布下是不可视的。我妈也在哀求,求贺叔叔动用他的影响、权力,救救我爸。说到救,并不是语意过量,并不是我的英文用字莽撞。我们国家那时随时有性命攸关的事。我们说,政治命运。一个人的名字给黑墨写得很大,劈上两道红墨十字架,这个人的政治生命便结束了。肉体的死,相对而言,是平面的单一的,是无伤大雅无损尊严的。肉体之死是种微不足道的消亡,若你经过政治的死刑。贺叔叔在那次晚餐后救了我爸爸。他劫了我爸爸的政治法场。
是我在十岁以后逐渐听说的。
一点不奇怪。这些事让所有局外人困顿。我们所有的概念是独立于人类心理、行为概念之外的。因为那四十五年伦理规范的独创。我的引言之所以如此冗长。我试过,却见听众眼里两江瞌睡。一个无关人类痛痒的例外。有个人听出眉目来了,对我说:啊,一个小女孩的自淫。小女孩对成年男性荒诞不经的探究;突破禁忌的秘密欲望。其实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找到了你。
舒茨教授给了我一个册子,上面有本市二百多位心理医师的名字。拨一早上电话,只有你声音中有种关怀。你没有张口就问我有没有医疗保险。你的价钱也适合我。
是我们的系主任。我们在约会。
想是见过。六十多岁,该同各个专科的医师有过交道吧。否则他不会建议我来你这儿。
告辞了。这是诊费。九十元。
你答应二十元的折扣。
还行,谢谢。
是吗?其实我并没睡好,不过谢谢。你看上去也挺好。
第一部分 8。心理医生在吗(8)
这是刚才那个小姑娘摆的吗?这儿,把巧克力埋在沙盘里了。她几岁?
比那时的我大一点。健壮多了。那些年里,我飞快地在懂得事情,我只知道贺叔叔是爸爸最好的朋友,常会同爸爸一同回家来。只知道他的妻子是个县长,在一个一夜火车之距的遥远陌生的城镇。只知道贺叔叔不露面的时候是去妻子那儿探亲了。我妈早已不拿贺叔叔当客人,一面同他打招呼一面把一只热水袋继续揣在衣襟下面的胸口。她的病因不明的发冷已深得原谅。他还是伸展双腿从栅栏上一迈而过,直接把我的脑袋搂进怀里,揉一阵。他身心中有那样的快乐。
我必须先告诉你贺叔叔这个人。
我讲过,他个子很大。他玩笑说那是乞来的百家饭催的。他腿上、脚踝都有狗咬的疤;他握着我的手指,去碰过它们。他巨大的一只手把我八岁的手攥住,只留我尖细的食指在外面,使劲而轻微地触碰那浮雕般的伤痕,然后看着我半是恐怖半是恶心的满足。他留一个清爽的发式,一个总存积三两日胡碴的下巴;哪里都显得坚定、快乐。
对了,在一本英文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一页是写他的:十八岁开始扫盲,二十岁成了小说家;他不识字时编的打油诗常常被刊在鲁豫解放区的油印小报上。后来打油诗又成了抗日代表作给印到小学课本里。我印象中的贺叔叔是个太阳。喝多酒他会讲乞丐的故事。他成了八路军的小兵还偷行军干粮给他仍在乞讨的母亲送去。他会忽然一口乡音,眼神温存哀婉。
贺叔叔一生中唯一亲手动笔写的小说《紫槐》就是他和母亲的关系。我是这么猜想。是个非常残忍非常非常罪恶和优美的故事,我会在某一天好好给你讲。
那个时候,我常常猛不丁地,朝正与爸爸低声谈话的贺叔叔瞥去目光,想看清他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他哪一抹神情,哪一个举手投足,哪一束微笑和愁眉中。
贺叔叔和爸爸经常那样低声交谈。有时爸爸在绝望辩解时,贺叔叔会从他方正的衣袋里抽出一叠纸,然后用手指戳点这处那处同爸爸说着。我以后知道了那是我爸爸的一篇杂文,叫做《儿不嫌母丑》。〃儿〃与〃母〃的关系,喻指公民和政党。〃儿〃可以接受丑陋的〃母亲〃,但绝不容忍她的堕落。我爸的眼珠子逐渐空白,焦距彻底散开,希望彻底泯灭。
我一生对我爸的同情都源于此刻。
我十一岁那年,知道了爸爸和贺叔叔究竟是怎样一种朋友。
在贺叔叔同我爸熟识之前,他还在省委负责宣传。一个有权力有名望因而显得极其有力量的男人,也显得性感,以我现在已有了情场世故的眼光去看。权力之一是审查每个作家的政治态度,政治言论。政治言论恶劣的,叫做右派。爸爸那篇《儿不嫌母丑》,尽管语气温良诙谐,但底蕴一目了然,那样的敌意和杀伤力。危险的天赋,在我爸体内。加上爸爸的血统和背景,以及1948年问世于上海的嘲讽短剧。
你已经知道了,会有什么前景。
叫做〃反右倾〃运动,举国动员。
第一部分 9。心理医生在吗(9)
我爸的案情被送到省委。正是贺叔叔一手接过核审的。贺叔叔和爸爸正在接近,彼此生出一种奇异的兴趣。是有陈腐学究家谱的人与草莽秀才之间带一点点猎奇的尊敬。
贺叔叔把那份置我爸于死地的案卷暂搁下来。搁在他抽屉底层,许多天不去开那抽屉。忘却了,或疏忽了。或者想把一个政治徒刑缓期而使我们一家的正常生活稍稍残延。这残延是痛苦的。盼望侥幸也等待诛灭,爸爸一夜一夜不眠,在香烟的雾障中蹚来蹚去。一夜惊醒,见爸妈对坐在昏天黑地里,结伴等待贺叔叔红笔一挥,定个死活。再次醒来,见爸爸弓着腰,飞快抖动腕子在写字。妈妈看着他写,把早就冷掉的热水袋贴在苍黄的脸颊上。爸爸在给贺叔叔写信,写了几十张又忽然决定不写了,写讫的也叫妈妈放在痰盂拿到小院去烧。遥遥地传来早班车的声音,爸写下一行字,请贺一骑有空来吃晚饭。就这样回到我们那个开头,那个晚宴。
我在想贺叔叔的首次登场。大步流星,成熟的日色照在他铜像一样的前额上。那时我并不知道谁来赴晚宴。不知道这个有名望权力的三十岁男人正将他的影响渗进我们的日子,我们本来已有另一番注定的日子。我正写正楷,不知道贺叔叔正朝爸爸和我走来。走过办公楼门外黑黝黝的冬青甬道,走过电影宣传牌楼,上面是苏联电影演员邦达尔丘克,一行大红字:〃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十五周年〃。再走过一大堆烂芦席,那是一条街的大字报栏给台风刮倒,被堆放在这里,下起雨大字报沤化开,周围地面便聚起黑墨和红墨的大小水洼,再往里,是王琛白的巨型雕塑〃革命知识分子〃。巨大雕像矗在凹字形办公楼所形成的院子里,使那院子好多年都没有阳光。有时看见娇小的王琛白满头石膏屑,趴在脚手架上开山凿石般朝雕像挥榔头。都知道它是将要矗立于博物馆门前的工、农、兵之中,因此从来没人认真注视它的进化。贺叔叔想必是站下来看了看它。直到王琛白吓一大跳地叫道:〃贺书记!〃他才笑笑离开。王琛白想必是追着贺叔叔的背影问:〃你看怎么样?贺书记。〃
贺叔叔这时已快走到诗人彭晓夫家门口晒的霉豆腐了。南侧,是条小巷,两边屋檐叠上了边缘,脚步声是有回音的。会在巷子里碰上张帆,有人这样告诉你。张帆是贺一骑书记的前任,在贺一骑上任之前去五里外的包公祠上吊了。大些的孩子们冬天的夜晚躲在巷口,用白丝巾裹住面孔,头上戴一顶蓝呢子帽,突然把过巷者拦住,再把一根裤带提住颈子说:〃我是张帆。〃
走出巷子有个天高地阔的大院,七十二家房客。当中有个井台,正南正北犹如祭坛。蹲着坐着的是主妇或〃阿姨〃们,剥豆、淘米、捶打衣服。井台是没有井的,在我落生于这儿之前井就填了,筑起水泥台子,中间有四个自来水龙头。于是就排起四条接水的队伍。晚饭前这个时间,贺叔叔在缭乱的一排排晾衣绳之间快要迷失了。水分蒸发去了的浅色印花被单给风招摇起来,同色或异色补丁透露给你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家境。这些补丁一半不是真的:太完整太簇新的东西在这个时空里会孤立。偶然见我妈妈拿一块新布在崭新的寝单上设计补丁。我爸非常害怕孤立。
第一部分 10。心理医生在吗(10)
过了井台,食堂那宝塔一样雄伟的烟囱就可以看到了,毛雨天里,两把烟凝成细小黑色的固体,落到院子的杨树叶和柳树叶上。细细的黑色飘降物也落积在大烟囱的自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字黑茸茸一层,那些字看上去像一百年多了。
贺叔叔就这样走来的,左手摆动的幅度比右手大,好像右手还按在曾经佩带过的左轮上。
我和贺叔叔在十来年后会了一次面。他讲起头次到我家的心情。我那时十八岁,远离父母,他也在类似流放的孤苦境遇中。倘若他一生只有一刻的真诚,就是那一刻了。
抱歉我一下子跳跃到另一时空里。
没关系吗?
最后一次?来美国之前。
七年前,他六十好几了。
他摔了一跤,爬起来,发现周围没人注意他。他心事重重地坐到了石台阶上。一个人路过,见这白发老爹抬头看着他说:〃麻烦您送我去医院吧。〃从此他再没了那把象征的左轮和那个步伐,右手抓起一根拐杖。我迎面走到他跟前,对他说我要走了。
怎么也不会忘他那样看着我。
他〃呃呃〃了两声。白发老爹从他的青年和中年只提炼出这一部分,因此现在的他失去了一些质感。对舒茨,我也有类似感觉。
他和贺叔叔绝对不同。不只是种族、文化。
我对他说,贺叔叔,我要去美国了。
他眼睛还很明澈,却映不出那个小女孩来。他想看出小女孩结束在这女人的皱纹里还是眼神里。他对我与他之间的情感跨度恍惚了一下。
我说的是恍惚吗?我是指晕眩。
对一个永不会痊愈的老人,仅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