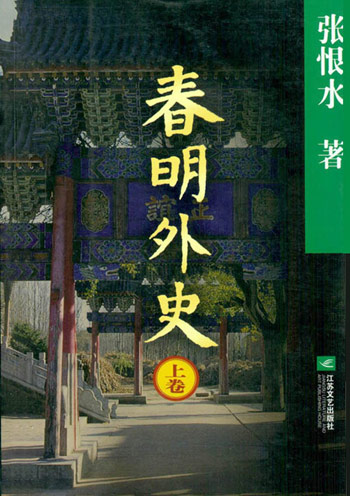春明外史-第17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面沙发椅子上斜躺下。不多一会工夫,就睡着了。醒来时,已经挤了满屋子的人,
何太太和朱伯桐女士也来了。
李冬青和朱韵桐还是别后初见面。都不能有笑容,只是拉了一拉手。朱韵桐叹
气道:“想不到杨先生就是这样下场。前几天我们在西山请客,他也到了,还逗着
我们说笑话呢。”李冬青昨天曾听到何太太说,朱韵桐和吴碧波订了婚,现在她左
一句我们,右一句我们,当然是兼指吴碧波而言。人家多们亲密。也叹了一口气道:
“人生如朝露,真是一点意思没有。我现在觉得他学佛,大有理由在里面了。”何
太太和朱韵桐极力的劝她一顿,她也觉心里宽慰一点,偶然站起来,只见七八个人
吆吆唤唤。抬着一口棺材,直送进里面院子里来。李冬青看见棺材,不由得又是一
阵心酸,泪珠向下直滚。何太太拉着她的手道:“人已去了,伤心也是枉然。你不
要这样闹,苦苦的伤坏了自己的身子。本来呢,大家相处得很好的人,忽然分手起
来,心里自然难过。莫说是你和杨先生象手足一样。就是我们,也觉可……”可字
下还不曾说出,劝人的也哭起来了。那屋子里,何剑尘早已指挥人将杨杏园殓好。
本来用不着等时候,所以即刻就预备人格。吴碧波悄悄对何剑尘道:“入棺时候,
我看最好是避开李女士。不然,她看见把人送进去,格外伤心,也许出什么意外。”
何剑尘道:“这个时候,要她离开这里,是不可能的,有什么法子,让她避开呢?”
吴碧波道:“我倒有个法子。可以把杏园的书件文稿,一齐送到前面屋子里去,请
她去清理出来。就说我们要把他的得意之作,列个目录,登在明日的报上。如此一
说,她必然尽心尽意去清理的。那时候就可以轻轻悄悄把杏园入棺了。”何剑尘道:
“很好很好,就是这样办罢。”于是把话对李冬青说了,还要朱女士何太太二人去
帮忙。
李冬青信以为真,在杨杏园屋子里,搜罗了两篮子文件,到前面去清理。李冬
青认为这事很是重要,仔仔细细的在前面料理。检了约有一个钟头,忽然听到隐隐
有一片啜泣之声。心里一动,忽然想到要到后面去看看,于是就走出来。何太太一
把拉住道:“那面乱七八糟,人很多,你不要去罢。”这样一来,她更是疑心,把
手一摔,向后院子就跑。走进那篱笆门,就看见上面屋中间,用板凳将棺材架起,
许多朋友,围了棺材流泪。几个粗人抬了棺材盖,正向上面盖住。李冬青忘其所以
了,将手一举,乱嚷道:“慢着,慢着。”一面如飞似的就向里面跑。不问好歹,
一头就向棺材头上撞去。何剑尘见她跑进来的时候,情形不同,早就防备着。等她
向前一奔,身子向前一隔,李冬青这一撞,正撞在何剑尘胸口上,把他倒撞得倒退
了几步。何太太和朱女士都赶上前,各执着她一只手,苦苦的相劝。李冬青哭着道:
“何先生吴先生都是朋友呀,为什么不让我和他最后见一面呢。打开盖来啊,打开
盖来呀,我要看一看。”说时,尽管向前奔,别人哪里拉得开。吴碧波拦住道:
“李女士,您别忙,请听我两句话。这话,我也对杏园说过的,就是亲在不许友以
死。李女士这样的苦恼,就不替老太太想吗?见一面的话,原无不可。但是要知道,
不见是可惨,见他睡在那里面,更可惨了。我们都不忍多看呢,况是李女士吗?”
这几句话,倒打入了她的心坎,她把两只手掩住了眼睛,猛然一转身,跑进里面屋
子里去,伏在桌上放声大哭。大家和杨杏园都是朋友,自然都不免有些伤感,所以
李冬青那样哀哭,不但禁止不住,引得各人自己反哭泣起来。混闹了一日,大家都
疲乏已极,一大半朋友,都在这里住下。因为李冬青不肯走,朱韵桐女士也在这里
陪着她。
又过了一天,正中屋里已布置了灵位。棺材头上,便挂了李冬青所献的加大花
圈。花圈中间,是原来杨杏园的半身相片。屋子半空,正中悬了一根绳,挂着杨杏
园自挽的两副对联。灵位前的桌子上,挂着白桌围,上面只有一个古钢炉,焚着檀
香。一只青磁海,盛了一杯清茶。一列摆着四大盘鲜果,两瓶鲜花。李冬青穿了一
件黑布夹袄,一条黑裙子,一身都是黑。蓬蓬的头发,在左鬓下夹着一条白头绳编
的菊花。她本来是个很温柔沉静的人,这样素净的打扮,越发是凄楚欲绝。她不言
不语,端了一张小方凳,就坐在灵位旁边。两三天的工夫,就只喝了一碗百合粉,
两碗稀溜溜的粥,不但是精神颓废,而且那张清秀的面孔,也瘦得减小一个圈圈儿
了。这日下午,何太太自家里来,看见正屋里那种陈设,旁边坐了这样一个如醉如
痴的女子,也替她十分可怜。走进来,李冬青望着她,只点了点头。一手撑着灵桌,
托了腮,依然是不言语。何太太道:“李先生,我看你这样终日发愁,恐怕会退出
病来。今天下午,到我家里去谈谈罢。”李冬青摆了一摆头,轻轻的说道:“我一
点气力没有,懒于说得话,我不去了。”何太太道:“我是天天望您到北京来。好
容易望得您来了,一下车,就到这儿来了没走。我有许多话要和您说,可是一句也
没有谈上。您瞧,我可也门得难受。您就瞧我这一点惦记您的情分,也不好意思不
去。”李冬青明知道她这话是激将法。无奈她说得入情入理,未便过于拂逆。便道:
“不是我不和你去谈谈。但是我丧魂失魄,语无伦次,要我谈也谈不上来的。”何
太太道:“就是因为您精神不好,才要您去谈谈。也好解一解闷。”
李冬青心里虽然十分难受,表面上也不能不敷衍何太太。只得和朱女士一路,
一块儿到何剑尘家去。当时也不觉得怎样,不料在吃晚饭的时候,李冬青手上的筷
子,落在桌上,人已坐不住,就向旁边一歪,倒在地板上。何太太和朱女士连忙过
来将她搀起,只见脸色白里变青,双目紧闭,嘴唇带了紫色。何太太跳脚道:“不
好哟!不好哟!”何剑尘道:“不要紧,这是她两天劳累过分了,人发晕。”就叫
老妈子搀她到床上去安息,一面打电话叫医生来看病。据医生说,也是不要紧,不
过精神过于疲倦,要多休息几天。何剑尘是格外体谅,自己搬到书房里去住,却在
何太太隔壁屋子里,另外设立了一张小铁床,让李冬青在那里睡。
李冬青当天晕倒以后,到晚上八九点钟,也就清醒过来。无如人是累极了,竟
抬不起头来,眼睛里看的东西,仿佛都有些晃动,只好微微的闭着眼。何太太几次
进房看她,见她闭着眼睡着,也就不作声。不过枕头上湿着两大片,她的眼角,也
是水汪汪的。何太太叹了一口气道:“也难怪人家伤心。”说到这个字回头一见她
两颗泪珠流到脸上,就不敢作声了。当时拿了一点女红,就坐在这屋子里做,陪伴
着她。一直做到十二点钟,李冬青才缓缓的睁开眼来。何太太便问道:“李先生要
喝点茶吗?”李冬青摇摇头。“眼睛却尽管望着窗户出神。何太太问道:“李先生,
你望什么?”李冬青道:“很奇怪,我似乎听到有人在窗户外面叫我的名字。”何
太太道:“没有,谁有那么大胆呢?”李冬青道:“刚才有谁进了屋子吗?”何太
太道:“没有。我坐在这里也没有动身。”李冬青道:“那大概是梦了。我看见杏
园走进来,摸着我的额角。他说病不要紧,不过小烧热罢了。他还是那个样子……”
李冬青只见何太太听了,脸色都呆了,只是睁着眼看人。她想起来了,她是害怕,
就不向下说。何太太道:“怎么样,杨先生说了什么吗?”李冬青道:“我看你有
些害怕,我不说了。”何太太道:“怕什么?我和杨先生也熟得象家里小叔子一样。
只因是刚才李先生说话,我也仿佛听见有杨先生说话的声音,所以我听下去呆了。”
李冬青道:“咳!人死如灯灭,哪里还有什么影响?这不过我们的心理作用罢了。”
何太太见她说话渐渐有些气力,就让她喝了一碗稀饭。何太太因为大夫说,李冬青
的病并不怎样重要,所以也不主张她进医院。以为在家里养病,究竟比在医院里便
利,而且也不至于感到孤寂。李冬青自己是精神衰败极了,哪管病在哪里养,所以
静静的在何家养病,关于杨杏园的身后事务,由一班老朋友去料理,并没由她操一
分心。
光阴易过,一眨眼就是十天过去了。李冬青身体已经大好,据何剑尘说,明天
就和杨杏园开追悼大会,要公推李冬青做主祭人。李冬青道:“这是我不容推辞的。
不过我想另外做一篇祭文哀悼他,我要单独的祭一祭才好。”何剑尘道:“李女士
身体是刚好,还要这样去费心血吗?”李冬青道:“我和他的文字因缘,这是最后
的事,我想我就费些心血,也是应该的。”何剑尘想了一想,点头道:“那也好。
追悼会的时间,是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我想把白天的钟点,缩短一小时,李女士
就可以在四点钟另祭。”李冬青道:“缩短时间,那倒不必,就是晚上去祭也好。
我不过表示我对死者的一点敬意,时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何剑尘道:“晚上祭
也好。不过李女士的祭文,不要洋洋万言才好。作得太长了,念祭文的人,恐怕有
些念不过来。”李冬青道:“我想请何太太念一念,何先生答应吗?”何剑尘道:
“那有什么不可以,不过她肚子里的字有限,她能念得过来吗?”李冬青道:“大
概行吧。让我作好了之后,把祭文的大意,对她先讲一讲。她自然会念了。”剑尘
道:“好,就是这样办。我今天下午也不在家。李女士可以到我书房里从从容容去
做。我想李女士这篇文章,一定是很沉痛的,我很愿先睹为快呢。”李冬青却淡笑
了一笑,没有作声。在她这一笑,究竟是哭是笑,也就难说了。
第八十六回 旧巷吊英灵不堪回首 寒林埋客恨何处招魂
这日下午,何剑尘果然避了开去,把书房让给李冬青。何太太把花瓶子里插的
菊花,换了两朵洁白的。又替她沏了一壶极好的清茶,放在桌上。李冬青坐了起来,
先在屋子里坐着,休息了一会,定了一定神。然后走到何剑尘书房里去。自己心里
一腔幽怨,只待机会发泄,祭文的意思,早就有了。所以文不加点的,不到两小时,
就把那篇祭文草就。写完之后,自己看了一看,文意倒还流通,就不更改了。那祭
文道:
维重九之后三日,义妹李冬青,敬以鲜花素果,清茗古香,致祭于如兄杨君杏
园之灵前而言曰:嗟夫!天之处吾二人,何其遇之奇,而境之惨也!吾识兄今才两
年又八间月耳。去年此日,吾人既有生离之怅们,今年此日,更有死别之悲哀。人
生最苦者,厥惟生离死别,而吾与知,只相识二年,只于此二年中乃备尝之。似天
故布此局以待普人之来而匆匆演之以终其场也者。造化不仁,吾欲无言矣。不然,
何其遇之奇而境之惨也?妹之瓣香吾兄,在读兄和梅花诗十首之时。吾诚不知此诗
何以得读之也。假使妹不读此诗,虽见兄犹不见也,则亦无从用其眷眷矣。即读兄
诗,而未有何剑尘君家之一晤,终其身心仪之而已。而又不料兄适为何君之友,致
妹之与其夫人友,而决不能不识见也。妹之于兄,则不过世俗所谓红粉怜才之一念,
何以如此,殆不得言其所以然。而兄之于我,或亦如是,惟其如是,乃足以见吾二
人情谊之笃。妹尝发愚想,必将此事,与死一详尽讨议之。顾犹不得尽除儿女子态,
未能出于口而笔诸书。今欲出于口而笔诸书,又孰能答之,孰可知之者?呜呼!吾
兄英灵不远,聆妹之言、殆亦悠悠而入梦乎?痛矣!妹自知不祥之身,不足以偶吾
兄,更不能与此世界有姻缘之分。故其初也尼友我,则亦友之,兄弟我,更亦师之。
城府不置于胸,形骸遂疏于外。而兄不知,竟直以我为终身之伴侣。妹欲拒之,情
所不忍。妹不拒之,事所不能。迁延复迁延,卒以一别以疏兄之眷眷。兄苦矣,妹
亦未能忽然也。然兄诚人也,其爱人也,而不拘拘于形迹之远近。惟其诚而远,则
思慕愈切。妹不才以凡人视兄,而兄乃以超人之态度待我。妹之去,不仅苦兄,且
不知兄也。兄以我为知己,我乃适非兄之知己,更因非凡之知己,而使妹之知己如
兄者,悠悠然以思,郁郁然以病,昏昏然而铸成不可疏解之大错。妹之负兄,将于
何处求死在天之灵以原宥之?呜呼!亦惟伏地痛哭而已。妹之自知非见之知己,因
非自今日始也。当去秋致书吾兄之后,已自知觉其措置之谬误,遂以古人炼石补天
之言,以为李代桃僵之举,惨淡经营,以为可于异日作苦笑以观其成。乃妹知兄不
拘拘于形迹之远近,而独不悟兄情爱精神之绝不磨灭。愈欲知兄,乃愈不知兄,遂
在兄精神间斧凿无量之创痕。兄之不永年,妹安得不负咎耶?妹之在赣也,为兄熟
计之久矣。来京而后,将如何以陈我之痛苦,将如何以请见之自处,将更如何以保
持吾人之友谊,使其终身无间。且预料妹果言之,兄必纳之,乃于冥冥中构一幻境,
觉喜气洋洋,其华贵如我佛七宝琉璃法座,灿烂光荣,不可比拟。且妹直至长辛店
时,回忆知去年送我之留恋,恍然一梦,以兄乌料有今日更能见我?今故不使已预
闻,及时突然造君之寓,排阔而入兄之书斋。时兄左挥毫而右持剪,栗碌于几案之
间。忽然翘首见我,将为意外之惊异,妹喜矣,兄之乐殆不可思议也。呜呼!孰知
妹之所思者,适与事相背也哉!当妹至何君之家,闻兄小不适,以为兄体素健,年
来劳顿过甚,倦焉耳。乃造兄寓,则见仆役惶惶然走于廊,药香习习然穿于户,是
室有病人,已不啻举其沉重以相告,我未见兄,我已心旌摇摇矣。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