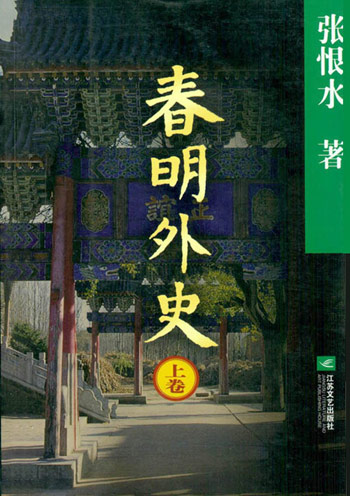春明外史-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子一扭,里面屋子的电灯亮了起来,她就走进里面去换裙子。她回头一看,门帘子
没有放下来,便隔着屋子叫道:“密斯脱李,你进来,替我放下门帘子,免得伙计
乱闯进来。”李吟雨听了厉白的话,当真走进来,把门帘子放下来。只见床上叠着
棉被,把枕头堆得高高的,厉白枕着枕头,仰着半边身子,横躺在床上,一只脚悬
在床沿上,一只脚却伸出去勾床面前那个小方凳子。李吟雨见她勾了许久,没有勾
着,便弯着腰替她把凳子端了过去。厉白看见,伸脚趁势将李吟雨的腰一句,李吟
雨不曾提防,身子往前一撞,脚一滑,上半身便倒在床上,一个脑袋,直伸到厉白
怀里。李吟雨埋怨道:“你这人真是冒失鬼,倘若腰硌在床沿上,那可不是玩儿的。”
厉白一只手按着他的腰,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笑着问道:“我问你,刚才
你在女子改造会,为什么和秦漱石那样客气?”李吟雨被她按着,站不起来,连忙
捉着厉白的手,说道:“摸得人家的脸,怪痒痒的,快别动手,有话好好的说罢。
要不然,我就要胳肢你了。”厉白听了这话,先笑起来,赶快放了手。李吟雨站了
起来,把两只手东指西戳,往厉白脖子上胁下腰下,四处乱揣,厉白在床上把口笑
得茶杯那样大,满床乱滚,两只脚就像踏自行车一样,也是上上下下的乱蹬,口里
不住的求饶。李吟雨道:“你要我饶你也容易,必得叫我一声哥哥,我才住手。”
厉白笑得上气接不上下气,喘吁吁的说:“哥……哥,好……哥哥,这还不成吗?”
李吟雨这才住手。厉白坐了起来,一面理耳朵边的鬓发,一面指着李吟雨笑道:
“你闹得够了,我非重重罚你,不能让你走。”李吟雨道:“罚我什么事,你说。”
厉白道:“罚你和我写两封信,一封写给庞总长,一封写给汪督办。写完信,还得
替我在煤油炉子上熬一锅莲子粥。”李吟雨道:“现在已经七点钟了,再要做这些
事,到了什么时候呢?”厉白道:“不要管他什么时候,反正你不替我做完了,我
不能放你走。”李吟雨没法,只得一样一样替她去做。到了十一点钟,两个人才把
莲子粥,吃下肚去。李吟雨笑道:“现在没有什么事了,可以放我回去吧?”厉白
道:“你要走,只管走。”李吟雨偏着头,斜着眼晴望着厉白笑道:“我还有一件
事要求你,不知道你赏脸不赏脸?”厉白听了这话,眯着眼晴一笑,说道:“你瞧,
这一副骨头!什么要求,这不是废话吗?干脆你就……”李吟雨笑道:“那固然是
一桩事,还有一层,我这两天实在穷得厉害,你若手中方便,务必借十块钱给我使,
等我好去还些零碎小债。”厉白听了这话,猛然伸出手来,揪着李吟雨一只耳朵,
笑着骂道:“你这坏透了的东西,哪回都是这样问我借钱。”李吟雨缩着脖子把两
只手掩着耳朵,嚷道:“哎呀哟,耳朵揪掉了。”厉白道:“别嚷,仔细隔壁屋子
里人听见。”便放了他的耳朵,握着他的手,正色说道:“玩笑归玩笑,说真话归
真话,你若真没有钱用,在我这里再拿十块去,也不算什么。可是我刚才所说,叫
你搬来住的话,你究竟意思怎样?”李吟雨道:“只要能把那边公寓里的账开销清
楚,你要我什么时候搬来,我就什么时候搬来。但是,我很不愿意和你说这句话,
免得你又说我在你面前敲竹杠。”厉白道:“这也很容易,倘若你真欠公寓里的钱,
我明天可和你一路去算账,欠他多少,我替你还他多少,这你也就无话可说了吧。”
李吟雨听了这话,心里想道:“人心都是肉做的。她在外面七拼八凑弄来的钱,我
实在用的不少,对于人家,不能不拿出一点良心来。”心里这样一想,就觉得她的
这张大嘴,也并不讨厌,便又坐下了。和厉白找些闲话谈谈,一直谈到两点钟c再要
走时,共和饭店早已关了门。一宿无话,到了次日,李吟雨只得和厉白一路回公寓
去,把欠账算清。从这天起,他们就实行合作。
当他们实行合作以后,约摸有两个星期,外面说女子改造会的闲言阐语,实在
不好听。谁知就在这个时期,女子改造会,忽然分裂为二。另外成立了一个女子解
放会。女子解放会的会长,正是秦漱石,却与她的好友厉白,处于政敌的地位。外
间看见这种的现象,都十分叹惜,说是政治这样东西,真是参与不得的,连所谓水
做的女孩儿家,一做了政客,也会内哄起来。这话一传到新闻界耳朵里去了,也有
许多人要打听真相,以便揭破外面的疑团。
也是事有凑巧,女子改造会的厉白,这时忽然发出一大批请客帖子,就在会内,
开一个茶话会,招待新闻记者。接到帖子的人,看见上面大书厉白谨订,知道她是
一个异性的时髦人物,无论识与不识,早就愿莅会,瞻仰一番。况且逆料这回招待,
与女子改造会的分裂必定有关,也应该去看看,以便为女子参政历史上,多留一点
材料。所以这日到会的新闻记者,居然有二三十位。一会儿,大餐桌子上,茶点摆
好,厉白穿了一套灰色哔叽衣裙,头发烫的蓬蓬的,擦了一脸的粉,十分素净。走
了出来,站在主席台,对来宾一鞠躬。当时劈劈啪啪,满座就鼓起掌来。厉白便开
口说道:“鄙人今天约诸君前来,蒙诸君惠临,十分感谢。诸君职务很忙,我也是
很知道的,倘若没有不得已之处,也不敢轻于奉请,现在我有一桩事,要求诸位帮
忙,望诸君念我是个弱者,要尽力援助才好。”大家听了这话,都吓了一跳,想道:
“糟了,许是她要藉口会里经费支绌,请我们捐款,或者要我们在报上和她鼓吹,
也未可知。”都在大悔此来上当。厉白接上说道:“我为什么事要求诸位援助呢?
这句话,说来也长,我现在简单的报告诸位。不是别的什么事,就是我的未婚夫,
被人引诱,现在不认我了。”说到这里,嗓音就硬了。那些来宾,高高兴兴而来,
以为厉白必有一番大议论,不料说了出来,原来是这一回事。大家打一个照面,不
好做声,顿时桌子底下,却好像打无线电一样,你敲敲我的腿,我敲敲你的腿,忙
个不了。厉白接上说道,“我的未婚夫是谁?大概在座的人,也有知道的,也有不
知道的。今日我正式宣布出来,他姓李,名字叫做吟雨,本来是我一个同学。我看
见他很好,就和他订交为友。这是两性恋爱的初步,诸君不少个中人,当然是知道
的。”这句话说完,当时就一阵鼓掌。厉白又接上说道:“从此以后,我们感情逐
日进步,就有了婚约。近来我们为合作办事便利起见,并且住在一个旅馆里。无论
如何,我们有了夫妇的关系,是很明白的了。不想我们会里,有一个秦漱石女士,
她竟做这样不道德的事情,实行勾引我的未婚夫。其初我以为他们不过精神上的结
合,还没有肉体上的关系,谁知前几天晚上,密斯脱李却有一晚上没回来,我就有
点疑心。到了第二天一早,他才走了回来,就告诉我说有一桩急事,要十块钱用,
叫我借给他。我说:‘你昨天晚上,准是闹了什么岔子吧?钱是有,你必须说出用
途来,我才能拿出来。’这句话,我原出之无心,以为他或者在外面赌钱输急了,
借了人家的钱,等着要还。谁知他听了这句话,涨得满面通红,赌咒发誓的说:
‘一点儿岔子也没有,因为有朋友住在旅馆里,要上天津去,却因为欠了账,走不
脱身,清早找了我去,干托我,万托我,请我替他找十块钱。我想别处去张罗,也
来不及,所以回来请你通融一下。’我就说:‘你昨晚住在哪儿?’他说:‘住在
朋友家里。’我说:‘住旅馆的人,也认得这位朋友吗?’他说:‘不认得。’我
说:‘这就不对了,住旅馆的那个人,既然不认得你那位朋友,何以知道你住在他
家里,一清早就来找你?’他见我如此说,分辩不过来,只得笑着说:‘老实告诉
你,我也住在旅馆里,怕你疑惑我,所以我这样绕弯儿告诉你。’我听了点点头,
便拿出十块钱来。他正要伸手来接,我说:‘慢点,你这话靠不住,你要告诉我,
是哪家旅馆,多少号房间,我才能给你。’他也没有思索,一口气说出来,是明星
旅馆二十四号。他说完了,我不动声色,将钱交给他,他匆匆忙忙就走了。我等他
出门之后,马上跟了出去,雇了一辆车一直就上明星旅馆。到了旅馆里,我一问茶
房,二十四号有没有一位李先生住在这里?茶房对我看了一看,就说:‘不错,可
是带了太太的?’我说那就对了,茶房便引我走到二十四号房间门口。我在外面,
就听见密斯脱李的笑声,推门进去一看,他正和秦漱石女士坐在一处说笑。密斯脱
李见了我来,脸上像漆了朱砂一样,说不出话来。到后来他反恼羞成怒,质问我追
来做什么。当时就是活菩萨也忍耐不住,是我和他两人吵了一顿,方才回家。谁知
密斯脱李就此变了心,由前日起,就搬着走了,和我脱离关系。诸位都是舆论界的
明星,向来主张公道的。秦漱石这样卖友,李吟雨这样的赖婚,实在是学界的败类,
情场的蟊贼,望诸位对我加以援助,一致声讨。”说着嗓子就一埂,扑扑簌簌掉下
泪来,脸上擦的那层粉,被眼泪洗着,现出一条条的紫痕。加上她的蓬头和那一身
浅灰衣裙,活像一个小寡妇。在场的人,都十分可怜她。厉白将话说完,对在场的
新闻记者,深深的一鞠躬,满大餐桌上,劈劈啪啪,又是一阵鼓掌。大家用了一些
茶点,各自散去。厉白觉得今天所来到的新闻记者,对她的感情,都还不错,心里
比较舒服一点。
厉白雇了车子,自回共和饭店来。茶房开了房门。走进房去,室迩人遐,心里
又生了许多感触。觉得这些男子汉,他对于女子,是专门以貌取人的。你若脸子生
得不好,就挖心给他也是没用。掩上房门,坐在桌于边,呆呆的想。这时,暮秋天
气,院子里的葡萄藤,早已收拾干净,只剩一所空架子。瑟瑟的西风吹了过来,越
发觉得院子空落落的。厉白的房间,和这院子,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纸上有
几个指头大的小窟窿,风在眼里吹了进来,屋子里增了许多寒气。屋顶上,悬着的
那盏电灯,微微的有点摆动。却也奇怪,觉得它的光,今夜都是惨白的。再一看,
砚池是干的,茶壶是冰冷的,满屋子都显得冷清清的。厉白坐在桌子边,正对着一
面梳头镜子,想起这一次烫火发,还是李吟雨帮着烫的。不料他的温存体贴,全是
欺骗我的,自己一味疾心想和他结婚,供给他的衣食,真是冤透了。这一伤心,不
由得又掉下泪来。刚才在会场上流泪,伯把粉洗去了,不能不忍住一点。现在反正
要睡觉了,不必顾虑,就伏在桌子上,尽量的一哭,足足有一个钟头。虽然没有哭
出声来,眼泪抛珠似的流了出来,把脸上的粉洗个干净,一照镜子,脸黄黄的,眼
睛泡也有一点儿肿。正在凝神,猛然间,壁上的时钟,当当响了二下,想道:“时
候不早了,去睡罢!我们江西人有一句话,三只脚鸡公找不到,两只脚老公要几多!
这样忘恩负义的人,我还想他做什么?他虽然用了我几个钱,他也小小心心陪着我
住了许久,我也不上当。我还有许多正经事没有做,何必为这点小事烦恼。”想毕,
脱了衣裳,就去睡觉。
到了次日,厉白起来,想起庞总长那里,几回前去,他都不在家。今天不如趁
个早,前去碰碰看。主意打定,她便换了两件朴实点的衣服,重新擦了雪花膏,照
照镜子,衣服穿得端正了,然后才雇了一乘车于,往庞总长家里来。这天庞总长正
为有特别阁议,一早就走了,厉白又扑个空,好不烦恼c心里想道:“他每天下午,
总要到部里去的,我到部里去找他罢。我虽然是求差事,和别人不同。别人要做官,
无非是想弄两个钱,我们做官,却是为女界参政运动作先锋,是正大光明的行为,
犯不着瞒人。就是到部里去找他,他要嫌太过于公开,我还要把这番话教训他一番
呢。”她自思自想,很觉不错。到下午三点钟,她果然一直到衙门里来会庞总长。
走到门房,她掏出一张名片交给号房道:“我要会你们总长。”号房接过名片一看,
上面写着女子改造会会长,北京学生同盟会干事,爱社总干事,各团体联合会交际
员,妇女周刊社编辑,旅京赣省青年会干事,水灾急赈会会员。还有几行名目,号
房也来不及看,心想她多少有点来头,我且替她上去回一声。便请厉白在接待室里
坐着稍等一等,自己便拿了片子,直送到总长室里去。
庞总长接过名片一看,把眉毛皱了一皱。摇摇头,噗哧的一声又笑了。便吩咐
茶房,对面屋于秘书室里,把舒九成秘书请了过来。舒九成来了,庞爱山将片子递
给他,笑着说道:“这个女学生真是荒谬绝伦。她并没有经过人介绍,前次曾找到
我家里去过一次,见面之后,她就找我要差事。我说:‘我那里并没有女职员,这
却是无法安置,你们年轻,还是安心读书罢。’她却老师长,老师短,叫个不了。
伸手难打笑脸人,叫得我实在没法申斥她。只好说:‘你暂时回去罢,若是少学费
使,我可以替你想点法子。’她才走了。以后她就常常来找我,麻烦透了。”舒九
成道:“总长怎么是她的老师?”庞爱山笑道:“我哪里有这样的学生!只因那华
国大学,我也是个董事,她就硬派我是她的老师了。这回来,大概又是来找差事。
你可以去见她,看她说些什么。”
舒九成答应着去了,便在会客厅里等着,吩咐茶房请厉白。厉白来了,遥遥的
看见舒九成,两脚并立,两手交叉在胸面前,放出娇滴滴的声音,口里叫着老师,
便弯着腰深深的鞠了一个躬。等到走进来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