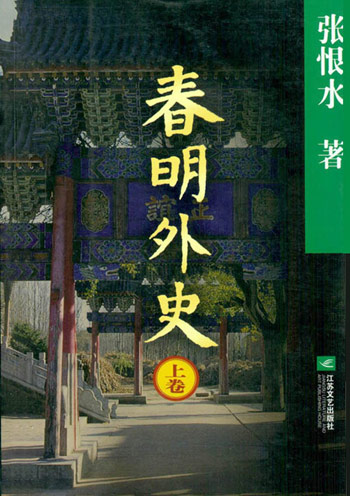春明外史-第4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己在被上坐了一会子,没有洗脸,又没漱口,很不舒服,只得慢慢的穿起衣服,
自行下床。心想幸亏是中寒的病,病得快,好得快,若是病上十天八天,也像这个
样子,不病死也把人烦闷死了。正想走出房去叫胡二,何剑尘却一脚走进来,失声
道:“咦!你却爬起来了,你好了吗?”杨杏园道:“我本想还睡一会儿,要点茶
水,一个人也叫不到,只得爬起来了。”何剑尘道:“我早就劝你搬出会馆,你喜
欢这个院子僻静,老不肯搬。害了病你就感到旅舍萧条的痛苦了。我就去和你叫人
罢。”说毕放下一卷纸,走出院子去了。
一会儿何剑尘转来,杨杏园问道:“那一卷纸是什么?”何剑尘道:“是春联。”
杨杏园笑道:“你还弄这个,太无聊了。不说起来我也忘记时候了,今天是什么日
子?”何剑尘道:“今天是腊月二十三,是送灶的日子了。”杨杏园道:“二十三
了吗?单身做客的人,最容易忘记日子,没有人提起,大概一直到响了爆竹,才知
道过年呢。不过你也太妈妈经了,还闹着贴起什么春联来。”何剑尘笑道:“我原
不要贴的,我们那一位,一定的要办。我想这事也有点趣味,只得弄起来。不过莺
声燕语那些老套头,未免大肉麻,所以又自己做了几副。买了一些纸预备自己去写。
你常告诉我的‘养气塞天地,煮酒论英雄’,我很喜欢它豪放,已把它预定下,算
作堂屋门上的一联了。”杨杏园道:“你大门口的一联如何?我却要看你的标榜。”
说时,胡二送着茶水进来,杨杏园一面洗脸,一面和何剑尘说话。何剑尘道:“很
难着笔。铺张不好,拘谨又不好,我想总以四五言为妙。我现在想了十个字,就是
‘犹守箪瓢乐,幸无车马喧’。不过我嫌它腐一点。”杨杏园洗过脸,端了一杯茶,
坐在躺椅上,听着何剑尘的话,没有做声。双目注视茶里浮起来的轻烟,半天笑道:
“你下面用现成的陶诗,不如上面也用现成的论语,就是‘未改箪瓢乐’罢。”何
剑尘道:“总觉得有些头巾气,不好。你替我想一副罢。”杨杏园呷了一口茶,将
茶杯放下,睡在躺椅上,闭眼养了一会神,说道:“我还不能思索,过了一二天,
再和你拟一联。不过你卧室的一副,我却和你想得了。”何剑尘架着脚坐在那里,
端着茶杯摇摇头道:“这个更不容易,要从大处落墨方妙。”杨杏园道:“‘画眉
恰是生花笔,割肉亲遗咏絮人’。如何?”何剑尘道:“不好不好,一来我不姓张,
二来我又不在总统府当什么书记和侍从武官,一点也不相称。”杨杏园道:“上联
表示你的风流,下联表示你的滑稽,不很合吗?”何剑尘笑道:“这样说你简直是
骂我打我了。我却被生花两个字,引起书房一联,是‘抄诗爱用簪花格,沽酒拚消
卖赋钱。’”杨杏园赞了一声好,说道:“你照样送我一联。”何剑尘放下茶杯,
站起来,背着两只手在屋里踱来踱去,复又坐下去说道:“有了,‘吟诗小试屠龙
手,卖赋消磨倚马才。’”杨杏园笑道:“你这也是骂我打我了。”说着咳嗽了几
声。何剑尘道:“该打,我只顾和你说话,忘记你是一个病人了。”杨杏园道:
“不要紧,痛痛快快的谈话,也很能提起人的精神,比较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发闷,
还好得多呢。”何剑尘道:“我原是没有工夫,因为要看看你的病,所以绕个弯到
你这儿来。明天我们南方人过小年,我叫我们太太亲自烧两样江苏莱,和你作一个
长夜之饮,去不去?”杨杏园道:“谢谢!你们小夫妻在一处浅斟低酌,多么有趣。
夹上我一个插科打诨的有什么意思呢?”何剑尘却再三的说,一定要他去。杨杏园
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以为明天是个小年,我一个人在家里必定会发牢骚。其
实到了岁寒日暮的时候,看见人家一篮一篮的年货往家里拿,随时可以发生感触的,
何必一定限于明日晚上。早几年呢,我确乎是这样,现在外面一个人鬼混惯了,却
不发生什么感触了。”何剑尘知道他的脾气古怪,见他不去,也就不勉强,谈了一
会自去了。
杨杏园一个人在屋子里倒反显得疲倦,饭也懒得吃,也懒起来走动。只买了一
包饼干,躺着喝茶,随便吃了几片。虽然口里说没有什么感触,看见何剑尘正式的
过年,又闹着贴春联,一想起自己的失恋,人家的家庭那样快乐,就不能无动于衷
了。自己也怕越想越烦,便在书架上抽了一本《陶靖节诗集》看,看不到三页,隔
壁院子里,叽哑叽哑,发出一片拉胡琴的声音。那胡琴拉的非常之慢,头两下听去,
好像是六工六,尺工尺。拉到第三下,便停了半天拉一个字。听去老是叽叽叽,哑
哑哑。接上就有人唱:“我本矢,恶弄岗,散淡的伦拉。”听进耳朵去,十分难受。
害病的人,原怕人吵闹,这种初上手的胡琴,好比用铁铲子刮锅煤烟的声音,最是
刺耳。杨杏园皱着眉毛,实在没奈何,这时胡二恰好进来泡茶,他便问谁在拉胡琴。
胡二道:“是徐二先生。’他一听,立时想了个调虎离山计。便道:“你去告诉徐
二先生,说我有一封给苏议长的信,请他来给我誉一誊。”胡二答应着去了,不一
会儿,徐二先生果然来了。说道:“杏园,你好阔呀,居然写信给苏议长了。我就
原知道你们镜报后台的九号俱乐部,是一条好路子。如今果然要望上巴结了。”说
着把手掩着半边脸和嘴,就着杨杏园的耳朵说道:“你写信给他,是不是问他弄几
文过年费?”杨杏园心里想着:“既然骗他来了,若要否认,他一定要恼,不如骗
他骗到底。”说道:“那却不是,只因为他现在要保一大批简往职,和荐任职,我
想要求他在名单上加上一个名字。”徐二先生道:“你和他够得上这个交情吗?”
杨杏园道:“我有一个朋友,和他有交情,我不过托朋友间接说情罢了。”徐二先
生听他是间接的,便道:“我说呢,你哪里会认识他?他家里阔极了,有八个会客
厅。除了一个洋会客厅,专会洋人之外,还有一个内客厅,专门是招待我们院里人
的。有一天我们科长叫我送一封公事去,他就在内客厅里会我。他的记性真好,一
见面,就能叫我的名字。究竟做议长的,脑筋和别人不同。你想我院里,单是议员
就有八百人,若不是有本领的,哪里能认识许多呢?而且他那个人又最客气,待院
里的属员,就像家里人一样。那天还拿了两匣埃及烟出来,亲自递了一根给我。”
杨杏园道:“原来你和苏清叔,有这样好的交情。怎么他不把你的差事升一升呢?”
徐二先生道:“照交情帮忙,本来可以说得过去,然而呀,这里面也有分别。”杨
杏园叫他来,意思原是教他停止拉胡琴,哪管他议长家里什么事。如今见他嘴转不
过来弯来,正好把他的话撇开,便道:“日子真快,今天已是送灶的日子了。你们
快放假了吧?”徐二先生道:“我们放了两天假了。这几天没事,我正想找你教我
填词呢。”杨杏园道:“这个我也不会,我把什么教你!”徐二先生笑道:“论起
作诗,我还可以对付着和你谈谈,填词我实在不懂。我今天在书摊子上买了一部残
的词书,回来一看,老念不上句,念去七个字不像七个字,五个字不像五个字,也
不知押什么韵。我看了半天,一点摸不着头脑,我这就拿来,请你教给我怎样念法。”
说着就去了。一会儿工夫,徐二先生拿了两本书来,交给杨杏园。接过来一看,原
来是两本木刻版的《花间集》。随手一翻,里面掉下两张名片。徐二先生弯腰捡起
来一看,说道:“哎哟,叫我好找呀。”连忙便揣在衣襟里。杨杏园道:“两张什
么东西,这样要紧的收起来?”徐二先生道:“是两张阔人的名片。前天何次长的
老太太生日,我也前去送份子的。吃过酒之后,回头我们就看戏。何次长两位令弟
也在那里,却和我坐在一排椅子上。一谈起来,我中学堂里的老师,也当过他们学
堂里的教员,论起来,我们竟是同学。大家就交换名片。我一看他们的官衔,一个
是存记的道尹,一个是关监督,都是简任职,真是同学少年都不贱了。”杨杏园道:
“你们又没同在一个学校读过书,怎么算是同学?”徐二先生道:“不然,从前同
拜一个老师的,都称为师兄弟。现在我的教员,当过他的教员,和同门拜老师一样,
怎么算不得同学?你还不知道呢,他兄弟两个,和气得很,一见就要我换帖。我想
他们都是简任职,我连一个荐任职还没有巴结上,怎样可以和人家换帖?所以我极
力推辞,不肯奉命。不过他两个人给我的名片,很算得我一种交际上的纪念品,我
就留下来了。”
杨杏园听他说话,一面将书翻着。只见书的总序后面,有半页白纸,上面行书
带草,写了十几行小字。字虽写得极小,但是笔法秀丽,看得很是清楚的。把那段
文字,从头至尾一看,却是一段小跋,写的是:
孟夏日永,端坐多暇,作茧余热,捣麝成尘,顾影自怜,徘徊几榻。因检点旧
笈,收拾残篇,闲取一卷,自遣愁闷。忽得是书,重睹先人手泽。犹忆十三四岁时,
先严赐果案前,抚鬟灯下。常为指点四声,口授诵咏。时窗外月落梧桐,风传蟋蟀,
娇笑憨问,秋漏每尽,一展斯篇,依稀如梦,释卷怃然,不期双袖之湿也。浴佛前
一日,就槐荫窗下,磨陈松烟墨随笔。
杨杏园念了一遍,不觉失声道:“竟是一篇六朝小品,好清丽的文字!”再一
看那段文字下面,印了一颗小图章,是两个篆字。看了半天认出那篆文,是“冬清”
两字。心想看这文和这个印章,一定是个女士了。照我看来,一定还是几十年前的
大家闺秀哩。便问徐二先生道:“你这书从哪里来的?”徐二先生道:“花三十个
子儿,在琉璃厂书摊子上收来的。”杨杏园道:“世上的东西,真是没有一定的价
值。有人爱它,就当着珍宝,没有人爱它,就只值三十个子儿了。”涂二先生不懂
他的意思何在,还想问呢。有人在院子里喊道:“徐二先生在这里吗?”徐二先生
道:“你别忙,我就来,反正和你打起两块头子钱得了。”那人道:“那末,我就
去催他们了。”杨杏园问道:“什么人邀头?”徐二先生道:“说起来好笑,就是
住在隔壁屋子里,刘议员的兄弟刘子善,这一些时逛起来了。昨天晚上,有两个学
生,又带了他去逛二等,怂恿着他快活一夜。他正和哥哥要了几块钱,身上带着六
块,一时高兴,就答应了。那两个就拉他在一边,教他放下三块钱,又教他回去换
一身小衣服再来,刘子善都照办了。回到会馆,他一声不响,自在屋里换小衣。忽
然听到我屋子里的钟,已经敲了十二下。心想往日这时候都睡了,今天还要出去呢。
换衣服的时候,打开皮夹子一看,只剩三块钱。又心想要买好多东西都没买,这样
的花去三块,岂不冤枉?今日若是早睡一刻,就省下来了。越想越心痛,越心痛越
舍不得。就和那两个学生吵着,要去退钱。两个学生被他吵不过,只得和他去了。
那窑姐儿当然不肯,刘子善哭丧着脸,说要告诉他哥哥。两个学生,又怕刘议员知
道了,说好说歹,退回来了两块钱。还差一块钱,两个学生就替他邀一场小麻雀牌,
给他抽头抽出来。我就是四角之一。”杨杏园笑道:“胡说!没有这样的怪事。”
徐二先生道:“你不信,回头我们打牌的时候,你去看一看就明白了。”杨杏园笑
道:“他哥哥刘续,本来是个新补的议员,来自田间,为日无多。他这兄弟,当然
是个老土了。老土花钱,没有舍得的,你说的话,也许可以打对折相信。”徐二先
生道:“说了半天,你还是疑信参半,我不和你辩论了。那里还等着我呢。”说着
自去了。
杨杏园一人坐在屋里,将那本《花间集》打开,见是哀感的句子上,或是用红
笔,或是用黑笔,都圈两个圈。看了这本,再看那本,都是一样。心想这冬青女士,
一定是个伤心人,所以遇到哀感的句子,都表示同情。由此类推,她一定也是个女
词章家了。翻着书,随手打开一页,只见书页里面,夹着一张纸条。条子上写着两
首七绝:
净水瓶儿绿玉瓷,秋花斜插两三枝,
移来意态萧疏甚,相对凄然读楚辞。
霜后黄花不忍看,铜屏纸帐润秋寒,
晚来几点梧桐雨,愁煞灯前李易安。
杨杏园念了两遍,看看那个笔迹,正和那位题跋的冬青女士一样无二。心想道:
“这位女士何怨之深?看她后面一首诗,却是崇拜李清照的,词一定填得好,我来
翻翻看,书里面可还有她的大作。”想着把书乱抖了一阵,却是没有。在睡椅上,
拿着那纸又念两遍,心想“清丽得很,我却做不上来。这样的女子著作,我还不多
见呢。”
他一人在这里想得出神,无如隔壁院子里,哗啦哗啦,那打牌的声音却闹不休。
杨杏园被麻雀牌的声音吵不过,心里很是烦躁。便放下书慢慢的走出来,到隔壁院
子里去。走到刘子善的屋子边,由窗懦朝屋里一看,徐二先生等四个人,正在那里
打牌。那刘子善却背着手站在一边看,杨杏园情不自禁的,也就走了进去。徐二先
生一回头说道:“你是最不愿意走进别人屋子的。怎么来了?”杨杏园笑道:“你
们能打牌,我看一看还不行吗?”说时,这刘子善早客客气气的递过一支烟卷来,
杨杏园接着烟卷道:“我们同住一个会馆,不必客气。’划子善又擦了一支火柴,
递给杨杏园。他只得接过来,燃着烟卷吸了一口。这一吸,不打紧,几乎把嗓子都
呛断了,不由得咳嗽了一阵。这烟味又辣又燥,也不知道是什么烟,拿在手里却不
敢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