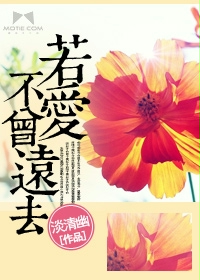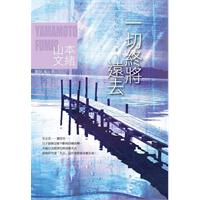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狂人刘文典-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洌捎谌兆邮翟谔蹇啵幸淮瘟跷牡淙滩蛔×耍米诺朗棵遣蛔⒁猓党粤说慊缧龋峁弧ùㄗ×耍至烁龃蠛炝场�
这可能只是个笑谈,但却透显出大学者们〃坐得板凳十年冷〃的辛酸。
胡适版〃明星制造〃
高举〃整理国故〃大旗的胡适,一直在静静观望着刘文典的努力。他预感到,这将是国学领域的一颗〃新星〃。作为旗手,他有责任伸出援手,为这位〃未来之星〃指引方向。
事实证明,没有胡适,就不可能有刘文典的一举成名。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胡适不遗余力的支持,刘文典即便最终能够在国学界树立声名,恐怕也得延迟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刘文典写出了《淮南鸿烈集解》,胡适当然是第一读者。1921年9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刘叔雅(文典)近来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今天他带来给我看,我略翻几处,即知他确然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功夫。〃在同一天的日记里,他甚至不吝笔墨地夸赞道:〃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竟能发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正是在这一天,因胡适的推荐看到了刘文典的这部书稿,因此考虑出版。
尽管在校勘《淮南子》之前,刘文典已经翻译出版过《进化与人生》、《生命之不可思议》等著作,但他毕竟只是个〃学界新人〃,出版界对于他基本上是不怎么买账的。因而从一开始,胡适就充当了刘文典的〃经纪人〃,全权代表刘文典与出版社进行谈判、洽商。刘文典就多次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淮南子》事,既然你这样说,典无有不依〃。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在目前可查的刘文典写给胡适的四十余封书信里,有大量书信都紧紧围绕一个主题:让胡适帮助他与出版社就稿酬讨价还价,或者干脆是直接找胡适借钱。可以说,刘文典对胡适的信赖,是全方位的。
1921年10月16日,刘文典因为校勘《淮南子》购买类书、雇人抄写等用途找学校借了六百元钱,到了快要偿还的时候了,可他的书还未正式出版,兜里没有分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给胡适写信,请他找商务印书馆的大老板张元济(号菊生)说情:〃两三个月薪水一扣,典年内就无以为生了。典想拙作将来销路总不会十分错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张菊生先生商量,垫几百元,总该可望办到。拙作比起平常的书来,费的心血也多些,将来定价也要贵些,并且价值比较的永远些,无论多少年后都可以有销路,究非那些风行'一时'的书可比。先垫一笔款,早迟准可以捞得回来的,典想只要请你和张菊生先生一说,典目下这个围就可以解了。你对于典的事素来肯帮忙,这件事必定可以答应我的。〃
第9节:朋友胡适之(6)
过了几天,刘文典再次为稿酬垫资的事情给胡适写信:〃典因此又起了一个奢望,看起来好像近于'无餍之求',其实和原议相差也不远。就是《淮南子》的垫款六百,加上《印度思想史》的二百,共计有八百元,如果拿二百,就可以凑成一千整数了。〃从刘文典后来写给胡适的信件中看,胡适果然十分热心地为他与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交涉。当年12月初,刘文典收到了商务印书馆预支的稿费支票。
到了后来,由于刘文典未能及时将最后几章校完,商务印书馆始终不肯将剩下的五十元稿费付给他。而北大也一直未能如期发放薪水,刘文典的生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只得再度求助于胡适,〃弟之经济状况已濒绝境,务请你即刻替弟和他交涉一下(打一个电话即成了),我向他开口,实在有些不好,请你援救我一下罢〃。
除了充当〃经纪人〃与商务印书馆周旋外,胡适还逢人说项,毫不吝啬地夸赞刘文典的校勘功力。这让刘文典感到了莫大的鼓舞与温暖。1920年年初,在他刚刚决定进行校勘《淮南子》的时候,许多人听了,不由冷笑,认为这是他异想天开。现在看到胡适如此热情、如此肯定,那些曾经嘲笑刘文典的人〃也热笑着问长问短了〃。
在刘文典的委托下,胡适还专门将他已经校勘好的《淮南子》部分篇章,送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审阅。这其实也是让蔡先生〃重读〃刘文典,消弭刘文典〃不出名〃的尴尬。
1923年2月2日,就在《淮南子集解》(后定名《淮南鸿烈集解》)即将付印之际,刘文典又向胡适提出了新的要求:〃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经全部完成,许多学生们都急于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
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就几乎已经不再用文言文写文章了。刘文典的这个要求,未免有点强人所难。但胡适毕竟是胡适,他略作思考,最终爽然答应了刘文典的要求,〃破天荒〃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言文序言,为《淮南鸿烈集解》擎旗开路。
细读这篇序文,就可以发现胡适的良苦用心。这绝不是一篇随随便便敷衍朋友的〃客套文章〃,而更像是一篇气势磅礴、论证全面的学术论文。他要让这篇序文常留于中国文学史上,这样自然就让〃刘文典〃这个年轻的名字永远留在了文学史上。
在这篇文章里,胡适将尽可能的溢美之词送给了这位与自己同龄,但亟须掌声的北大新派教授。他说,〃今日坊间所行,犹是百五十年前之庄逵吉本,而王、俞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数学人之享用;然则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之先务哉?〃
对于刘文典〃集解〃《淮南子》的〃精严有法〃,胡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凡其所自得有与前人合者,皆归功于前人;其有足为诸家佐证,或匡纠其过误者,则先举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证附焉。至其所自立说,则仅列其证据充足、无可复疑者。往往有新义,卒以佐证不备而终弃之,友朋或争之,叔雅终不愿也。〃总而言之,在胡适看来,刘文典这本《淮南鸿烈集解》的价值,〃读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与方法之严而慎〃,是足以在国学界博得相当声名的。
第10节:朋友胡适之(7)
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学界新人来说,未免有些〃拔高〃。1924年1月1日,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写了篇《读刘叔雅〈淮南鸿烈集解〉》,对刘文典的校勘提出一些补充和完善。十几天后,学界在安徽会馆公开举行戴东原(戴震)诞辰二百年纪念会,杨树达应邀到会,〃余初坐东厢听讲,适之见余,邀往演台,并于彼之作序赞刘叔雅《淮南》书有所辩解,盖见余评刘文字也〃。辩解归辩解,胡适依然觉得,给予学术新人一些必要的奖掖,并不是什么坏事。
1923年3月,正值学术界〃开书目热〃,胡适应《清华周刊》胡敦元等人的邀请,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在〃思想史〃部分毫不犹豫地就将尚在印刷之中的《淮南鸿烈集解》写了进去,并且〃加圈〃重点推荐。
不出胡适的意料,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刚刚走上书市,就引发了〃明星效应〃。就连明确表态〃不赞成〃胡适所开国学书目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在自己为《清华周刊》重新开列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竟也英雄所见略同地推介了刘文典的这本新书,〃《淮南子》,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
鲁迅一向〃主张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或者干脆不读〃,但在听说刘文典的新书正式出版后,也特意跑去买了一套。1924年2月2日的《鲁迅日记》就记载,〃往商务印书馆买《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六册,三元〃。
《淮南鸿烈集解》的确有过人之处。它博采庄逵吉、王念孙、陶方琦、俞樾等众家校注《淮南子》之长,综合宋本、刘绩本、《道藏》本、庄逵吉本、尤本、俗本等优劣,重内证,辨真伪,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对《淮南子》作了校勘与评述,成为近现代学术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伴随着《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刘文典声名大振,一举成名。胡适在后来的代表性作品《中国思想史长编》里,再次不吝笔墨地夸赞了这本书:〃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著最完备,为最方便实用的本子。〃周作人后来评价说,〃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甚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刘文典本人对于这本〃成名作〃也异常看重。《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后,十年间曾三度重印。但是,刘文典并未因此而停歇,继续完善努力。在平常的读书、教学过程中,凡遇到与《淮南子》有关的新材料或新思考,总要记录下来。这些成果在他后来著作的《三余札记》、《宣南杂志》里均有所体现。1948年春天,正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刘文典,趁着课余闲暇,又用红笔将整部《淮南鸿烈集解》重新点校了一遍,留下二十余则眉批文字,都是新的校勘成果,为《淮南鸿烈集解》的传世殚精竭虑。
目前行世的《淮南鸿烈集解》就是由其门生、云南大学中文系张文勋教授根据中华书局版本,结合刘文典的最后校正,增补完成的。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淮南鸿烈集解》的最全善本。
这颗由胡适精心打造的〃国学新星〃,就这样冉冉升起在20世纪初叶的天空中。
〃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胡适是〃红学大师〃,刘文典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受其影响较深,但又不完全拘泥于胡适的研究门路,故而有不少新观点。
第11节:朋友胡适之(8)
听过刘文典《红楼梦》讲座的人,都难以忘记他大谈研究心得时的〃牛气冲天〃,风头完全不亚于今日《百家讲坛》上的〃红学大师〃刘心武:
其时天尚未黑,但见讲台上已燃起烛光(停电之故),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不久,刘文典先生身着长衫登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先生从容饮尽了一盏茶,然后霍然起立,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这段文字是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的学生马逢华留下来的,他曾亲耳聆听过刘文典的《红楼梦》讲座。据他说,当天晚上的那场讲座原本是准备在一个小教室开讲的,后来由于要求来听的人实在太多,只得改在了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广场上举行。即便如此,讲座还没开始,广场上就已经坐满了人。由此,刘文典在〃红学〃研究方面的声望,可窥一斑。
刘文典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最早文字,就与胡适有关,始见于1922年2月22日他写给胡适的一封信。这也是目前可查的刘文典关于〃红学〃的唯一文本记录。在这封信里,刘文典表达了对于胡适〃新红学〃思想的认同:
今天在《晨报》的副刊上看见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间接看着了你对于这部书的批评,心里十二分快活。典对于这部书的意见,完全和你的一致。你对于众人所认为〃句皆韶夏,言尽琳琅〃、〃徒警其浩旷,但嗟其峻极〃的著作,能下这样严格的批评,真有仲任问孔、子玄惑经的气概,这一层实在令典对于你生无限的崇仰心啊!
信中提到的〃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实际上是蔡元培〃驳斥〃胡适关于《红楼梦》研究观点的一篇商榷文章,写于1922年1月30日,发表于1922年2月21日和22日的北京《晨报》副刊上。
在《红楼梦》研究领域,蔡元培是典型的〃索隐派〃,代表作是初版于1917年的《〈石头记〉索隐》。在这部著作里,蔡元培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观点:〃《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在他认真而细致的〃索隐〃之下,贾宝玉成了康熙朝的太子胤礽,林黛玉成了清朝名词人朱彝尊,薛宝钗成了康熙朝的宠臣高士奇,如此等等。一部《红楼梦》,就这样变成了一部《康熙王朝秘史》。
胡适从一开始就不赞同这种牵强附会的研究方式。1921年3月,他写出了平生第一篇〃红学〃文章……《〈红楼梦〉考证》,后来又补充了一些新发现的材料,于当年11月写成了《〈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
一上来,他就直接指出〃索隐派〃的路走错了:〃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在这篇〃战斗檄文〃里,胡适甚至没有〃放〃过自己所在大学的最高负责人……北大校长蔡元培,〃我总觉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第12节:朋友胡适之(9)
对于胡适的这些批评言论,刘文典还是比较认同的。这不仅仅缘于他与胡适之间的特殊关系,更出于他对《红楼梦》独到的视野与观察。尽管他并不完全赞同胡适考证认为《红楼梦》就是曹雪芹〃自叙传说〃的说法,但他非常拥护胡适提出的〃新红学〃的研究方法,〃它原是传统学者们所习用的,这便叫做'考证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