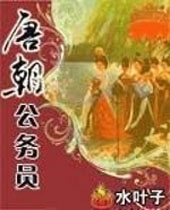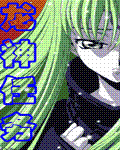为人民服务-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白纸的主角。吴大旺并不为刘莲模糊的回答感到过渡吃惊和不可理喻,只是自己明明知道
事情必然如此,可又总是在内心里的某一瞬间,幻化出不可能的美好景像,往往以这种幻化
去取代对未来实在的设想。而现在,两个人的泪水都流了许多,谁也不会怀疑彼此献给对方
的某种真诚里有太多的虚假,只是在面对现实时,都不得不从浪漫中退回到日常的实际中来。
为了在现实的无奈中挽住刚才那动人的时刻和彼此对爱情真诚憧憬的美丽,吴大旺变得
有了些学生们那不甚成熟的深沉模样。他从地上站了起来,后退几步坐回到了桌边的椅上,
一如刚才样深情脉脉地望着没有原来神圣却和原来一样引逗人心的刘莲,有几分倔犟地说,
刘姐,不管你对我咋样,不管你和师长离不离婚,给我提不提干,调不调我媳妇、孩子进城,
我吴大旺这一辈子都在心里感激你,都会在心里记住你。
显然,吴大旺这几句内心的表白,没有收到他想要收到的效果。刘莲听了这话,又一次
抬头庄重地望着他,默了片刻,在床沿上动动坐僵了的身子,笑了一下说,小吴,你的嘴变
甜了,知道哄你姐了。
吴大旺就有些急样,睁大了眼睛,说你不相信?
她像要继续逗他似的,说对,鬼才相信。
他就更加急了,又无法证明自己内心的忠诚,便左看右看,最后把目光落在地上被他弄
碎后、又用脚拧碾成末粒的毛主席的石膏像粉,说你要不信,可以随时去保卫科告我,说我
不光弄碎了毛主席像,还用脚故意碾碎这像的石膏片儿。说你告了我,我不是被枪毙,也要
去监狱住上一辈子。
刘莲便看着急出满头汗水的吴大旺,还用脚踢了踢地板上的石膏像粉,可抬起头时,她
的脸上变得有些坚毅,一本正经。
她望着他说,小吴,你忘不了我,你以为我会忘了你吗?
他说,你是师长的媳妇,你忘了我,我也没法儿你呀。
她就忽地从床上坐起,瞟了一眼桌里墙上贴的毛主席的正面像,猛地过去一把把那像从
墙上揭了下来,在手里揉成团儿,又撕成碎片,甩在地上,用脚踩着跺着,说信了吧?信了
吧?不信你也可以去保卫科告我了,我们两个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我们两个都
弄碎了毛主席的像,我们谁告了谁,谁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了,可你是无意弄碎了毛主席的
石膏像,我是故意撕碎了毛主席的像,我是大反革命分子,你是小反革命分子,现在,你吴
大旺信了我刘莲一辈子心里有你的话了吧。
她极快地说着去看他,却看见他脸上被她的举动惊出的一脸苍白。显然,他不仅信了她
的爱情表白,而且还被她自己把自己送上大反革命分子的舞台的举动所震憾和感动。为了向
她进一步表白自己爱她更胜过于她爱自己,吴大旺扭身把脸盆后边墙上挂的毛主席语录撕下
来,揉成团,又踏上一只脚,说我是特大的反革命分子,要枪毙该枪毙我两回呢。
她就在屋里四处找着看着,看见了放在写字台角上的红皮书《*** 选集》,上前一步,
抓起那神圣的宝书,撕掉封皮,扔在地上,又胡乱地把《*** 选集》中的内文撕撕揉揉,最
后把宝书扉页上的毛主席头像撕下来,揉成一团,踩在脚下,盯着他说,到底是你反动还是
我反动?
他没有立马回答她的问话,而是瞟了一眼凌乱的屋里,几步走出卧室的屋门,到楼梯口
的墙上,摘下那块上边印着林彪和毛主席的合影、下边写着大海航行舵手的语录的彩色镜框,
一下摔碎在地上,又弯腰在地上用指甲狠狠抠掉那两位伟人画像上的眼睛,使那张伟人的合
影上,显出了四个黑深的洞穴,然后直起腰来,望着屋门里的她说,刘姐,你能比过我吗?
她就从屋里走了出来,说了一个能字,快步走到挂有许多地图的师长的工作室里,气喘
嘘嘘地搬出了和真人大小不差多少的一尊镀了金色的毛主席的半身塑像,而且手里还拿着一
个精美的小锤,把那金色塑像摆在吴大旺的面前,用锤子一下敲掉了塑像的鼻子,使毛主席
那金色的脸上,露出特异的泥色。她不去看那泥色,也不看吴大旺的脸色,自顾自地问到,
我比不过你吗?又敲掉了毛主席一只耳朵,说我比不过你吗?
他不答话,不知从哪弄来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一颗钉子,到她面前用锤子把那钉子砸到
了那像章上的鼻梁里,叮当的声音,像砸着毛主席牙齿一样,砸完了,他抬头望着她,算是
对她做了回答。
他们就这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青出于蓝胜于蓝,比赛着穷尽自己的智慧在圣物上
做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毁灭,以亵渎的程度来表达自己对对方那神圣到怪异的情感和爱情,
直至黄昏又一次悄然到来,彼此都在二楼找不到毛主席的像、书和语录,还有凡是印有毛主
席最高指示的器物儿,两个人就从二楼下到一楼里,她又从墙上摘了三块毛主席的语录牌,
在语录牌上抹了锅灰,还在*** 的三个字上都又打了粗重的红叉。
他从哪儿找了四本毛主席的书,把那书纸揉撕以后用小便浇了上去,和便纸一道扔在厕
所的纸篓里。她将一把每根上都印有最高指示的筷子全都折断扔在了垃圾斗。
他把印有毛主席头像的味精瓶子找出来,把味精倒在一个小碗里,在那味精袋里装了一
袋灰垃圾。
她就又开始翻箱倒柜,挖地三尺去找那些神圣庄严的器物儿,到末尾实在找不到时,她
在厨房站了站,想一会,到餐厅就抓起了餐桌上那块曾经成为他们情爱见证的为人民服务的
木牌子,举起来要往地上摔着时,他上前一步捉住了她的手,一把把那木牌夺下来,又小心
地放在餐桌上。
她说,小吴,这可是你不让我把它摔个稀巴烂。
他说,对,我要留着它。
她说,留它干啥呀?
他说,不干啥,就想留着它。
她说,那你得承认我是天下第一的反革命,最、最、最大的卧藏在党内的女特务,埋藏
在革命队伍中威力无比的定时炸弹,得承认我刘莲爱你吴大旺胜过你吴大旺爱我一百倍。
他就说你是天下第一的反革命,最大最大的卧藏在党内的女特务,埋藏在革命队伍中威
力无比、胜过轻弹、原子弹十倍的最大的定时炸弹。说你喜爱我小吴胜过我小吴喜爱你一百
倍,一千倍,一万倍。
说完了,他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她,彼此的眼里又都有了深情而意味深长的泪。
第七章
那一夜,他们就睡在那一片神圣的狼藉上,连前所未有的淋漓快活的爱情之事,也是在
地面的一片狼藉上顺利地进行和完成。然在极度的快活之后,随之而来的疲劳和饥饿,如同
暴雨样袭击了他们。他们很快就在疲惫中睡了过去,然后又被饥饿从梦中叫醒。吴大旺去为
她和自己烧饭时,发现屋里没有了一根青菜,这就不得不如同毁掉圣像样毁掉他们那七天七
夜不开门出屋的山盟海誓。好在,这已经是了七天七夜的最后一夜,离天亮已经不会太久。
他知道她还在楼上睡着,想上去穿条短裤,到楼后的菜地拨些菜来,可又怕挠乱她的睡
意,也就那么赤裸着身子,慢慢开了厨房后门的暗锁。
打开屋门时,月光像一块巨大的玻璃,哗的一下砸在了他的身上。吴大旺没有想到,月
亮也会有这么刺眼的光芒,他站在门口,揉了揉眼睛,又眯着双眼抬头朝天空望着。凉爽的
细风,从菜地朝他吹来,空气中湿润的清香和甜味,争先恐后地朝他的鼻腔里钻。他张开嘴
巴,深深地吸了一口夜气,还用那夜气,水一样在自己身上洗了两把。抹掉了胸前身上的许
多石膏像的灰粒和书纸的屑片儿,他开始慢慢地踩着田埂,往他种的那两畦儿大白菜的地里
走去。累和疲劳,使两腿软得似乎走路都如了辫蒜,可吴大旺在这个夜晚,还是感到无比的
轻松和快活。内心的充实,如同装满金银的仓库。
吴大旺已经不再奢望什么,满足感长城样码满他的血液和脉管,使他不太敢相信这段绝
妙人生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不敢相信,他会七天七夜不穿衣服,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和往
常他见了都要低头、脸红的师长的夫人足不出户,相厮相守,如守在山洞里的食草野人。
坐在那两畦白菜地的田埂上,他很想回去把刘莲也叫来坐在那儿,共享这夜空下一丝不
挂的美妙。可却是终于坐在那儿一动未动,独自做了静夜的主人。七天七夜的足不出户,使
他近乎死亡对鲜活的自然的贪恋获得了新生。
可他不知道正有一场爱情的变故,如同河道的暗流一样藏在他的身后,不知道今夜过后,
他和她的爱情,就要嘎然休止。一个寒冷刺骨的冬天,早已在不知不觉间,尾随在了夏秋之
后。寒冷的埋伏,如同冬眠的蛇,惊蛰以后,它将抬头出洞,改变和影响着他的生活、命运,
乃至整个的人生。
命运中新的一页就要揭开,情爱的华彩乐章已经演奏到关闭大幕的最后时刻。随着大幕
的徐徐落下,吴大旺将离开这一号院落,离开他心爱的菜园、花圃、葡萄架、厨房,还有厨
房里仅存的那些表面与政治无关,没有语录、伟人头像和革命口号的锅碗瓢盆、筷子菜袋。
而最为重要的,是要离开已经完全占满他的心房,连自己的每一滴血液,每个细胞中都
有她的重要席位的刘莲。现在,他还不知道这种离别,将给他的人生带来何样的变化,将在
他内心的深处,埋下何样灵魂苦疼的伏笔。不知道关于他的故事,将在这里急转直下,开始
一百八十度的调向发展。不知道人生的命运,总是乐极生悲,在短暂的极度激越中,总是潜
伏着长久的沉寂;在极度快活中,总是暗伏着长久的悲伤。
他不知道这时候刘莲早已出现在了他的身后,穿了一件浅红短裤,戴了她那乳白的胸罩,
静静地站了一会,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楼里,拿出来一条草编凉席,还拿了一包饼干,
端了两杯开水。这一次从屋里出来时,她没有轻脚蹑步,而是走得松软踢踏。当她的脚步声
惊醒他对自然和夜色贪婪的美梦时,他扭过头来,看见她已经到了近前,正在菜畦上放着那
两杯开水和饼干。
他想起了他的职责。想起来她还在楼里等着他的烧饭。他有些内疚地从菜地坐起来,轻
声叫了一声刘姐,说我一出来就给忘了呢,说你想咋样罚我就咋样罚我吧。说没想到这夜里
月亮会这么的好,天也不冷不热,凉快得没法儿说。
没有接他的话,没有在脸上显出不悦来。她脸上的平静就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样。不消
说,在他不在楼里的时间里,她已经把自己的身子重新打理了一遍,洗了澡,梳了头,还在
身上擦了那时候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从上海买到的女人们专用的爽身粉。她从那楼里走出来,
似乎就已经告别了那惊心动魄的七天七夜。似乎那段他们平等、恩爱的日子已经临近尾声。
她还是师长的女人,杨州城里长成的漂亮姑娘,这个军营、乃至这座城市最为成熟、动
人的少妇。尽管她只穿了一条短裤,但已经和那个七天七夜不穿衣服,赤身裸体与他性狂疯
爱的女人截然不同,判若两人。她后天的高贵,先天的动人,都已经协调起来,都已经成为
她身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她没有说话,到白菜地的中央,很快把还没最后长成的白菜拨
了十几棵,扔在一边,把凉席拿来铺上,又把饼干和两杯开水端来摆在中央,这才望着他说,
小吴,你过来,先吃些饼干,我有话要给你说。
他惊奇她身上那不易觉察的变化,比如说话的语调,而不是她穿的粉红的短裤,戴的乳
白的绣花乳罩。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忽然间,他在
她面前变得有些胆怯起来,不知是怕她,还是害怕那发生过的什么事情。他望着那先自坐在
凉席上的她,想要问她什麽,却因为某种胆怯和惊恐而没说出一句话来。
她平静地看了看他,像一个老师在看一个将要放假回家的学生,又问他说,小吴,你在
这儿呆着,听没听到电话的铃声?
他朝她摇了一下头。
她便极其平静地说,师长的学习提前结束了,明天就要回来,这是你和我在一块儿的最
后一夜了。
她的话说得不轻不重,语调里的真诚和悲伤,虽不是十二分的浓重,却也使吴大旺能够
清晰地感受和体会。直到这时候,月亮已经东移得距军营有了百米百里,远近无法算计,寒
凉也已渐渐浓烈地在菜园中悄然降临,连刘莲嫩白的肌肤上都有了薄薄的浅绿淡青,肩头、
胳膊上都已生出一层鸡皮疙瘩来,他似乎还没有明白刘莲的话的真正含义,只是觉得天是真
正凉了,他要和她一样在身上穿一件衣服该多好。想到衣服时,他身上不合时宜地打了一个
寒颤,他就母亲样把他拦在怀里,说你明天回去看看老婆、孩子,在家多住些日子,由我给
你请假,没有你们连队去信、去电报,你在家里住着不要回来。然后又问他说,小吴,坐过
卧铺没有?天亮我就打电话让人去给你订卧铺票;上午十点,你到火车站门口,那儿会有人
等着给你送一张卧铺票,还有开好的军人通行证。
说完这话时,菜地里浓郁的菜香和黄土在潮湿中的浓郁的土腥味,伴着一声晨早的鸟叫,
从他们身后传了过来。天是真的凉了,吴大旺在她的怀里又打了一连串的寒颤,
第八章
吴大旺回他的豫西老家休假一个多月又回部队了。
在一个多月的假期里,他仿佛在监狱里住了四十余天。不知道师长回来以后,刘莲身边
都发生了什么难料之事,有何样的意外的在发芽与生长。不知道部队拉练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