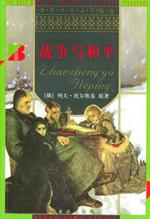战争和人-王火-第16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叫韦鲁斋,是他亲信,我认识。我去给他打个招呼,他准会代表‘汤屠夫’请你吃饭,甚至请你到 叶县去逛一逛同汤见面,然后送上盘缠为你饯行派车将你送到洛阳或西安。那多方便!见你带了公子与寻常百姓一样起早赶路,我心里很不是 味。今晚你们好好睡一觉,这事明天交给我办就是了!”说着,给大家搛菜。
听他这样说,童霜威心情激荡开来了。本来,未始不想公开身分,找找熟人,弄辆汽车上路,既快又稳,自己身体又不太好,比在酷暑天 气里步行起早要舒适迅速得多。但听了刚才褚之班的一番谈话,心里对汤恩伯之流十分反感,觉得再上门去找他未免可耻,甚至自己又有了一 种新的想法:脱离大后方已久,在沦陷区里,一直闭塞。现在既要到重庆参加抗战,理应多看多听多了解。在这一路上,与柳忠华和家霆做伴 ,广广见闻,亲眼看看,亲耳听听,未始不是好事,何必去乞求汤恩伯之流给一杯羹?因此,对柳忠华说:“忠华,我想,还是不找他们派车 送的好。你说呢?”
柳忠华放下汤匙,连连点头,说:“对对对,不去麻烦他们的好。这一路,虽然艰苦,我们和家霆看看,都有好处。”
家霆吃着饭也说:“我也愿意走走。”他这一路上已经走出滋味来了,觉得人生行万里路也像读许多本无字的书,听褚之班讲了汤恩伯的 种种,完全能理解和尊重爸爸的心情。
褚之班是了解童霜威脾气的,看童霜威的表情和语气,又听了柳忠华和家霆的话,明白童霜威是不会让他找韦鲁斋的了,不等童霜威开口 ,尴尬地笑着说:“秘书长,我是一片好心!大热天,从此地去洛阳,足足七百里。他们俩年轻,你哪能经得起折腾。再说,从去年到今年, 大水大旱,蝗虫为害,灾歉之年,战争又加重了天灾人祸,老百姓倒了穷霉,路上也不太平。我们学法的人容易清高,其实众人皆醉,惟我独 醒又何济于事?你若是不吃他们的饭,不去叶县,我都可以跟韦鲁斋打招呼。可是,汽车,叫他们派一辆,那又有什么?”说完,又动筷给三 人搛菜。他是吃过晚饭喝过酒的。陪着吃饭,目的就是给大家敬菜。
童霜威明白褚之班确是好意,心里也深受感动,诚恳地说:“之班,不必了!我还是一路看看听听的好。我到重庆,人家一定要问我一路 上的观感,得便我倒想谈谈亲耳所听、亲眼所见。”他看看柳忠华和家霆又说:“路上,好在有他俩照应,不会成问题的。我把此行当作一次 考察,机会难得。我决心已下,今天打扰一夜,明晨就走!”
褚之班看着童霜威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发红的脸,又看看他花白的头发和胡髭,听了童霜威的话,他觉得童霜威身上有了些变化。是什么变化 ?还辨别不出,但确实是一种变化。他似乎颇有触动,一时竟无言对答。最后,才十分恳切地说:“唉,暑热袭人,你也上了年岁,身体又有 病,那,无论如何,也该在我这里休息几天再走!人生难得这样的重逢,也许今后就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四
在界首休息了五六天。离开界首,童霜威、柳忠华和家霆三人,仍雇了辆高架车拉物件,起早步行,千辛万苦,一个多星期后,终于在夜 晚到达离洛、阳七十里的彭婆镇,住进了一个兼卖甜面条和咸面条的小客店。
所谓甜面条,是白水煮面条;所谓咸面条,是白水面条里加点盐加几滴油。
彭婆镇是个穷苦落后的小镇。一条破旧的街道又窄又小,房屋破旧,没有什么市面。夜里黑灯瞎火,有些人家点的油灯像鬼火。小客店是 一对黑瘦的中年夫妇开的,前边半间搭个小席棚卖面,后面有几间用高粱秸子隔开的小屋,供人住宿。也没有个床,只在地上铺上篾席给人睡 。小木窗棂上糊的报纸黄旧破烂,高梁秸的顶篷上挂着黑色的蛛网尘串,墙角砖缝里有时还出现可怕的翘起尾巴的蝎子。
三个人都累得腿酸背疼。童霜威上了年岁,身体又不好,格外觉得劳累。在彭婆镇找到这家小店住下以后,吃了一碗咸面条,觉得浑身像 散了骨架,弄点水洗一洗,就躺在高粱席上休息了。柳忠华走过来摸摸他的额头,觉得没有热度,才放心了,坐着陪童霜威,让童霜威好好睡 一觉。家霆在外边同架子车夫算账:本来讲好是到洛阳的,听说洛阳常有日机空袭,不准备进城住。童霜威累了,打算在彭婆镇住两天休息休 息再赶路。家霆为人厚道,虽然不去洛阳了,仍照原来讲定的价钱付给了架子车夫。车夫当然满意。
这一个多星期步行起早,走烂了好几双草鞋,有想象不到的艰难困苦,也有想象不到的危险。不走不知道,走了这一程才知褚之班的劝告 确有道理。童霜威无论如何想象不到“水、旱、蝗、汤”四灾竟会将这本来古今闻名的中原大地糟踏成这样可怕的人间地狱,以致到了离洛阳 不远的彭婆镇,想起一个多星期来的经历,心头仍感到战颤,疼痛。
他们离开界首后,向西北走。雇着一辆高架车拉着行李物件。架子车夫,是个慓悍的汉子,黑脸上皱起核桃壳似的皮。他套着车袢,用两 只紫铜般的胳膊拉着高架车。他光着脊梁,只穿一条脏得发了黑的白短裤,汗流浃背地迈着大步。他们由架子车夫带路,步行到周家口,又由 周家口向西到漯河市。从漯河市过铁路线到郾城,然后向西北经安沟、襄城、郏县到临汝,由临汝又来到彭婆镇。
烈日当空,火辣辣的,地皮像给烧灼着。
在从界首到周家口的路上,行人不少,多数是逃荒要饭的和商贩。日寇打到了河南,烧杀奸淫,离战区近的地方,田地早已荒芜,百姓都 向河南西南流亡逃难。去年河南大旱,今年旱情更重,农夫已经无法生存,大批逃荒出外。逃荒的人携家带口,男的头扎黑污羊肚巾,挑着些 破烂物件或挑着小孩,衣衫褴褛地离开家乡,盲目地流浪,一户户聚着、蹲着,端着黑碗,一路乞讨。看到灾民饥饿飘零的可怜景象,叫人心 酸。
正逢最炎热的暑天,日头毒辣辣,公路上灼热的尘土飞扬,公路两边种的高粱、玉米和粟子缺水,都卷着叶片,稀稀疏疏,萎瘪矮小,长 得像癞痢头似的。原来该是青纱帐起满目碧绿的景色,如今,高梁和玉米连不了片成不了“帐”,只看到迷漫浑黄的土地上,疏落地点缀着绿 色。
童霜威问一个挑着破棉絮、铁锅和小孩又带着女人逃荒的青年农夫:“是哪里的?”
“杞县的。”
“家乡不能呆吗?”
他摇头:“地老天荒,要有一点活路也不能出来逃荒啊!”
“打算去哪里?”
那青年骨架大肌肉瘦,一看是饿成这样的,瓮声瓮气地回答:“哪里能活命就去哪里!”
“家有老人吗?”
“有!年岁大了,没法出来逃荒,少锅断顿的,只能留下等死了。”
血泪的话,童霜威心酸,只能让家霆掏些钱给他。
烈日当空,白热的太阳太炽烈了,反而显得混浊不清。公路和大车路上也没个遮荫的地方。偶尔有搭着草棚卖小米稀饭和大米稀饭的摊子 。苍蝇嗡嗡地乱打转。所谓稀饭,只是稀薄的糊涂汤,很少米粒,价钱还贵得很。童霜威和柳忠华、家霆带着架子车夫就靠喝点这种稀饭充饥 解渴。
日行夜宿,第二天到达周家口附近,忽然听见一片窸窸窣窣的怪声。张眼看时,三个人都惊呆了,只见公路上黑压压拥过来无边无际海浪 似的大片蝗蝻。这种飞蝗的幼虫,青黄色,有淡黑的花纹,还没长成翅膀,会爬会跳,倾轧拥挤着,有三四寸厚,漫地都是,足足有二三里地 面积,流水一般向东北面爬行,看了叫人汗毛直竖。可怕的情景,真是见所未见。
童霜威叹息了:“日寇还在肆虐,再加上这样的天灾如何得了?”
蝗蝻占了公路,童霜威等三人和架子车夫避也避不开了,只好迎着蝗蝻在公路上向前走。柳忠华和家霆走在公路上有意拼命用脚去踩蝗蝻 ,一脚下去,起码踩死十几只,但你踩你的,它爬它的。踩不尽杀不完。约摸十几分钟,那群黑压压绿浪似的蝗蝻,一起过了公路到两侧地里 去了。只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蝗蝻都在嚼食庄稼,地里种的那点本来萎瘪矮小的高粱、玉米和小米,转眼间七歪八倒,绿叶都被啃得精 光。蝗蝻虽小,吃不饱似的蜂拥着又边吃边向前蔓延过去了。迎着蝗蝻刚才来的方向朝前走,只见路的两侧,庄稼像收割过似的一片精光。
家霆扶着心在战栗的童霜威向前走。柳忠华同那架子车夫正在边走边谈。架子车夫平时看上去不声不响,似乎对什么都不关心。其实不然 。他说:“去年,就大旱了,也闹蝗虫。飞蝗成片飞来时,天都被遮黑了,声音嘶嘶嘶哗哗哗,像落大雨似的,可骇人了!庄稼被蝗虫啃光了 ,许多人家都逮了蝗虫放在锅里炒熟了充饥。可是军粮还是照样征收。当兵的也吃不饱,有些兵像匪一样。上头还让百姓自带粮食工具去周家 口到开封之间挖深沟工程提防鬼子来。为挖深沟,民房拆了好多,祖坟也给扒了!其实那深沟并没什么用,百姓心里的怨恨呀,就没法说了! 今年又旱,春天从周家口到漯河的大道两边,隔不了多远,就能看到几具尸首,都是饿死的,也没人收敛,全叫野狗啃了!那个惨呀!说了也 叫人掉泪,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说着,他显得很生气,额上凸起青筋,黑脸都涨红了。
童霜威听了,闷闷无言,浑身是汗,脚下迈着步,心里因感慨想赋首诗。情绪不对,搜索枯肠,怎么也做不出诗,只是反复边走边吟起唐 诗来:“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寒禽与衰草,处处伴愁颜。”
唐代诗人司空曙的这首五律,虽然写的是寒冬,现在正是酷暑盛夏,但童霜威觉得心情与感触以及心境都与诗中相似。只有吟着诗时,他 觉得还能发泄心中的痛苦。
铁路线上的漯河,在河南省大灾之年,依然灯火辉煌一片升平。路灯光线黯淡,如蒙云罩雾,但酒楼上电灯明亮,猜拳敬酒,胡琴声嘹亮 ,女招待、歌女,红绿满眼,梳妆打扮;旅馆里牌九、麻将聚赌,妓女进出,数量惊人。漯河是个市,比界首更繁华。找家小客店住了,茶房 马上来问:“要不要女人过夜,最漂亮的大姑娘一夜只要八十元。”柳忠华回绝了他。童霜威等三人带那架子车夫一起上街,到小馆店里炒菜 吃了一顿馍馍。
架子车夫提醒说:“从这再往西北去,灾情重,一路上可能买不到吃的,要买些馍带着上路当干粮吃。”
柳忠华问:“火一样热的天,买了馍就馊了,怎么带呢?”
架子车夫笑了,说:“买点麻绳,把馍一个个串上,斜背在身上起早,不容易馊,路上要吃掰一个下来就是。”
家霆依他的话,同柳忠华一起在馆店里买了六十多个馍。馆店门口卖馍的地方,防备灾民抢食,馍上都罩着网子。两人将馍馍用细麻绳分 串成三串。三人各背了二十多个馍,很像《西游记》里沙和尚挂的那串骷髅念珠。
小客店隔壁是家小铁匠店,一盘炉子,一台铁砧,一个白胡子老汉带着个十四五岁的瘦弱徒工给人家的马挂掌,叮叮当当敲打,夜里敲到 半宿,黎明又敲打起来。听到铁锤打在砧上的声音,叫人心情;情沉重。加上蚊虫太多,客店里牌声和人声嘈杂,大家一夜都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出发向西北行。太阳还未升起,三人同架子车夫一起,走出漯河市郊。见路边挂着个“军警督察处”的牌子,有张办公桌, 两个当兵的坐着收钱,十几个荷枪的士兵站在一旁。一群客商和起早的行人,正拥在桌前交钱办手续。
架子车夫指指拥着人的地方说:“去缴钱吧!缴钱他们可以派兵护送。这一路,我不熟,听说不甚太平,常有打闷棍和抢劫的。”
童霜威听了,倒有点担心了,说:“忠华,去缴钱吧!有兵护送总好一些。”
家霆拔腿说:“我去办!”他径直跑到桌前,付了四个人的保护费。大家就在一边同那伙等候的人一起等待。
大约过了半个多钟点。火辣辣的太阳升起了,干旱的地面上沐着红光像着了火。懒洋洋走来六个军衣不整懒懒散散荷枪的士兵,由一个班 长似的人带领,大声吆喝:“走啰!走啰!”说着,大批等着护送的男男女女约摸有五六十人,一窝蜂地跟着动身了。六个荷枪的士兵开路先 锋似的同大伙一起走着,倒真有个护送的模样。
漯河往西北,大道两侧树上的树皮早被剥光。树多数全枯死了,枝杆有的也都砍断了。远处的垂杨柳,也被攀光了新枝,只剩下了粗脖子 的秃树干。高梁、玉米长得虽不好,倒已形成了稀稀疏疏的青纱帐,这是由于边上有条刚干涸的小河的原因吧?在青纱帐中的大车道上行走了 不过十几分钟,被护送的五六十人,走得快的在前边,走得慢的已经落后很远。童霜威父子和柳忠华带着架子车夫走得不快也不慢,发现那护 送的六个兵士已经不见踪影。估计是钻进青纱帐里打回票了!护送实际是个骗局,各人仍旧只好各走各的。
天上烈日熏人,一丝风也没有,空气像要燃烧,人热得难受。公路上尘土飞扬,印满车轱辘印,路边的高梁、玉米叶子,有的卷着,有的 垂着头。人在阳光下走,头里昏昏沉沉。忽然,前边远处听到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撕肝裂肺地哀嚎:“救命!救命!”
童霜威一惊,立定了脚步。
家霆上前站到爸爸身边,说:“有人叫救命!”
柳忠华和架子车夫也停下脚步,侧耳细听,叫救命的呼喊声消失了。后边有些步行的人也听到了救命声,匆匆走上来了。大家合计着往不 往前走?走,有危险;不走,怎么办?终于,还是往前走了,心里是战战兢兢的。刚才,一声女人凄厉的求救声太可怕了!
走着走着,在青纱帐里绕了大约一刻钟,见路边歪倒着一辆空独轮车,车旁两摊鲜血,虽然太阳暴晒,血迹还很新鲜,但边上没有尸体。
架子车夫龇着牙说:“有人打闷棍!尸体准拖进青纱帐里去了。”
天虽热,听到他的话,看到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