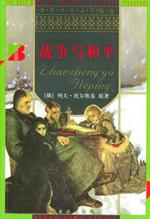战争和人-王火-第2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结了婚的初恋恋人的情景。那小说中在形容莱茵哈德看到她时,她身材比以前丰满了。……为什么这样想呢?问题是家霆不能 不这样想:难道她已经同别人相爱结婚了?所以负疚避开我不再愿意同我见面,想着想着,他心里懊丧到了极点。他深情地凝望着她,像过去 一样地那么热爱地凝望着她,心头涌上甜里带苦带涩的滋味,说:“欧到家了,我们谈谈好吗?”
欧阳素心啜饮着开水,她那可爱可怜的脸上透露出意志消沉。她的生活似乎并不贫穷,无论肤色还是穿着,都显示出这一点。她也仍然美 得周身像飞溅出吸力似的引人注目,只是眉心问那道以前没有的皱纹,却呈现出她生活得不好。她常皱眉,她不快活。”我对不起你!家霆!有 过这样的你,我比谁都幸运。但是——”她忽然开口说话了,而且这话是发自内心的,“请一定原谅我!一切都完了!我早完了!我们之问的一切 也早完了!”她流下泪来,拭着泪唏嘘起来。
家霆再也不能忍受了,一把拥抱着她,像他过去曾吻过她似的那么吻着她。她的两颊发烧,她哭泣,他也哭泣,把脸颊紧紧贴着她的脸。 两人的泪水流到了一起。见面本是喜事,绞心的是现在双方都能意会到这是悲剧,只有哭泣,才能发泄心中的痛苦。这样,哭了一阵,两人才 都松开手,各自拭泪,面对面地坐着,静静无——一
“欧阳,告诉我吧。”家霆心中充满了爱,十分诚恳地说,“你遇到了什么不幸的事?你怎么了?好吗?我想,我们的幸福是该由我们俩 一同创造的。不管是谁都阻挠不了我们的相爱,我也不会计较什么的!我只要有你,一切都满足了!没有你,我简直压抑死了!”
欧阳素心摇摇头。此刻,她似乎平静下来了,镇定地说:“不要问我什么了,我是不会说的!一切都过去了!我的个性你知道,你不要逼我 。”她看看表,“我不能多留,但让我们谈谈吧。告诉我一些你和老伯的情况,好吗?”
家霆简单介绍了自己和爸爸的情况,也谈了冯村的事。
欧阳素心忽然问:“你那位在上海让我介绍去同我父亲做生意的舅舅柳明好吗?”
“柳明〃是舅舅柳忠华在上海时的化名,去年一起离开孤岛同路到大后方来的事欧阳素心已经知道。现在她问起,家霆如实回答说:“成都 分别后.一直不知他在哪里。”说到这里,家霆不禁问:“你上海家里好吗?情况知道吗?”
欧阳索心平静地说:“知道一点。依然是那样子吧!银娣仍在。你舅舅柳明离开后,那个贸易公司的生意仍在做。”
从她的话里听不出什么感情来,似乎那个家同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她的父亲和继母也同她无涉了。
但她又说:“现在,战局起了极大变化。日本的处境不好,做汉奸当然死路一条f.'她语气凄凉,“听说政府正在大量做策反工作,共产 党当然也不会放弃策反。说实话,我倒希望我那不光彩的父亲能从汉奸的泥潭中爬上来。但我已经连对这也没兴趣了。”她的话什么意思呢? 家霆体味着。
欧阳素心忽然问:“有酒吗?”
家霆诧异了:“你现在爱喝酒?”她想寻求刺激填补心灵的空虚,还是想用酒慰藉心灵的创痛。爸爸喝过的那瓶酒就在橱里,但他不愿她 喝酒。
她摇摇头,苦笑笑:“不,有时想喝一点。”〃别喝吧。”他央求说。
她点点头,对他笑笑,笑容凄惨,使他心酸。
她突然说:“家霆,还记得在上海时,我们争辩过关于战争的问题吗?”
“记得!那些事我一点都不会忘记。”
“我直到今天还是怨恨战争,恨战争给了我苦难,恨战争破坏了一切,恨战争使人变态和疯狂,使人类流血屠杀,我亲眼见到日本兵就像 野兽。你还记得我的那张画吗?那张《山在虚无缥缈间》?我追求的一切美的善的东西,都是缥缈的!实际对我都不存在。我其实早已是行尸走 肉。世界之大,我从上海到香港,又从香港到大后方,走了一个大三角形,见到了牛头马面,看到了黑暗内幕,已经厌倦!厌倦人生,厌倦这世 道。路走得太多了,太长了!我累了!想休息了!”
家霆心怦怦跳着,听得急了,说:“欧阳,你太消极了!不能这么想!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战争是毁掉了许多东西,但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它 是毁不掉的。发动战争的侵略者终究在走下坡路了!反对侵略战争的人们会胜利的!战争毁了许多东西,但也能生发了生机。你也许还不了解, 中国也存在着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那儿有国家民族的希望。”
“可是,谁叫我是半个中国人又是半个日本人呢?我恨日本兵!他们无恶不作!但我站在中国一边,日本人骂我是日奸;日本如果战败了, 中国人又会骂我有日本血统。”欧阳素心似乎没有耐心听家霆的唠叨,更不想多思索,她只哀怨地自顾自在说:“中日结了仇,无论中国失败 还是日本失败,我都要遭受苦难。我恨为什么要让我降生到这世界上来。国家的悲剧加上家庭的悲剧本来已使我无法忍受,何况我个人是如此 不幸,我已经没有生路了!”
家霆劝慰着说:“欧阳,别那么想!你只应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边。再说,发动侵略的是日本的法西斯军阀,不是所有的口本人。日本人反 对侵华的也绝不是极少数。”他想把在上海时那位冈田医学博士暗中搭救爸爸的事讲给欧阳素心听,又觉得似乎太哕嗉,只是说:“欧阳,中 国也有法西斯,日本也有法西斯!中国也有好人和坏人,日本也有好人和坏人。你站在好人一边你就对了!”〃可是,我惶惑得很。哪里有正义 哪里有什么好人呢?我只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劫掠、强奸和轰炸,我也只看到大后方到处都有陷阱和豺狼虎豹!”她的眼睛像月光下的 树影一样阴沉,里面动荡着愤怒的火焰。
家霆恨不得把自己心里要讲的话都讲出来,可是,既没法一下子讲明白,电没法使她一下子就接受,更无法察知欧阳此刻内心想的是什么 ,她曾遇到些什么不幸,只能痛心地连声说:“啊!欧阳!譬你别这样消极,你别这样消极,为了我你也不该这样消极呀!”他起身上来抚慰她 。可是她拒绝他再接近她,只是摇着头,泪水潸潸流下来。
远处,房东陈太太念佛敲木鱼的声音隐隐传来,十分阴森,十分凄恻。
家霆终于问:“欧阳,告诉我,你现在在哪里?干什么?住在哪里?”他将脸凑近她,只看到灯光下她的眼睛好像深深的海洋,他好像沉 了进去,好一阵子都浮不上来。
欧阳摇摇头,烦恼地说:“别问了!家霆,我对不起你,我希望你将来有一个幸福的前途,也有幸福的生活。但,把我忘了吧!我已经不爱 你了,真的!我以前说过:'生命不在长,而在好!'我的生命太坏了!今后,把我从你的心上抹去,就当我们从不认识……”不容她说完,家霆着 急地说:“欧阳,你怎么这样说?在我的心中,你比我自己更贵重百倍、干倍、万倍!你真急死我了!……”说着,他真诚地流泪了,晶莹的泪 水挂满面颊,“你必须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别再追问我了!我早已经不知我为什么还要活着!战争时期死一个人毁一个人算得了什么!”欧阳素心闷闷地叹了一口气,脸上有一种冷 漠的伤心失望到极点的表情,“今天,我去朝天门江边,如果不是偶然碰到你,我也许早跳在江水里了!我去过好几次朝天门江边,都想去死! 但每次,我都又一念之差走回来了。不过,我确实只想死!你别逼我!我的个性你知道,你如果再逼我,我随时可以死给你看!”
家霆当然知道她那任性而坚定的个性,她说了是会做到的。但什么事使得她如此厌世想去死呢?怎么解开这个谜呢?
任由寂静的空问沉淀下各自澎湃的思绪。家霆犹豫了,只好说:“欧阳,我不逼你!我怎么会逼你呢!我只是为了要你好,只是为了要使我 们又能像过去一样过那种幸福美好而难忘的生活。”
欧阳素心皱着眉头,有着沉重难抒的神情,冷冷地摇头,重重地叹一口气:“不可能了!完全不可能了!”她站起身来,说:“我要走了, 放我走吧!”长叹声中透着解不开的沧桑。
“你再坐坐,我们再谈谈!”家霆说,看到欧阳把头摇得非常坚决,又改口说:“把你的地址告诉我吧!或者约定个时间再见面,好不好? 你知道,我真是日思夜想,我怎么能失去你呢?我的魂魄系在你的身上。”
远处,陈太太念经敲木鱼的声音始终不断地传来,慢悠悠的,炉火纯青,却又使人有镜花水月的空落之感。
欧阳素心又叹口气,摇摇头:“恨我吧!家霆!我和你不一样,我完了!忘了我!你自己好好努力生活!我该走了!”她起立就要拔步。
“你留在这儿!今夜就在这里,我们谈一个夜晚吧!”家霆求她。
“我有事!我得马上走!”
“我……送你!”家霆实在没有办法留下她了,说,“答应我送你回去吧。”
“不!”欧阳素心的表情显得冷酷,“我说过,你如果逼我,那就是说你要我马上就死!我一定走到马路上就冲到汽车上面去!我也可以回 去就死!我可以触电!我也早准备好了一把刀片,可以割破我的静脉!”
多可怕呀!她说得多可怕呀,但看得出她说的全是真话。这倒吓住r家霆,简直不知所措。她变了,那么美丽可爱的她变得这样了!是怎么一 回事呢?家霆心里明白:她如果走了,将倏然消失,如同夜空上转瞬即逝的流星!可是他能不放她走吗?连如此深厚的爱情都无法挽转她的决心 时,用别的东西更无法拴住她了。家霆伤心之至地拭着泪问:“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呢?”
“永远不再见面了!”欧阳素心摇头微喟了,“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她的声音,听来既强硬却又有无限伤感。她看了他一眼,从她的眼 神里,家霆心里感到她仍是深爱着他的。只是,她是那样违心地控制住自己。
啊!啊!……
她迈步向屋外走去。步伐是无力的,像是一种勉力的垂死挣扎。
“欧阳!——”家霆痛哭出声,“难道你就这么忍心吗?”欧阳略一战栗,但没有回头。
家霆紧跟上去。
欧阳回头,冷冷的脸上蓦然流闪出一种死亡的神态:“我说过,别逼我!你不要跟!那样只会使我马上就死!”
她头也不回地匆匆走了。
家霆等她走了一会儿,马上快步追出门去,沿黑黝黝的余家巷石级向上跑。他浑身发烧,心里火燎火烤。天暗,路灯昏黄,有些人在走, 却都不是欧阳素心。欧阳素心早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她走了,可又到处使他感到她曾在此存在过。他充满了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呆呆地像木 头人似的伫立在街边黑暗中。他拭不干泪水,想放声愤怒地狂叫。欧阳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呢?是什么事使她对生命已经如此厌倦了呢?是什么 不幸使她这样一位多情善良的少女,竟会变得这样铁石心肠完全要捐弃过去呢?……他想不出、猜不透这个谜。
一切都已枉然。他像被一盆冰水从头淋到脚地浑身发冷,颓然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来。
四
如果不是谢乐山亲自把粉红色烫金精印的结婚请柬送到余家巷来,并且说起了一些情况,童家霆今天是未必会去参加谢乐山在〃冠生园〃举 行的婚礼的。
那天,谢乐山油头粉面地来了,恭恭敬敬地叫童霜威〃老伯”,然后,把结婚请柬拿出来,说:“我要结婚了!家父请老伯和家霆兄赏光! ”后来,同家霆两人在外屋谈话时,谢乐山说:“我四月九日结婚,在'冠生园'。吃西餐,你一定要来捧捧场。那天,我把原先的老同学能请 的都请了。杨南寿、韦锋都要来,还有曹心慈,是新碰到的。他父亲是军委会的中将参议。我记得小时候你俩是很要好的。他也一定会参加我 婚礼的。所以,你一定要来,跟大家见见面。我们老交情,我再忙也不能不亲自来请你。”
家霆小时候同曹心慈确实很要好。两人斗蟋蟀、踢小皮球、划船,都常作伙伴。听他说起曹心慈,家霆不禁打听:“心慈在于什么?”
“好像也在军统呢!”谢乐山说,“看样子混得不错!那天街上遇到,匆匆互相留个地址就分手了。”
家霆又想起了欧阳素心,忍不住问:“欧阳素心还是没有消息吗?”自从那晚同欧阳见面又分手后,家霆一直伤心,只要想起欧阳就心里 难过。
“你还在想着她哪?”谢乐山眨着跟他父亲谢元嵩十分相似的蛤蟆眼说,“根本不知她在哪里!从那次在七星岩兴隆街附近偶然瞥见她后, 就没再见到过她。”说到这里,谢乐山可能是察觉家霆脸上的表情反映出心里难受,排遣地说:“童家霆,别做多情种子了!何必再去想她呢? 听说你现在跟一个姓燕的漂亮女同学很好,常常两人一起进进出出看戏喝茶什么的。早点请吃糖不就行了么?还去想欧阳干什么?女人的事么 ,不要太认真。就拿我说吧,我现在这位新娘子呀,名叫艾春茹,长得不好看,但她父亲早年留美,如今是孔祥熙院长的亲信,中央信托局的 副局长。同她结婚后,我们也许很快会一起去美国留学。我就图她这一点。好在,她长得不好看自己也知道。我要是想在外边怎么样,她也管 不着。我在这方面是不太认真的。你该学学我。”
谢乐人逢喜事精神爽。小分头上的发蜡搽得油亮,蛤蟆嘴一直笑得咧开着。走前,又炫耀地说:“这次我结婚后就去成都我父亲那里度蜜 月。我结婚,家父当然要来主婚。不过,家父不愿招摇,这次请的人不多。主要是让年轻的朋友们一同热闹热闹。所以伯父要是忙,不去就不 去。我知道,他同家父之间有点小误会。哈哈,不过家父为人忠厚,历来对老伯是很好的。我们之间就更不用说了。那天,你一定要光临!” 他像个小政客似的若悬河。送走谢乐山后,家霆把谢乐山讲的话说给童霜威听了。童霜威忙于写《三朝三帝论》,听后说:“谢元嵩是永远都 会使自己走红的,我不想见他。不过,谢乐山结婚既来请了,你当然应该去一去。你们有些老同学能见面,你也可以打听打听欧阳的下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