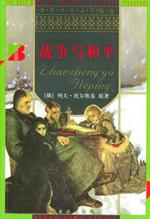战争和人-王火-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江聚贤后来有事告辞,留下了童霜威父子。童霜威叹口气对儿子说:“这下,我们要在此地住一段日子了。虽然不是自己的家,比起挨日 本飞机轰炸,还是在这里好,安全,又安静!”
家霆没有答话。刚到南陵县才第一天,他已那么想念南京了。想念潇湘路一号,想念鸽子,想念集邮本,(唉!为什么不带来呢?)想念玄武湖 、北极阁,想念同学和老师,也想念小叔童军威、冯村、尹二、庄嫂和“老寿星”刘三保。真奇怪,连喜欢手执鸡毛掸子动辄抽打桌子的英文 老师刘方叔和爱用板子打学生手心的算术老师、绰号叫“单老板”的单永安老师都想了!……院落里树上响起了单调、刺耳的蝉声,蝉声已经 不像在南京潇湘路一号花园里那么多那么响。他想:蝉儿老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秋意不久就要来了吧?
二
半夜里,一片幽暗。桌上那盏捻小了灯芯的煤油灯,发出一星微微的橙黄色的光芒。
打更的刚敲着竹梆打了二更,江聚贤家的大小老婆就开始吵架、打架。虽然她们是压低声音的,吵骂声和砸碎玻璃器皿声以及江聚贤的吆 喝声,都是压低声音在进行的。但这些声音却与阶前院子里的“曜曜”的蟋蟀叫一起传来,童霜威都听得很清楚。
后院夜间静寂,除了听到秋虫呜叫,除了打更的老头敲着竹梆走过的脚音,除了听到那只圆脸狸猫偶尔懒洋洋地“喵喵”叫两声外,有时 静得连树叶从枝上飘下或夜鸟轻轻在窠里吱叫都听得一清二楚。江聚贤的大小老婆一直吵闹到鸡叫头遍才停歇,童霜威一直没睡好。这些,家 霆熟睡着,一点不知道,童霜威却半夜常常失眠,能听得声声入耳。而到天明时分,江聚贤大老婆念经的木鱼声就又清晰传来。“笃笃笃笃” 一下一下都打在点子上,吵得童霜威心烦意乱非起来不可了。
江聚贤的大小老婆常是为争夺江聚贤到自己房里睡觉闹起来的。有时大老婆到小老婆房里闹,有时小老婆到大老婆房里吵。小老婆“金娃 娃”长得雪白粉嫩,像面捏成似的,据说是江聚贤花了一千多元从芜湖堂子里给她赎身娶来的。“金娃娃”是她在芜湖时,用成串的红字白灯 泡高悬在堂子门口做招牌时用的名字。那时,不但芜湖,连合肥、安庆一带常跑这种地方的达官商人都知道这个“金娃娃”。
她小巧玲珑,秀丽的白里透红的脸上薄施脂粉,两只黑亮灵活长睫毛的眸子有股魅力,红润的嘴唇笑起来特别迷人。她梳发髻,热天时, 髻上插满喷香的茉莉花,远远走来就带来一股香味。看样子,江聚贤喜欢如夫人,大太太偏不放松,事事都要监督。“金娃娃”又倚宠不买账 ,争吵自然不可避免。江聚贤虽然有心计也有手腕,还是一筹莫展。
童霜威觉得,八月中旬刚来江三立堂的头二十多天里,江聚贤的大小老婆似乎从没有发生过龃龉。可是近一个月里,争吵越来越频繁了。 童霜威明白:刚来的那头二十多天里,并不是她们无可争吵,是因为贵客刚来,她们不敢争吵。住的时间长了,大小老婆间的矛盾终于忍无可 忍爆发了。吵开了头,顾虑就越来越少。今夜的吵闹,声音又在向高处发展。尤其是“金娃娃”,一口道地的芜湖腔,已经清脆得字字都叫人 能听清了。童霜威被她们吵得心烦,联想起方丽清的吵闹。两种吵闹不一样,同样使人在生活上产生烦恼。方丽清在上海法租界上住着,来信 说她要到南陵来,却又没有来,也不说什么时候来。离开了她,童霜威有时也思念。但想起她的爱吵爱闹,又感到不在身边倒也有清静的好处 。现在是十月初了。来南陵瞬忽已经一个月零二十多天了!“着书立说”,童霜威是意兴索然,来此后简直一字未写,每天只是等着报纸看, 等着南京、上海来信,想得到些消息。这种皖南的小县份,实在是太闭塞了!人住在这里,像蹲在一池死水中。每天,只能闲逛闲聊,或是吃 吃喝喝,下下围棋。
南陵的所谓“名胜”,实际不过是一个“二乔墓”:黄土一塚,石碑一块,一些老树,一些荒草。想起《三国演义》上对二乔和孙策、周 瑜的描述,想起苏东坡《念奴娇》中的“小乔初嫁了”的词句,想起唐代诗人“铜雀春深锁二乔”的诗句,是会使人心向往之的。可惜闻名不 如见面,一见那也许纯属伪造或虚构的“二乔墓”那种荒凉模样,也就一点兴趣也没有了。另外,有个周瑜的“点将台”,也仅仅是块荒凉的 土坡;离得远远的黄盖墓,在青弋江边“黄墓渡”附近,人说根本不值得去看,他也就兴尽不去了。
住在江三立堂后院里,有点像是幽禁。每天,童霜威总带着家霆出去闲逛。踩着鹅卵石垫路面的大街小巷,嗅着那些黑屋脊上小烟囱冒出 的柴烟,脚步声惊吓得啄食的鸡群像爆炸一样四处飞。有时在清净点的馆店里吃早点,不外是米粉蒸糕、排骨面条之类,并无特色。然后,就 是早晚的散步,县城小得可怜,洋货店、烟纸店也小得可怜。想买盒牙签买盒好的香烟也没有。倒是县政府旁有户人家养着些鸽子,经常放飞 。家霆爱停步看上片刻。看到鸽子飞时,总想起潇湘路的鸽子,由此也就引起一连串对南京的怀念。
在城内散步厌烦了,童霜威带着儿子就走出北门向乡下走。到小河边上看看那些颇有风韵的洗衣女人,看她们用木头棒槌在河边青石板上 捶洗衣服。或者,到野外小树林或田埂边,听听秋虫呜叫,让家霆逮些蟋蟀回来喂养。这自然总是很单调很寂寞的散步,除了农舍、丛树,除 了看乌鸦绕树、蝙蝠飞舞,并没有什么新鲜事物可看。
冯村每隔十天光景来一封信:信上说起褚之班不知走谁的门路,居然到安庆地方法院去当院长了!信上也提到潇湘路两家邻居的信息:管 仲辉忽然又到了大本营担任高级幕僚,似乎突然又相当得意,但家眷留在上海租界,他本人已不常住潇湘路,为便利办公,住到陵园附近去了 。叶秋萍一直在郊外居住,家眷因为轰炸已迁往武汉租界居住。冯村信上更说:传闻共党代表周恩来、朱德等曾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划定作 战地区。
南陵县消息闭塞,南京的《中央日报》每每要隔三四天或四五天才能送到,新闻也成了旧闻。上海战事仍在激烈进行,呈胶着状态。敌机 对南京的轰炸仍在继续,战争的结束似乎还遥遥无期,天天都在死人。这是一场不宣之战,中国和日本都未宣战,似乎是想为和平留下一线生 机?时局究竟如何发展?谁也估摸不透。回南京总不是办法,也只好在南陵县继续住下去。想到这些,童霜威心里就说不出的气闷。
夜里睡得不好,早上起来,童霜威头里昏沉沉地很不舒服。带着家霆吃了丫头小英端来的早点:豆腐浆泡豆腐皮,油酥烧饼外加煎荷包蛋 。吃完,刚想出去散步,王汉亭来了。
王汉亭,是童霜威在南陵新结识的熟人。童霜威来南陵后,严格遵守一条戒律:不愿向外宣扬,只愿隐姓埋名在此悄悄住上一段时日。可 是,人总不能没有朋友,也不能只有江聚贤这种只会谈粮食、谈租税、谈田地房产的朋友。江聚贤不是笨蛋,自然也知道童霜威寂寞。来后不 久,有一天,江聚贤递过一张空白无官衔的名片给童霜威,告诉他:这地方,去年新回来一个少将,本地出的军界人士官儿数他最大。早年在 北方当兵,后来爬上师长宝座,可是行伍出身,不是黄埔嫡系,也无资历,最后落得个队伍被整编、自己被裁减。大老婆被他遗弃,他被裁撤 后小老婆卷逃跑了,他就独自解甲归田回到家乡来了。江聚贤说:“此人名叫王汉亭,虽然行伍出身,阅历广,见过世面,又会下得一手好围 棋。他想来拜望秘书长,秘书长认为合适,我就找他来,陪你聊聊,也陪你下下围棋。”
童霜威同他一谈,虽然此人气质粗鄙,见解也并不高明,在这样的小县城却还属可以降格谈心的人。王汉亭又常能带些内幕消息来,比如 陈独秀已经减刑出狱,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在由南京乘汽车到上海时,受日机袭击负了重伤已经痊愈。南京警备司令部逮获重要汉奸黄溶执行 枪决。这黄溶四十六岁,闽侯人,是行政院秘书,与他儿子黄晟一起向日本出卖情报,泄漏了军事会议的秘密。本说要在江阴封锁长江,将日 本军舰一起拦截住,黄溶父子将情报卖给了日本,日舰一夜之间都逃跑了。……听王汉亭说说内幕消息,不管真假,总很有趣。又加他能作棋 友,一盘棋杀上两个小时,倒也消磨不少时光,排遣不少寂寞。平日,多数是他到江三立堂来,有时,童霜威也去。王汉亭解甲归来以后,本 来无家。因为打牌,结识了本地王三槐堂家的一个四十多岁的遗孀。认了本家以后,不久两人就以叔嫂称呼相好起来。王氏遗孀一个独子已经 长大在南京上大学。她用出租房屋的名义,将自己院子里的一溜东房“租”给王汉亭住。王汉亭搬去后,日夜陪着王氏遗孀打牌喝酒。外边人 都知道这中间奥妙,可是无人干涉。王氏族人有想干涉的,知道这个“少将”脾气火爆,早年当营、团长时是有名的“不怕死”,当师长时, 亲自枪毙过临阵脱逃的十二名士兵,没谁敢去老虎屁股上拔毛。
王汉亭在南陵赋闲,结识了王氏富孀手面就阔绰起来了,衣着也很华丽,俨然是地方士绅中的头面人物。认识了童霜威,他自然高兴,不 时在家里摆酒设宴,邀请童霜威小酌。王氏寡妇烧得一手好菜,像烩猪脑、炸虾球、滑熘鱼片、冬瓜盏等这些菜都很吸引童霜威。童霜威虽不 嗜酒,来到南陵后心里苦闷,偶尔也免不了喝上半小盅逢场作戏。今天,王汉亭穿了一件浆洗得极硬的灰团花绸长衫,手执一把九华山描金黑 扇,一早跑来,童霜威估计他准是又备下了好酒好菜邀去吃饭的。倒没有猜错,王汉亭一来,掏出一包强盗牌香烟来抽,说:“秘书长,中午 请到舍间小酌。”家霆仍在卧室里吃早点,童霜威请王汉亭到书房里坐。王汉亭接着说:“今天我找了个陪客,请秘书长一定赏光。”
江聚贤大太太的木鱼声正“笃笃笃笃”传来,她念的是“南无(笃)观世(笃)音(笃)菩萨(笃)”,一遍,又一遍……
童霜威在上首红木太师椅上坐下,用牙签剔牙,惊讶地问:“谁呀?”
院子里,丫头小英左手拿着畚箕,右手正在用扫帚扫树下的落叶,发出“哗哗”的声音。
王汉亭笑涎着脸说:“秘书长来后,秘而不宣,实际上你是一棵撑天大树,怎么能不引人注目?怎么能守得住秘密?天下哪有不透风的窗 户?本地的父母官朱县长,打听到了,他很惶恐,觉得自己失职!秘书长是大人物,来到小地方,他既未过来请安,又未关心起居冷暖,内疚 得很。找到我,要我先来作说客。他怕贸然来看望,太失礼。如果秘书长赏脸,他马上趋前拜谒。我就决定邀他作个陪客。”他“呼”的一声 ,吐了一口浓痰,身旁放着铜痰盂,不往铜痰盂里吐,却将浓痰吐在青砖地上。
童霜威皱皱眉,倒不仅是见王汉亭随地乱吐痰,实在是因为不愿意在此隐居被人知晓。但事已如此,听王汉亭的一番话倒还入耳,加上这 县长倒也似乎有一片诚心,就又释然于怀了,松开眉头,说:“呵呵呵,行啊行啊!我本来是怕惊动各界,不太合适,既然他知道了,见见也 可以嘛。”
王汉亭抽着烟,哈哈一笑,说:“秘书长,实不相瞒,其实,朱县长已经来了,在前边等候呢!我去叫他,马上就来!”
木鱼声仍在“笃笃笃笃”地敲。
童霜威也哈哈笑了,说:“啊呀,刚才何不一同进来呢?”他起身叫了一声在扫地的丫头:“小英!”说:“快去前边,请朱县长来这里 客厅坐,等会儿客人来了要泡茶。”
小英“呣”了一声,伶俐地转身到前边去请客人了。童霜威和王汉亭都慢悠悠地站起身来。
童霜威风趣地说:“走,我们接一接父母官吧!”
走廊上充溢着浓烈的鸦片烟香。鸦片味童霜威每天要闻好几阵,每阵总得有半小时至一小时,都是从走廊那头的卧室里传来的。江聚贤的 大太太和如夫人金娃娃都吸鸦片。大太太敲敲木鱼念佛,停一阵就要吸一阵烟。
王汉亭用鼻子嗅了一下,说:“好香,烟土不孬!”
两人刚走出房间步下台阶,穿过紫藤架,走到麻雀“吱啾”的院中,看见穿蓝花布短衫的丫头小英在前边跑来。后边,江聚贤恭敬地陪带 着一个穿灰中山装手拄“司的克”的中年人走来。中年人剃的平头,白净微胖的脸,一对精明的小眼睛,一看就是办党务的人的模样。远远见 到童霜威,江聚贤用手一指,他立刻九十度鞠躬叫了起来:“啊,秘书长,鄙姓朱,朱大同,撇未朱,‘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的‘大同’。 鄙人来得太迟了!太迟了!”说着,走前几步,双手递过一张布纹纸名片,抢上前来同童霜威热烈握手。
童霜威笑着同他握手,手被他捏得生疼,说着戏言:“你消息灵通得很哪!”
王汉亭、江聚贤也在一边帮着笑。四人笑着上了台阶进人客厅。鸦片烟香冉冉传来。童霜威闻着皱了皱眉,心想:新生活运动,禁吸鸦片 。我在会见县长,这儿却在抽鸦片,不是故意给这县长出难题令他难堪吗!看看王汉亭、江聚贤连同朱大同都似乎嗅而不闻,若无其事,也只 得若无其事,坐着微笑。
小丫头小英忙着赶走睡在红木太师椅上的一只狸猫,端茶送烟。
朱大同说他不会吸烟,其实是他见童霜威不吸烟,怕童霜威不喜欢吸烟的人,所以表示自己无嗜好也不抽烟。他恭恭谨谨地说:“鄙职想 先把本县关于抗战的情况向童秘书长报告一下。”
童霜威闻着鸦片香,心想:我又不是钦差大臣来视察工作的,我的官职早卸除了,谁想听你说些冠冕堂皇的嘴上文章呢?又不能不听,有 意捧场地说:“我来贵县一个月零二十天了,贵县的情况已经略知一二。你这父母官的政绩是有口皆碑的嘛,你简单讲讲吧!”
朱大同听了一番颂扬话,受宠若惊站起一鞠躬,说:“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