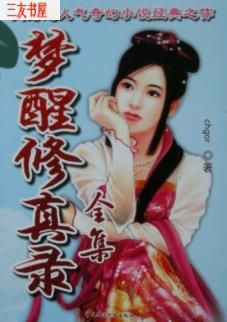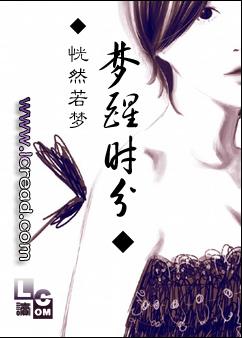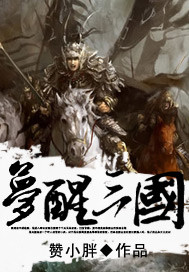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 作者:张鸣-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将之分成在朝和在野的,或者高层、中层、低层的,以及 富绅与寒士等等,甚至名士、俗士、学者……等等也可以算是一 种分法。 32
不论怎样分,不同类别和不同等级的士,其政治态度是有差 别的,其政治动作与习惯也不相同。有的差別是由各自的位置和 身份所决定的,比如在朝与在野的士,很自然政治操作与习惯就 不可能一样。(有人因为几乎每个朝代的官方都将正在人仕为官的 人不视为吗民之首的士,所以在谈论士绅的话题时往往只限于在 野的士,显然,这种限定对于我的话题是不合适的,跟实际情况 也相脱节,我们在讨论士绅的地方上功能作用时固然可以将正在 为官者排除,但绝不能因为读书人作了官就失去了士的身份。入 仕为官恰是几乎每个士都热切追求的事。〉除了那些单纯想从权力 中攫取利益的人们之外,入仕实际是接近传统士子儒家式政治抱 负和理想的一种状态,而这种抱负和理想,也是士之所以为士的 要索之一。(当然实际政治中理想总是要打折扣的。)或多或少,为 官作宦的人均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政事的进行。愈靠近权力 中心〔皇权〉的人(倒不一定按官阶排列、这种机会就愈大。位 尊权重者或者皇帝的亲信可以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较大乃至决定性 的发言权,一省的督抚在有可能左右省级政事的同时,对中央或 全局的政务也有一定的发言权。(清代尤其如此,朝廷经常就某一 政策事务征询督抚的意见。〉同样,只要不是“闲曹’’,攀权柄者 都在其范围内干预政治活动的运行。是苛政还是宽政,是繁政还 是简政,即使小如知县也能让指针向某个方向偏动。
明清之际,处于士的金字塔塔顶的是有过进士功名的人,三 年一大比〈加上恩科也至多平均两年多一次考试〉,每次取士不过 二百余人,这种经过层层筛选下的仅存硕果,不言而喻地受到各 方的瞩目,相对来说,进士困子的自我认同感也较强,“科甲出 身”的金字招牌,往往成为这个阶层同气相求的“通行证”。在实 际的政治生活中,进士出身的人往往凭借同年(同科同榜同乡 和师生网络来运作,尽管皇帝三令五申不许士人结党结派,但进 士阶层中的宗派团体活动却从来都在有形和无形中存在着。西方
33
中国军阀史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从未形成过类似西方军官团的 精神,但中国明清之际的“进士团”(文官团)精神却仿佛有之。 在张仲礼先生有关中国绅士的著名研究中,将进士集团视为“核
心团体?〔1〕
在士的塔顶,还存在一个特殊的顶尖,即翰林小集团。翰林 品级不螅词侨巳讼勰降摹皽'要之职”,从理论上讲,只有会 试中名列前茅的人才可以进教林院〔当然也有极少数殿在三甲如 曾国藩者因礼部考试成绩极优而侥幸得々的〉。一般来讲,翰林出 身的人日后的仕途都比较顺利,而且他们往往是各省学政和乡试 主考副主考的首要人选,这不仅强化了他们所负的学品与士望,而 且使他们成为传统社会士角色最充分的体现者。至于通过考试与 学官的职位建立师生阿络,实际上是政治操作中的副产品。正因 为这种“士林之望”的地位与身份,使得翰苑人物以道德学问自 负的湥{气比别的集团来得浓重,每每以挽回风气为己任,晚清 批评时政的“清流党”,大都身厲翰苑,或出身翰林,就是这个道 理。
在野的士是士林最大的一群,不仅相当多的士无法进人仕途, 而且不断有身在朝堂的人退下来。有的是暂时性的,因病或者丁 忧,还有些是长期的,丢官的致仕的和因宦海险恶而辞官还乡的。
在野的士当然也分阶层,做过螅傧曰禄瓜绲暮驮斯病≡返氖课抟纱τ隗室坏燃丁5诙燃兜氖侵泄康娜耍谌取〖妒蔷偃撕凸鄙加殴薄喂焙投鞴薄⒃偻戮褪巧保詈蟮妗〉孜抟墒侨耸疃嘤兄究瓶嫉耐�6不过,在野士人的等级,有 时也与人品、声望与学问有关,公认的硕儒和学者或者人品声望 俱优者丨即使只是一介生员,也往往能获得较大范围的尊重并在
〔1〕参见朱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I么 海社会科学院出饭社,1991年,第119页。
落4
地方政务上产生较大的影晌,即使什么功名都没有,也是一样。像 梁启超的父亲,一介白丁也能靠着能干与德望孚众,們然成为当 地乡绅的领袖人物。
在野士人政治活动的范围之大,是今天的人们所不可想象的, 大如賑灾、地区防务、文化教育以及賦税的征收,小至修桥补路, 排解纠纷,几乎无处不有士人的影子。明清两朝吃皇家俸禄的地 方官额数少的吓人,一个县也就那么几个人,再加上频繁的轮换 以及原籍回避制度,使他们的行政效率大打折扣,如果碰上个庸 才,连正常政务也维持不下来,私人聘用的师爷们和书办衙役,虽 然能帮忙办事,但为自家拂钱才是他们目的,摘得不好就会出大 纰漏,丢乌纱倒霉的,却是官员自己。所以,地方官几乎没有不 依靠当地士绅就能行使职责的,“为政不得罪于巨室”是地方官共 同的座右铭。所谓“巨室”,即为士人中有权有势又有财富的缙绅 望族。张仲先生说:“官吏们所做的事,恃别是县官,极为有限, 绅士所干的事,往往取代了官府的政事。绅士的这些事或许可称 为‘半官方’的,因为绅士代政府而行事,但又不是政府的代理 人。绅士仍然是一个社会集团,在自愿的基础上行事广〔1〕严格地 讲,士绅并不是“代政府而行事”,由士绅们做的那部分地方政务, 事实上是明清政治架构中特意留给士绅的,地方官所代表的皇权 和地方上的绅权以及各自的政务范围之间有某种平衡,谁越了界 都是种麻烦。,
由于在传统社会里,乡村的地位并不似后来这般的衰落,乡 居的士人明显多于城居的同类,即使达官显宦改仕后也往往回乡 养老。所以在野士人政治角色在乡村就显得格外鲜明,政治作用 也格外突出。按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的说法,传统社会乡村中的
11〕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杜 会科学院出饭社,第50 — 51页4
35
权力结构事实上是双重架构,官府一层,乡绅一层。在我看来,这
双重架构中,官府只是浮在上面的一层皮,没有士绅,那可真就一
是“天螅实墼丁薄×恕�
一位研究者将清代士绅在乡村的社会活动归纳为“地方学 务”,“地方公产”的管理和“地方公务”三大类显然,还必 须加上赈济、地方防务、宗族活动以及非教育性的文化活动等几 项才勉强能概括〈我所说的士的范围虽然比王先生的士绅要大,但 社会活动大体相近〉。问题是这些社会活动中有多少是政治性的 呢?地方公务和防务无疑是当之无愧的政事,而学务、文化活动 与赈济事实也与政治相关。士人在乡村起的是一种基层政权的作 用,把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最大限度地搅在了一起。
教育和文化事务是士人最乐意做,也最合乎身份的事情。从 某种意义上说,士人的社会活动是从文化和教育向外辐射的。退 休和离职的官员们,大都以担任书院的教席为荣,书院的维持,也 往往有赖于士绅的捐助。各县官学校舍和贡院的修造,也由当地 的士绅主持,从筹资到负责工程,面地方宵只是发起而已4 一般 来说,当地士绅还负责资助和奖励应试的举子,大一点宗族,都 设有专项的资金和田产来应忖此事,总其事者,大都为士人。此 外,文庙的香火,也由士绅来维持。一些有名望的士绅还热衷于 修撰地方史志,以维持道德风化。至于遍布乡野的各种义学、村 璺、家垫,就馆授徒,更是士人的专利,尤以那些寒儒为多。― 般的穷秀才(还有一些举人)成为各式私学教师的主要来源,屡 试不笫的老童生,开馆授徒的更是不在少数々广东花县不箅是穷 乡僻壤,可洪秀全、冯云山等“白丁”也能以授徒为业。宣称 “白衣致卿相”的科举台阶,也许是农村学子读书的动力,而乡野 文风之系,还真有赖于这些乡村塾师。
〔1〕王先明:《论近代社会中的绅士集团》,《史学月刊)年第1期。
36
维持地方治安与防务,是士人另一项大的重要政治活动。从 来乡村地区的治安,主要不是由官军来维持的,中国传统社会又 没有警察,防匪洽盗主要由乡村中的头面人物即士绅来张罗,修 筑圩寨,组织乡勇团丁。每逢社会矛盾尖锐,天下将乱和大乱之 时,这些乡村治安组织就变成大大小小的团练,自发地抵杭农民 起义军。
賑济活动是士人又一项社会“主业”。每逢发生灾荒时,一般 会有官方和民办的两种賑济活动。官方賑济常常很不及时,赖有 民办的賑济应急。就是官方的赈济,也需有士绅居中操办。賑济 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措施,显然,主持这项事务的士人们 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
此外,某些势力较大同时品质恶劣的士绅还能通过与地方官 乃至与胥吏勾结,把持和变相把持赋税的征收,不是有意为自家 减免,就是从中浮收渔利。同时乡绅还能借助于宗族系统,事实 上侵夺了相当部分的司法权,谁都知道,宗族对犯错的族人可以 自行处罚,小到鞭笞,大至沉渾(处死〉。而官方则多半睁眼闭眼, 听之任之。
比起在朝士人来,在野士人政治活动的习惯有所不同,对于 有些合乎身份、比较光彩露脸的政治和社会事务,他们的活动是 显性的和公开的;而某些显然包藏私利的活动他们则隐在台后。乡 绅们实际控制了乡村,但乡村中半官方的乡约和里正他们是不屑 担任的,甚至于宗族的族长他们也往往避而不就,但这些乡约、里 正和族长,却无一不听命于那些声大势隆的乡绅。在传统社会里, 士绅必须维护自己的道德形象,即使是恶人,也须以伪君子的面 目出现才更合乎“身份”。
行动必须合乎身份是士人行为的最基本准则之一,如果做出 了不合身份的举动,士入就意味着丢面子。贫穷的士人服饰上可 以将就,但行为必须谨慎。清人笔记记载了一段故事很有意思:
37
“一教书先生,居村数里,有小路逾沟而行,稍近数十步。先生平 生必由正路过桥,不趋捷也。一日自市归,遇雨。行至沟旁,四 顾无人,一跃而过。有童子匿桥下避雨,惊曰:是先生亦跳沟耶? 先生饵以一钱,嘱勿言。童子归、其父诘其钱所从来。争传是先 生跳沟,声名大损广〔~在今天看来,这位教书先生“声名大抿” 损得委实冤枉,但在那个时代,“先生”也只好委屈点了。在传统 社会的士人中,只一小类人的行为举止可以在一定范围逾矩过格 而不受舆论的谴责,这就是名士…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轭象,在十 分讲究礼法的社会里,大家对“道学先生”的行为评判往往过于 苛刻,而对于名士则又过分宽松。只要帔冠以“名士”的头衔,就 大可以恃酒狂放,不拘礼法,留连于秦楼楚馆,徜徉在酒家戏苑, 甚至放浪形骸,肆言无忌。当然也有玩得太过火而身陷囹圃的,如 明代的李贽。或者碰上个把用心险恶的地方官而丢了性命的,如 金圣叹1 一般来讲,名士还是安全的‘徐谓杀过妻子,扬州八怪 蔑视王侯,袁才子(袁枚〗招了一群女弟子,都活得好好的。名 士沉缅于琴棋书画、醉酒妇人,但绝非忘情于政冶。名士每每游 离于政治中心之外,并非他们不想出将人相,建功立业,或者缺 乏从政的才能,对于他们中的多数来说,恰恰是政治抱负太大,从 政热切太高,才情也过于旺盛,才在并不需要他们的才气、忠诚 和见识的官僚体系中处处碰壁,对他们来说,政治的悲剧不仅仅 是怀才不遇。名士洪亮吉一鸣惊人的上奏,针砭时弊,畅快淋漓, 却落了个远戍新疆,比贾府上忠心耿耿的焦大那一嘴马粪还惨。龚 自珍和王韬也是一腔救世之志和救世之识,却依旧只好在依红偎 绿、浅斟低唱里打发时光。
顽固的道德取向是士人政治行为的又一基本准则。我们这么 说不等于说凡士人都是讲道德的,任何社会群体都存有寡廉鲜耻
〔I〕清“阮葵生:《茶余客话I 38
之徒,士人中的无耻之辈并不比农、工、商中少些。但是戴过方 头巾的士,在明清时节经过理学的强化教育,都是名符其实的儒 士,僑家伦理和礼仪已经通过专门的学习和日常活动的习染,渗 透到了他们的骨糖之中。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他们至少在公开场 合要尽量使自己的言行合乎儒家道德礼仪,如果实在不符合,也 要找出些堂而皇之的理由或借口。比如为官者父母身死需丁忧守 制三年,如果有的权臣实在放不下乎中的大印,就得设法让皇帝 出面阻拦,借口 “忠孝不能两仝”而“夺情”。如果在非常时期, 那么理学家要求于妇女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符咒就会在士人 身上“显灵”,担心“失节”成为改朝换代时传每个士人的最大忧 虑之一。胜负已判,天下已定,还好说,自然会有“一队齐夷下 首阳”,就是天下混混沌沌的时候,最难将息,迎新还是恋旧让人 两难。一旦“事二主”的帽子戴到头上,就像那时代再醮之妇一 样让人难为情。明清鼎革之际,抵抗清军,为明死节者,后来受 到清朝的表彰,而帮了满清大忙的洪承畴、1钱谦益诸人,反被新 主子列人“贰臣传”有意让他们遗臭万年。真是巧妇难事两姑!
“节”这种政治上的道德要求是士人们所独有的,而其他的 “三民”则没有这个荣糴。这从另一面也说明士人在政治活动领域 道德气氛之浓重,他们在进行政治操作时,道德评价往往是首要 考虑的问题。有时候,事情的成败利钝,政治运作的利害得失是 一回事,而道德评价的好恶又是一回事,但是士人就更多地要考 虑在两者之间的权衡和抉择6在道德准则与政治现实发生冲突的 时候,只要与自己利害无直接相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