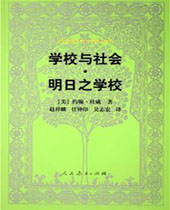明日歌·山河曲-第8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华灯初上,京城已然夜了。郦逊之搀了他,犹如搀扶另外一个自己,不期然有殊途同归之感。他隐隐知道楚少少跟他走的不是一条路,可此时此刻两人无比贴近,无比相似。他在月光灯影下看这个扰乱他心思的男人,竟生出同舟共济的念头。
楚少少忽然恶心,喉咙干呕了一下,郦逊之皱眉道:“不行,得找个大夫,你喝太多,身子要保重才好。”楚少少凄然一笑:“他日大难临头,你可还保得住我?”
郦逊之心头一跳,他指的绝不是眼前的事。埋藏在心底的灰绳草线一下被全数拎起,郦逊之瞪大眼看他,终于想明白了。楚少少一个踉跄,忍不住跌跌撞撞冲出几步,扶了墙根大吐。
郦逊之的脚粘在地上,他动不了。凝视楚少少的背影,他在想,该如何替楚家脱罪,保全这个乖僻俊秀的男人,保全将来会遭遇不幸的楚家。
郦逊之想到这里又苦笑。以现时赫赫盛名的楚家来说,即使如康和王府和郦家军,怕也不放在他们眼中。难道在他心里,所谓的保护其实是想借助楚家之力为己所用?郦逊之摇头叹息,为什么他连朋友之义都最终会牵扯出权术谋略的心思,究竟他能不能既是朝廷大员,同时又是江湖中人?
楚少少回头瞥他一眼,继续吐了几口。郦逊之直被这眼神瞧得心底发慌。楚少少是男人,却算不得他的知己好友,为什么心底竟会生出如此不忍与心动。一想到楚少少可能会死,他居然分外不舍。
等楚少少吐干净了,再看郦逊之时眼神透亮明晰,毫无醉意。一个雍容的少主又回来了,楚少少深吸了口气,对郦逊之道:“为什么我就是醉不了?”郦逊之柔声问道:“你心里真的想醉?”
“当然想。我从小喝酒,每次想醉,也都醉不成。”楚少少哈哈大笑,“如今成了酒鬼,喝多少不在话下,更加难求一醉。”他眉头深锁,难解的愁刻在眉尖心上,竟令郦逊之有几分心酸。
郦逊之按下心事,想到龙佑帝交代的苦差,不觉叹气道:“我要偷左家的账簿。”他如此干脆说来,换回楚少少一记苦笑:“你刚施恩,便望我图报,忘了我们早已两清?”郦逊之不觉拿出他当日所赠的匕首,在手上把玩,道:“恩怨纠缠,原是说不清楚。”蓦地里说出这句话,郦逊之自己也是一愣。
楚少少无奈说道:“你明知有我助你,左家账簿手到擒来,可我却担了什么罪名!”郦逊之默然半晌,抽出匕首,看那白花花的刀片反射刺目的阳光,方道:“进退两难,你该懂我。”楚少少歪着头想了想,神秘一笑:“你可知最令皇上心急的,并非左家的事。”
郦逊之心一动,想起那传唱京师的歌谣,却笑道:“皇上心忧社稷,哪一桩事不放在心上?”楚少少摇头,眼中流露出洞悉的目光,仿佛知道郦逊之故意岔开。郦逊之心如擂鼓,慌慌地想,莫非这亦是对方的局?便听楚少少悠悠地道:“我且告诉你答案,报你方才援手之恩。”
郦逊之不自觉间将匕首柄在手中攥得生疼,此刻强自镇定道:“你说。”
楚少少盯紧他,带了戏弄的神情,微笑道:“莫道君为天下主,天下笑谐谐。园中花谢千万朵,别有明君来。”郦逊之咽了口干沫,道:“原来你也听过。”楚少少道:“你心知肚明。你知道这歌唱的是谁?”见郦逊之茫然摇头,续道,“便是你的至交好友——江留醉。”
郦逊之无论如何没想到“别有明君来”的明君,居然是江留醉!天旋地转不足以表明他的震撼,不由呆立当地。江留醉,那个酒楼偶遇的少年,那个他认作了兄弟的好友,那个为他赶赴灵山的知己,竟是皇子!偏偏这身份如此诡异地显露于朝野,成了龙佑帝最大的心头之患。
郦逊之不无痛苦地想,如果某日江留醉的身份被人利用,一心拯救朝纲的他该如何是好?抬头再看楚少少,身后的璀璨华灯如刺目的火球泛出异样光芒,令他不可逼视。隐约的轮廓让他想到江留醉,举手投足里的知遇情深,成为他理智的羁绊。如江留醉此刻正站于面前,郦逊之心头狂乱,不知要以怎样的心情再去面对。
而在不久的未来,江留醉无疑会成为内乱的导火索,龙佑帝又会如何?
楚少少等他惊异够了,才悠然地道:“你的好友成了皇子,皇帝主子有了兄弟,为何不替他俩高兴?”
郦逊之苦笑:“皇帝有兄弟,从来就不值得高兴。”相反,令人不寒而栗。龙佑帝始终没有兄弟,这是他安坐帝位的原因,此刻突然冒出来一个兄长,相信皇帝也应手足无措。
楚少少目睹他的无奈,眼中流出一抹同情,拍拍他的肩道:“左家账簿你自去取。生死有命,我帮不了你……”说罢,跌跌撞撞一人去了。长街中他的影子拉得极长,始终在郦逊之眼前摇晃。
郦逊之呆呆望了他离去。
那一夜,又不成眠。郦逊之不再想江留醉的事情,此事事关重大,在没有看到真凭实据前,他不想兀自胡乱猜测,反而乱了方寸。于是唯有细思账簿一事。
他知道左家非去不可,去了或更有法子保全楚少少一家。只是账簿这等机密物件必收藏紧要,他上回深入左府险险中伏,这回如何能全身而退,颇费周章。
左思右想了很久,郦逊之灵光一现,突然想到楚少少不肯帮忙,雪凤凰又不在,可另一位神偷近在眼前。金无忧既已返京,金无虑必在旁照顾,那么前去左家一事就不难应付。想到此点,他一颗心踏实了,安稳睡去。
次日天亮,郦逊之叫了郦云出来,自换上一件雪白的鹤氅裘,裹了水红色瑞锦长服,施施然去了忘珍楼。
临窗挑一雅座,点了飞鸾脍、龙须炙、折箸羹、无忧腊、月华饭和西域龙膏酒,关了门自斟自饮。他这一席的花费胜过旁人一桌,郦云在楼下打点,并不上来。坐了不多时,一个身著韦袍的中年人走上楼来,推门在郦逊之对面坐下。郦逊之举杯相邀,那人端酒含笑,一饮而尽。
郦逊之道:“今日求见神偷,有一事想请阁下相助。”这地方正是金氏兄弟和龙佑帝约好通消息的场所,只是偌大排场是郦逊之一时兴起,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对金无虑的重视之心。
那人正是易了容的金无虑,金无忧的身子已大好,他也放了心,见忘珍楼有动静,打听到是康和王的世子,情知龙佑帝交代了郦逊之。他倒满一杯酒,悠然道:“有事直说。”
“我要取昭平王府的账簿。”
金无虑夹了块腊肉,生生停在半空,咽下口中的酒,道:“这与找死分别不大。”
“我知道此事千难万难,然而在神偷眼中,想来非是完全不可为。”
金无虑笑道:“东海三道的徒弟果有胆识。我写个单子,你备齐了,便一同去。”
郦逊之大喜,想不到金无虑快人快语,当下就答应了,连忙举杯敬他。金无虑摇手道:“左府的地图若不先备好,你给再多银两,也是枉然。”郦逊之含笑:“这却不难。”当即取出羊皮卷递上。
金无虑颇为惊异,盯他看了一阵,又道:“这些年来左府修葺了哪些地方,你可查明了?”郦逊之微一踌躇,金无虑嘿嘿接道:“这事我去办,报酬加三成。”郦逊之道:“这回为朝廷办事,酬劳自少不了,可也多不了。”他伸出一只手指。
金无虑会意,拍拍郦逊之的肩,低声道:“我瞧的不是朝廷面子,大家同坐一条船,你查得爽快,我哥乐得轻松。互相多通气,比银子实在。”
郦逊之点头,心下径自寻思金无虑会如何查明左府翻修的事,突然想到小佛祖,便完全明白。小佛祖带了儿时的郦逊之四处游荡时,经常做小本生意或是以小手艺活为生,因此与七帮八会的工匠们极为熟络。金无虑既是偷王,少不得打造偷门八宝以及其它奇怪称手的器具,认得中原各地有名的工匠并不稀奇。左府修葺之事极为隐秘,未必会请京师的人,但总有蛛丝马迹为各行会所知,几下里探听明白再一归总,推算得七七八八应该差不离。
去查这事是金无虑比他顺手,郦逊之放了心。当下约好时辰,拿了金无虑所开的单子,交给在楼下的郦云,径直回康和王府去了。
等过了一、两个时辰郦逊之再问郦云,这小子把所要的东西找了个齐全。郦逊之道:“你全给我抬上一只空轿子里去。”郦云喏喏应了。郦逊之道:“你不问为什么?”郦云道:“公子爷去办事,小的自然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
郦逊之心想,这小子果然乖觉,笑道:“郦风呢?”郦云道:“依旧守在左府。”郦逊之沉吟:“他日日候着,会不会太招摇……”
郦云忙道:“这小子长得憨厚,出不了事。左府边上就是有名的延恩棚头,斗鹌鹑调鹁鸽的富家子多了,他凑在里面装傻,前阵还输了钱。”郦逊之抚掌笑道:“必是你教他的惫懒法子。”郦云道:“哪能呢,小的我再老实不过,只知在公子爷跟前安心听使唤罢。”
郦逊之但笑不语,想了想道:“叫郦风回府歇息,今日不必再看着。你且去罢。”
正说话间,外面吵吵嚷嚷,郦云忙出门去看,回来时脸色发白,颤声道:“公子爷……郦风叫人给打了。”郦逊之起身喝道:“伤得如何?”郦云哭丧脸:“吐了不少血,现下昏死过去。”郦逊之道:“快请太医!”郦云慌不迭应了出门。郦逊之到了院中,众人正围了郦风在看,郦逊之仔细瞧了两眼,是被好手卸了两条膀子,又打中胸腹要害,对方出手非常狠辣。
郦逊之替他接好膀子,郦风仍昏昏沉沉。郦逊之拉下脸问:“被谁打的?”有下人便道:“刚才我们出门,就见郦风跌跌撞撞拼死回来,说是和人斗鸡,对方输了不给钱,把他打了。话没说完人就晕了,也不知对方是谁。”
郦逊之心下踌躇,对方是凑巧碰上还是有意示威?多半后者。郦风乔装扮成普通百姓,明眼人仍能探出是郦家的人,没把人打死已给足面子。想到郦云时常候在雍穆王府也是一般凶险,连日不换人,叫王府给认熟了脸,等于把他们往火坑里推。
郦逊之叫人把郦风送到房里,等太医开了方子,屏退其他人,郦风悠悠转醒。郦逊之安慰了两句,道:“打你的是什么人?”郦风撑手坐起,道:“说是外地来的,可我瞧着像左府的,大年夜里见过他们进门。”
郦逊之一听,发了会呆,他之前是否低估了左家?龙佑帝让他去左家窃账簿,必是别有根据。郦风道:“公子爷莫虑,他们打我一场,我只咬定他们赖皮,打完也就算了。”
郦逊之道:“他们使了阴着,你有一个月下不了床。”说完,暗想左家这幕后主使人不知是谁,是左虎,还是左勤?心下略过了一过,却见郦风气息吞吐无碍,微微奇怪。郦风低头俯身,恭敬地道:“小的自幼练功,这些小伤不碍事,原是怕对方看破才故意挨揍。请公子爷放心。”
这一说,郦逊之忽地想起留在雍穆王府的金成,问道:“你有功夫的事,其他人可知道?”郦风道:“府里只王爷知道。小的功夫太差,只有挨打的能耐。”郦逊之不觉好奇,道:“郦云这小家伙有些什么本事?”郦风摇头,“小的虽跟他有话就说,也不知他除了牙尖嘴利、办差伶俐外有什么其它本事。”
郦逊之点头,出了郦风的屋子。他摊开当时要郦云办事的单子,那上面要的东西换作是他非找上一天,可郦云一两时辰就凑齐了。父王啊父王,郦逊之喃喃念着,对南方老父的担忧不由渐渐淡了。他送出的加急密函该到父王手上,燕家军虽有十万之数,深谋远虑的父王必可想出应对之道。
左府既有防备,此去又险上几分,好在郦逊之想到有神偷相助,并不畏难。酉时和郦云回到忘珍楼,叫了一席菜。金无虑穿了一身玄色直裰,肩上搭了个包袱,闲闲散散晃上楼来。
郦逊之把准备好的东西摊开,金无虑一一仔细看了,道:“很好。”郦逊之道:“这里有几样玩意却是新鲜。”金无虑神秘一笑:“一会儿你便知道。”郦逊之道:“几时走?”金无虑道:“叫了一桌好菜,正可大快朵颐。”举起筷子东挑西拣,翻来覆去。
郦逊之也不急,倒好茶,道:“今晚不便喝酒,金前辈原谅则个。”金无虑轻笑道:“放心,这门道我比你熟。他府里晚上会放出三十条恶犬,闻到一丝酒味就要当堂咆哮,最好你连菜也别吃,再好好泡个澡。”
郦逊之“呀”了一声,这层倒未事先想到。金无虑见他着急,反而轻松自如笑道:“莫急莫急,那些狗交给我对付,你就算喝它十坛八坛,它们决不会找你的麻烦。”郦逊之心生钦佩,道:“有前辈在,逊之就放心了。”
金无虑停箸,神情严肃道:“左府这回翻修请的是巧手龚,这人最擅绳缚之术,若是被他的机关缠上,多半被绑得严严实实。你有锋利的匕首没有?”郦逊之怔怔地取出当日楚少少所赠匕首,金无虑一下拔出,清冽的刀气侵面一寒,不由赞道:“好刀!”郦逊之神思恍惚,推想楚少少当日赠刀的用意,愣愣地捏起一杯茶,不识滋味地品着。
想到楚少少,郦逊之头脑里忽然忆起那日和楚少少动手的司徒淡,心下总有不安。司徒淡是名剑江湖门的头领之一,他究竟遗漏了什么,为什么一想到此人,总觉得忘记了什么事。
郦逊之发呆地凝视忘珍楼的栏杆,脑海中电光石火一闪,他知道忘了什么。在和楚少少动手前,司徒淡原本在一家客栈前张望,如果不是楚少少生事,司徒淡当时很可能就踏入那家客栈。让他好好想想,那是什么地方。
一下子,脑海中清晰起来,那家客栈的招牌晃眼地出现。
“望远客栈”。
郦逊之急忙叫来郦云,吩咐了两句,让他和郦屏商量查明这家客栈的底细。金无虑皱眉道:“奇怪,这家客栈的名字,我在哪里见过。”郦逊之忙道:“哦?请再仔细想想。”金无虑灵光一闪,叫道:“初四那日晚上,我和大哥本想入住这家客栈,谁知牡丹和芙蓉进了店,牡丹见我们在那里,就退了出去。”
郦逊之神色凝重:“今日初十,过了不少时日,为什么昨天司徒淡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