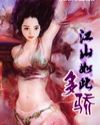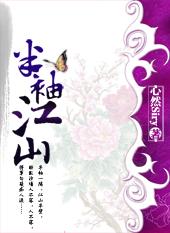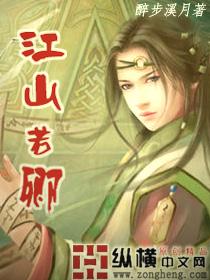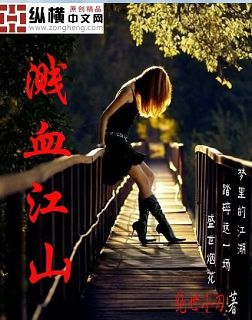江山岂是哭来的--正说刘备 作者 罗衾不耐-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两种成分,由此走上了他的英雄之路。
英雄自有英雄之器,英雄都是天生的料。百炼成钢,但炼的首先得是钢;烈火真金,但炼的首先得是金,否则都是白忙活。因此作为一个英雄,肯定从小就与常人相异,刘备也不例外。但这种与众不同,倒不是像虞舜和项羽那样一个眼睛里长着两个瞳孔(重瞳),也不是一定要显露现出什么英雄气概,而是要具备一种过人的特殊的内在品质。
少年时代的刘备就具有这种特殊品质,那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宽厚,而他日后为人称道的“仁义”,也无非是这种品质的延续和发展。人的秉性真的从小就不同吗?没错!三国时代的孔融三岁就懂得让梨,难道是谁教的?秉性使之然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善良是一种天性。即使一奶同胞,秉性也判然有别,命运更是天差地远。
在很多时候,具有善良根性的孩子,在童年的时候似乎总比别的孩子更加天真,乃至愚钝,但最终会走得更远。当刘备幼时站在那棵大楼桑树下,用手指着郁郁葱葱的树冠,对小伙伴说:“别看现在我家穷,将来我一定会坐上有这么大华盖的天子之车”(吾当乘此羽葆盖车)时,可以想见这个可怜孩子的孤独与无助。刘备幼年丧父,家道破败,但他的宗室身份,乡人知道,刘备自己也知道,乡人大概少不了逗他或嘲笑他,说你们家以前可不这样,还做过王爷呢。也许,从年幼的刘备嘴里说出的那番豪言壮语正是在一次次嘲笑的情况下被激发出来的。英雄不遇,古今同慨。
刘家的中兴昙花一现,家底还没攒厚就又一次败落了,沦落到孤儿寡母织席卖鞋的境地。这一波三折的家史,不能不对刘备的成长造成重大影响。在帮助母亲织席贩履的困苦阶段,刘备领略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和无比辛酸,“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先主传》)的性格大概正是在这一阶段炼就的。这段日子虽然辛酸,但对他绝对不是什么坏事。
其实,家遭变故并吃过苦,对于每一个官宦家子弟来说,都是一笔难得的财富,未尝不是他们摆脱纨绔子弟宿命的一个机会。大家族嫡出后继无人,而旁支庶出却人才辈出,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当年西汉灭亡,正是靠汉景帝第七子长沙王刘发的后裔刘秀在乱世中剪灭群雄,才得以光复汉室江山。而今,又出了一位汉景帝的远支玄孙,他也要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为汉室挣回一点颜面。他,就是住在幽州涿郡涿县大树楼桑连谱系都难以稽考的汉室宗亲刘备刘玄德。
幼年的刘备也不是一天好日子都没享受过,要不稀罕个“美衣服”就得了,怎么还同时向往“狗马”、“音乐”那样的高消费呢?同时,有心的族人也越来越发现刘备的确不是一般材料了,于是给予他越来越多的资助。《先主传》里特地留下了这位族人的名字,刘元起,大概是刘备的远房叔伯吧。
历史就是这样传下来的,大概是刘备当了汉中王以后,没少给自己的仨儿子痛说革命家史,说爹爹小时候可没少吃苦,还跟着你们奶奶一块织过席子卖过鞋。幸好你爸爸命中总有贵人相助,才创下了这么大的家业。记住:你们刘元起叔祖就是咱家的恩人,以后等咱们打回老家去,一定要报答他老人家呀。
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刘备的苦日子并没过多久,而且幼年也曾读书识字,这一点对于刘备的成长关系重大。三国时代之前有文盲打天下的例子,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位,三国时代以后也有,但这样的事情在三国时代却不成,一个文盲在那个时代蹦跶不了几天。同时,我们也可以确定,刘备小时候不可能一直跟着母亲织席卖履,那样涿州只会多出一位小商贩,而不会出现一位刘先主。
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想起近代中国的一个伟人毛泽东。毛泽东尽管生长在韶山冲一个殷实的富农之家,但他的父亲却目光短浅,不仅对自己的这个长子异常严苛,而且阻挠他继续求学。如果不是得到母亲家族以及其他族人的资助,毛泽东也许终身就是韶山冲的一个小地主或湘潭县城里的一个小生意人,但读书改变了他的命运。在长沙读师范时,毛泽东已经成为一个出了名的学生。后来得杨昌济教授的赏识,又在北大图书馆任过职,回到长沙俨然已是一个小小的名流,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熹平四年(175年),刘备十五岁,刘备的母亲让他拜当时大儒卢植为师。刘备之所以能够成为卢植的学生,一是刘家接受了可观的资助,摆脱了经济困境,甚至出得起不菲的束脩(学费)了;二是卢植也是涿县人,是刘家的乡党,而刘备汉室宗亲的身份多少也帮了点忙。
母亲这个非常有远见的决定,彻底改变了刘备的命运,从此,刘备不再是大楼桑树下那个孤苦无依的孩子,而是一个跃跃欲试要开创自己伟大前程的不凡少年。缑氏山下,风云际会。请看第四回:求学缑氏。
第四回:求学缑氏
刘备离开家乡,来到缑氏山(今河南偃师东)师从卢植。卢植身为一代大儒(儒宗),开的不是扫盲班,自然刘备也不是接受启蒙教育,而是求取大学之道。这也印证了刘备少年时代接受过启蒙教育,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否则太砸卢植的牌子了。
刘备在卢植门下时间不长,因为正是在熹平四年,卢植由于广才学、通文武,被朝廷任命为九江太守,后又转任庐江太守。尽管刘备不喜读书,但似乎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三国志》中记载了不少刘备出口成章、辩才无碍,甚至玩弄文字的故事,这说明缑氏山的学苑氛围对刘备多少有些影响,刘备在气质上多少也有点半吊子文人的意思了。
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拥有了“卢植学生”的名头,在那个时代这是所谓社会声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走上仕途乃至成为社会名流的重要条件。
从刘备后来的成长道路来看,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刘备结识了一个领路人——同学公孙瓒。这是刘备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缘,这个公孙瓒改变了刘备的一生,没有他,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刘备的命运肯定是另外一番模样了。
在卢植先生那里,第一次见到公孙瓒,刘备的感受肯定是震撼,在他的生命中也许这是第一次窥见一个世家子弟的风采。
出现在刘备面前的公孙瓒,身材魁梧,风姿伟岸,是一个阳光灿烂型的标准帅哥。也许更让刘备羡慕的是公孙瓒身上所流溢的那种世家子弟所特有的“范”,他神态自若,挥洒自如,说起话来虎啸龙吟,好像没有他办不到的事。可怜的刘备,虽然号称汉室宗亲,何时有过这等气度?刘备十来岁的时候跟着妈妈到集市上卖苇席和草鞋,低三下四,看人脸色,仰人鼻息,只学会了“善下人”的本事。沉默寡言,在人前甚至有些木讷拘谨的刘备,第一次发现竟然有这样意气张扬的人生,人竟然可以活得如此精彩。
公孙瓒,字伯珪,幽州辽西令支(今河北省东北角的滦县、迁安一带)人。幽州管着今天的河北北部以及辽宁、吉林的部分地区,属于东汉的东北边疆。《三国志》上没有记载公孙瓒的身世,但《后汉书》上有一笔,说他“家世二千石”,看来至少在他祖、父时任过郡守一级(相当于今天的局级)的官职。大概在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在本郡做了书佐,也就是一个抄抄写写的小吏,类似于现在的办公室秘书。《后汉书》怕别人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世家子弟怎么做了小吏,于是特意写道:“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看来公孙瓒尽管家道不错,但他却是庶出。不过这个“贱”字似乎还暗示不只庶出那么简单,也许他的母亲甚至都没有名分,而只是女婢或家伎。平常人家的子弟,能在郡府混个小吏也就不错了,但以公孙瓒的家世一开始做这样的差事却不见得有什么光彩。
前文已经说过,世家巨族的庶出或旁支往往更出人才,这个公孙瓒无疑又提供了一个例证。由于他才干出众,侯太守对他非常器重,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什么才干呢?史书记载的是,聪明机变,口齿便给,记忆力超群,每次汇报工作时也没废话,而是攒齐了几件事一起说,毫无差错。这样的干部,即使搁到现在,也一定会得领导欢心的。
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江山岂是哭来的——正说刘备》 第5节
说来有趣,那时与现在虽然相隔近两千年,但许多事情还惊人的相似。公孙瓒直接进郡衙门做了书佐,相当于现在的“走后门”。但这种方式跟现在一样都不是当官的正途,都属于“以工代干”,由于没有学历或公务员资格,很难“转正”,很有可能做一辈子小吏。怎么才能走上正途呢?侯太守给女婿指道了,还是得上学呀!于是公孙瓒来到了卢植的门下。
因此,刘备与公孙瓒这一对好同学,其实相当于现在的党校同学,只不过公孙瓒是在“干部进修班”接受培训,而刘备读的是“专接本”。其实,即使到现在,党校也是某些官场有心人联络感情、交朋纳友的好地方。
刘备是一个没见过太大世面的穷小子,对已经成家立业并在官场混过的公孙瓒自然非常仰慕,也很想高攀,这并不稀奇,但公孙瓒却也愿意结纳刘备这个穷困的小兄弟,这就有点奇怪了。其实也不难解释,因为他们属于典型的互补型朋友。他们两人性格大异,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公孙瓒性格外露,声若洪钟,喜欢大声谈笑,自恃才力,不甘人下;而刘备则性格内向,不善言语,喜怒不形于色,“善下人”。看来,这两个人不做朋友也难。
不过,公孙瓒能够与刘备成为朋友,也许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身份上的互补。公孙瓒虽出身世家,但身份却十分可疑,简直没法说出口;而刘备虽然穷困,却是传说中的汉室宗亲,他可以拍着胸口说:俺爷爷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因此,底子不太光彩的公孙瓒需要刘备这样一个有点“来历”的朋友,而空有虚名却经济拮据的刘备则需要一个有实力的朋友。在这里我们看到,汉室宗亲的名头还是帮了刘备的忙了。
在他们的交往中,自然是刘备把公孙瓒当大哥待,说穿了就是做了公孙瓒帮闲式小弟。做小弟有很多种,至少帮闲和帮忙是不同的。做帮闲倒不要紧,那未尝不是积蓄力量等待机会,关键是自己有没有大志和能力。当年的杜月笙不也给黄金荣做过帮闲吗?刘备不仅做过公孙瓒的小弟,以后还要改换门庭好几次,但他心中始终葆有不灭的志向,时间最终证明刘备不单单是做帮闲的料。
从十五岁开始,刘备把大自己几岁的公孙瓒当了大哥。但在潜意识里,也许这个幼孤的孩子已经把公孙瓒当成了精神之父。此后,刘备以这种心态,跟公孙瓒打了二十年的交道。前十年,刘备是公孙瓒的小弟和宾客;后十年则做了公孙瓒的部属,直到领兵救援徐州时才脱离公孙瓒的羽翼另立门户。这一经历往往被三国论者一笔带过,但我们不能忘记,刘备做过整整二十年的小弟。这二十年,刘备由一个胆怯的土里土气的村娃,成为一个被曹操和袁绍都待为上宾的英雄。
是公孙瓒栽培了刘备,不过多年以后刘备会发现公孙瓒竟然也有脆弱甚至孩子气的一面。后来,公孙瓒可笑而悲地死于自己的堡垒之中,而刘备则游走于广阔的天地中,与天下第一英雄曹操周旋。刘备一直在成长,公孙瓒没有做过的事情,他这个曾经的小弟做到了。
《先主传》上说刘备“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些爱好也只有在结识公孙瓒之后才能付诸实践。中国自古就有宠物狗,但犬与马连在一起,却是指骑马狩猎,犬应该是猎犬。纵马射猎,在当时既是享受,也是世家子弟磨砺品质、提高能力的一种方式,至少从西周开始就属于贵族子弟所必须掌握的“六艺”中的核心科目。而“音乐、美衣服”,则纯属享受了,不过在当时也是身份与尊严的象征。看来,一个无可稽考的宗室子弟在一个现任世家子弟的帮助下,学会了如何追求尊严,如何自信地对待生活。
按理说“声色犬马”是连在一起的,但在这里为什么唯独少了“色”?其实,古代男人对于女色,哪有不好的?这是不在话下的事情,而只有“声”“犬”“马”才值得一提。假如“好色”是指男性对女性的欣赏和占有,这在古代从来就不是男人的耻辱,而一妻多妾更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其实在古代,好色根本不是问题,恰恰是“爱”才有问题。袁绍、刘表喜欢宠妾所生的幼子,公孙瓒和吕布穷途末路只知沉溺酒色、贪恋妻女,这才是被人耻笑的。曹操分香卖履的遗嘱,大概也体现了所谓的“爱”,幸好他是一代英主,没有事败身死,否则他的“爱”也成笑柄。而曹操的“爱”,即使算做与当代语境接近的“爱”,但也是在妻妾成群情况下的“爱”,是对她们未来的关切,而希望她们自谋生路的想法,又何尝不是一种希望在自己死后也不想让别人染指的贪婪?这种“爱”,现在的小儿女真的可以理解并接受吗?现在有的小儿女还在替关羽辩护,好像关羽一旦好色就不是英雄。其实这也是对历史的无知。英雄哪有不好色的,关羽不好色还跟着刘备折腾什么。笔者尽管推崇三国英雄,甚至提出英雄从小就与众不同,但同时又时时刻刻在强调英雄的特性并不玄妙,只不过他们能够把常人的某种特性加以放大或坚持而已。
其实就连刘备的仁义也同样没有什么玄妙,也无非对民间疾苦和世事情伪有些体察,对老百姓多了些同情心,心软一些而已,还有其他吗?至于“女色”,先主自然是好的。但他的“好”,是从来不把女人当回事,也没因女人误过事!岂有他哉?在这一点上,有“高祖之风”的刘备,其实比他的先祖刘邦还要厉害,刘邦只扔过一次老婆孩子,而刘备竟然扔了四次,恐怕这也创下了一个吉尼斯记录了。不过在那时,这绝对不是什么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