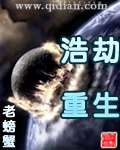上海生死劫-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海生死劫》
作者:郑念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纪实小说。本书主人公,曾是国民党一名高级外交官的妻子。上海解放前夕,携独生女儿自海外归来。解放后任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这是解放后唯一留在大陆上的西方石油公司)。十年浩劫打破了她宁静、舒适的生活,她被批斗、抄家,并被投入监狱。更使她悲痛钬绝的是,她所钟爱的当电影演员的独生女儿被活活打死……这是一个发生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的惨绝人寰的真实故事。它自始至终紧紧抓住读者的心,令读者随书中主人公而哭泣、而绝望、而愤慨!本书作者时。十午文革的独特的思考,也值得引起人们的深思。
一个对祖国有着深厚感情的,曾经与国家共同经历过生死的;非同寻常的伟大的女性。
一代名媛郑念以94岁高龄辞世,她留给人间最珍贵的礼物,莫过于其细述〃文革〃时期的个人回忆录《上海生死劫》。世人从中看到,一位优雅、坚毅、机敏、高贵的女性,面对野蛮和强权的侵犯时,如何坚守底线,维护自己生而为人的尊严,以及心中不可折损的价值。
作者介绍:
郑念,外交官夫人,曾留过洋,文革因被诬为英国间谍,坐六年牢,什么罪都遭了,硬没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出来时才知道女儿被红卫兵杀害。后来到美国写了本书。这是郑念72岁时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的照片。朱大可说,她有比古瓷更美更硬的灵魂。老太太最后在华盛顿异乡安静终老,享年94岁。
郑念,作家,生于1915年1月28日;逝于2009年11月2日。
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于中国北京。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北平燕京大学。留学英国于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著名的左翼政治学教授拉斯基(haroldj。laski),获硕士学位。她在英国认识了同是留学生的郑康琪,两人相爱结婚,婚后她跟随先生改姓郑。1949年带着唯一的孩子郑梅平从香港到上海,回来参与红色中国的建设。郑康琪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澳大利亚官员。49年后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shell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pany)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1957年死于癌症。1957年到1966年郑念在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任职。文革期间遭到迫害,导致家破人亡。独生女儿郑梅平遭红卫兵活活打死。她被抄家,1966年到1973年被关押在上海第一看管所,受到六年半的拘禁。1980年9月20日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后至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三年后定居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去国前,她将抄家发还的珍贵文物无偿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郑念对文革的个人叙述《上海生与死》出版于1987年。出版后即成为英语世界畅销书。好评如潮,该书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连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库切都忍不住在《纽约时报》上写书评,推荐这本书。
文章试读:
那逝去的,是再也回不来了,却是难以忘怀的。此刻,我的思絮,又回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那是个酷暑难熬的晚上。'那是在我上海故居的书房里。找女儿,正在她自己房里睡得香着呢。佣人们,也都在各自房里忙他们自个的事。我独自一人呆在书房里,只听得吊扇在我头上嗡嗡作响,空寂又单调。因着那恹恹的暑气,括在乳白色乾隆古瓶里的朵朵康乃馨,都垂头丧气,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沿墙一排书架,满是中外经典名著。幽暗的灯光,将大半间居室,都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下,但白沙发上一对缎面的大红绣花靠垫,却还是鲜亮夺目,扎眼得很。
我的一位老朋友,是个英国人,曾声称我这个家,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这话倒也不过分。我的居所,虽则称不上华厦美屋,但就是以西方标准来说,也可属于趣味高雅的了。唉,为了这个家,我真是费煞心思了,我力求让它成为我们母女俩一个温馨舒适的安乐窝,以使我们得以在这个越来越无产阶级化的城市里,多多少少还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品味度日。解放以来,在上海这么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之中,仅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方能维持着旧日的生活方式,诸如住在原来的宅第,家里雇有几个仆人。
当然,共产党悬从来不会强制命令,以划定人们该如何生活的模式。但事实上,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为着解决社会失业问题,雇主是不可以解雇自己雇员的,但不间断的各种政治运动,又使一些过去富裕之辈逐渐陷入日趋贫困之境。当他们成为多次运动的对象时,他们或被克减工资,或被课以大笔罚款,不少私方人员,不得不携带家眷离开上海,迁至内地边疆。而我依然能一切照旧,这不仅因为我具备有维持我旧有的生活方式的经济实力,而且也因为,我是统战的对象。但不管怎么说,我和女儿,还是谨慎小心、安分守己地过着日子,我们深信共产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愿跟随历史车轮共同迈步。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午夜前那段时光,竟是我们母女俩持续多年的宁静温馨生活的最后的几个小时了,难怪我的思絮,常常会回到那个时光。那晚,整个城市闷热异常,即使敞开门窗,也不见半丝凉风。我的脸颊和手肘都是汗涔涔粘乎乎的,衬衣汗湿得粘贴在脊梁上。我俯身逐句逐字地琢磨着报上的文字,每一次政治运动前夕,报上都会登载一些语气激烈、措词强硬的文章,它们是为着制造宣传舆论,用以武装群众的头脑。我经常琢磨细读这些文章、社论,因为从中可捉摸和分析出每次运动的目的和它们所针对及打击的对象。在这以前,我从未被牵连进任何政治运动之中。因此那时,我竟一丁点都未意识到,事实上,我巳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大难了。不过与往常一样,那些社论中的措词和强硬极端的语气,令我感到十分的不安。
基本信息:
本书郑念记述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八十年代初出国这段时间的个人经历。对文革的记录尤如史实,读起来好像在读一部文化革命史。郑念在记录史实的时候,既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政治事件,也仔细地记录了这些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使这本书有种个人编年史的性质。这本书也以编年的方式写下来的,从文革开始,到抄家,到软禁,到被捕入狱,上海的一月革命和军管,党内斗争和她在监狱中的经历,直到释放回家,尼克松访华和她最终获得离开许可,发展的顺序与时间顺序同步,对那些对文革所知不多的人来说,这本书可以是一本文革史,特别是上海文革史,虽然是通过个人经历来展现的。由于本书具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对文革中的种种政治风波、事件都有记载和分析,这本书也反应了一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红色中国的个人思考。个人性与历史性的结合,使本书独树一帜,其独特的角度弥足珍贵。
和女儿郑梅萍作者的女儿梅萍曾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念书,后来在上影厂当演员,但是可以肯定,她没有在银幕上露过面。书中多次提到一位梅萍的好朋友'孔xx',就是上影演员孙栋光,他是《武训传》导演孙瑜的儿子,也就是在《玫瑰香奇案》里演一只鼎的演员。
郑念原名姚念媛,丈夫郑康琪,是郑观应的后代。在《繁华静处的老房子》一书中有他们的介绍。。姚也是个收藏家,曾经将自己收藏的古董捐献给上博,在《上海收藏家》一书中有她的一些事迹介绍。
女儿梅萍的死是她心中一个永恒的痛。梅平生于澳洲,有澳大利亚国籍,本不须回中国,这个错给她的伤痛,当她老病孤苦无依时,就越发加剧。而当她获悉杀害她女儿的凶手胡永年依然健在、儿孙绕膝时,更是心如刀割。
〃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福楼拜在张戎的《鸿wild swan》(1991)在西方引起轰动之前几年,另一位中国女性的文革相关作品就已经成为了畅销书--那是第一本有关文革的英文畅销书,而作者本人也在文革期间历尽苦难。郑念的《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1987)是一本充满着巨大悲欢的回忆录,作者郑念日前逝世了,享年94岁;这本书可以解读为一部反映现代中国本身的代表作。
随着这本书的发行,她获得了赞誉。这本书好评不断,部分原因出于这本书以一个人的视角,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述了文化大革命野蛮残酷、令人不解的故事。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发生的那些事给郑念带来的心灵创伤却不易抹去。她在2007年对《时代周刊》说:〃我在华盛顿的生活充实而忙碌。只是有时会感觉到一种萦绕于心的忧伤。黄昏时分,当白天渐渐远去,我的精力也下降了,我会觉得自己抑郁沮丧,怀念从前。但是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又总带着新的乐观情绪迎接一天的到来,上帝赐予我们每一天,让我们有机会去获得启发,经历人生。我唯一的遗憾是梅萍不能陪在我身边。〃程乃珊是上海作家,其母亲潘佐君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43级教育系)。这个译本属于翻译体,有不少删节。
据说大陆译本以百家出版社内部发行的版本删节最少。
目前大陆及台湾的译本都有不少缺点,感兴趣的去读原版吧。
大陆曾经发行的中文版:
《生死在上海》方耀光、方耀楣、郑培君合译1988年8月百家出版社(内部发行)。
《上海滩的沉浮》上下册华克健曹思韧人译春风文艺出版社《上海生死劫》上下册苏帆译1988年10月中外文化出版公司这书也只能在87…88年间的中国公开发行。89年以后,该书和作者都受到了批评,幸亏当时作者已经在美国定居了。谢晋、徐枫都曾想把本书拍成电影,均无果。
=================
第一部革命风暴 第一章政治迫害
那逝去的,是荐也回不来了,却是难以忘怀的。此刻,我的思絮,又回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那是个酷暑难熬的晚上。'那是在我上海故居的书房里。找女儿,正在她自己房里睡得香着呢。佣人们,也都在各自房里忙他们自个的事。我独自一人呆在书房里,只听得吊扇在我头上嗡嗡作响,空寂又单调。因着那恹恹的暑气,括在乳白色乾隆古瓶里的朵朵康乃馨,都垂头丧气,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沿墙一排书架,满是中外经典名著。幽暗的灯光,将大半间居室,都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下,但白沙发上一对缎面的大红绣花靠垫,却还是鲜亮夺目,扎眼得很。
我的一位老朋友,是个英国人,曾声称我这个家,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这话倒也不过分。我的居所,虽则称不上华厦美屋,但就是以西方标准来说,也可属于趣味高雅的了。唉,为了这个家,我真是费煞心思了,我力求让它成为我们母女俩一个温馨舒适的安乐窝,以使我们得以在这个越来越无产阶级化的城市里,多多少少还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品味度日。解放以来,在上海这么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之中,仅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方能维持着旧日的生活方式,诸如住在原来的宅第,家里雇有几个仆人。
当然,共产党悬从来不会强制命令,以划定人们该如何生活的模式。但事实上,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为着解决社会失业问题,雇主是不可以解雇自己雇员的,但不间断的各种政治运动,又使一些过去富裕之辈逐渐陷入日趋贫困之境。当他们成为多次运动的对象时,他们或被克减工资,或被课以大笔罚款,不少私方人员,不得不携带家眷离开上海,迁至内地边疆。而我依然能一切照旧,这不仅因为我具备有维持我旧有的生活方式的经济实力,而且也因为,我是统战的对象。但不管怎么说,我和女儿,还是谨慎小心、安分守己地过着日子,我们深信共产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愿跟随历史车轮共同迈步。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午夜前那段时光,竟是我们母女俩持续多年的宁静温馨生活的最后的几个小时了,难怪我的思絮,常常会回到那个时光。那晚,整个城市闷热异常,即使敞开门窗,也不见半丝凉风。我的脸颊和手肘都是汗涔涔粘乎乎的,衬衣汗湿得粘贴在脊梁上。我俯身逐句逐字地琢磨着报上的文字,每一次政治运动前夕,报上都会登载一些语气激烈、措词强硬的文章,它们是为着制造宣传舆论,用以武装群众的头脑。我经常琢磨细读这些文章、社论,因为从中可捉摸和分析出每次运动的目的和它们所针对及打击的对象。在这以前,我从未被牵连进任何政治运动之中。因此那时,我竟一丁点都未意识到,事实上,我巳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大难了。不过与往常一样,那些社论中的措词和强硬极端的语气,令我感到十分的不安。
老赵,我家的男佣人,手持托盘端来一杯冰镇红茶。我呷,日冰茶,将目光投向我丈夫的遗像。虽说他离我而去已有整整九个年头了,然而因失却他而感到的空虚和寂寞,时时还萦绕在我的心头。每逢我在政治上受到缺乏安全感的骚扰时,我总会觉得自己是那般孤单无靠,我需要他的庇护和依傍呀。
我们是一九三五年在伦敦相识的。那时,他正在苦读博士学位。婚后,我们于一九三九年回到抗战时期的国民党陪都重庆,他就在国民党外交部任职。上海解放时,他是国民党外交部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当时前来接管的共产党代表章汉夫:仍然聘留他,请他任陈毅将军即过渡时期新任的上海市长的外交顾问。次年,他获准辞职,即就任亚细亚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与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及帝国化工厂等…样,亚细亚也是英国跨国贸易公司的机构。亚细亚公司当时仍然希望能保留驻中国的办事处。为着亚细亚是唯一的一家仍愿意留在中国大陆经营的西方石油公司,本着和西方国家发展贸易的原则,政府当局对该公司还是十分